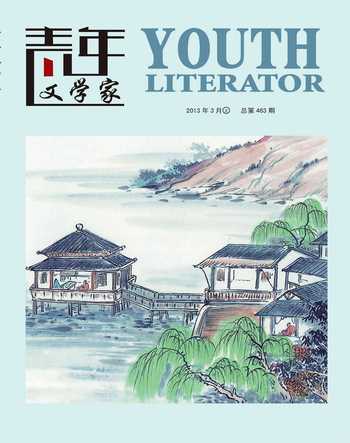論余華小說《活著》、《一個地主的死》
摘 要: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新歷史小說”的創作高潮。余華就是新歷史小說的代言人之一。本文在新歷史主義視角下分析余華作品《活著》與《一個地主的死》兩篇小說中所體現的“生”與“死”的意義與內涵,并詮釋人道主義存在的價值以及對人“生”與“死”的思考。
關鍵詞:新歷史小說;生;死
作者簡介:張雪芹(1987-),女,民族(侗族),湖南新晃,中教二級,湖南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學科教學語文。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7-0-01
一、新歷史主義的內涵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文壇上出現了的“新歷史小說”的創作潮流。小說家們通過寫“家族史”、“村落史”、“心史情史”、“秘史野史”、“外史異史”和“民間歷史”來“重構歷史”、“調侃歷史”、“戲說歷史”甚至“顛覆歷史”和“解構歷史”1。他們無情的批判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通過一些瑣碎的歷史片段和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來顛覆歷史的因果規律和必然規律。在新歷史主義小說中歷史的偶然性力量起了極大的作用。新歷史小說的角度從重大的政治事件、重大人物轉移到平常的世俗生活、普通百姓,實現了“從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從宏觀到微觀,從顯性政治學到潛在存在論”2的轉變。
二、新歷史主義與余華作品特點的結合
余華是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他的作品中所突顯的新歷史主義的特點:他特別關注在歷史中的個人命運,顛覆客觀、真實的傳統歷史并摻雜大量的主觀色彩以塑造文本化的歷史,隔斷了必然的連續的歷史,注重歷史中的偶然事件;他關注社會現實,試圖通過一些與主流社會不符合的人物,意識和結論顛覆歷史和主流意識形態;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品質都來源于民間,民間簡樸淳厚的文化和堅韌不屈的精神幫助余華鑄就了一部民間的“小歷史”,這對傳統“大歷史”進行有益的補充,也是對傳統的反抗,更是余華本人對人們生活與命運的深切關懷。
三、《活著》 中的“生”
《活著》是余華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角福貴便是余華虛構的地主形象。福貴生在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身上沾滿了各種惡習。年輕的時候吃喝嫖賭,中了龍二的圈套傾家蕩產。老婆離他而去,父親因病去世。還了賭債后便過上了多災多難的生活。自己耕田犁地,有上頓沒下頓。因為給母親抓藥,而被抓去當兵,飽受摧殘。后來母親也離世。僥幸還有妻子兒女在身邊,福貴決心做個安分守己的地里人。福貴從抗戰到文革期間命運多舛,既偶然也必然。福貴本來可以生活得很富足。可是福貴的命運并沒呈現這樣的必然趨勢。從祖宗到福貴,家產日漸變少,最后一貧如洗。但因此才因禍得福,讓福貴在批斗地主運動中挽救了自己。龍二賭贏福貴的家產在土地改革中,被劃成惡霸地主被槍斃了。歷史的偶然性在這里展現得一覽無余。福貴決心做一個好人民好丈夫好父親時,命運又“偶然性”地向他發出挑戰,親人接連死去,讓他苦不堪言。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老人活著。福貴目睹了身邊的人一個個死去,似乎是明白了生命的意義,也能夠坦然面對自己將要面臨的死亡。他說,“我也想通了,輪到自己死時,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著收尸的人,村里肯定會有人來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氣味誰也受不了。我不會讓別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頭底下壓了十元錢,這十元錢我餓死也不會去動它的,村里人都知道這十元錢是給替我收尸的那個人,他們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們埋在一起的。”余華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在被主流意識所掩蓋下的小人物,面對生活的艱辛與苦難,無法逃避,沒法解決,只能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在《活著》中,余華并沒有寫歷史大事件大人物,而通過對個別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寫,展示了底層社會既充滿悲苦艱辛又不失恬淡自在的面貌,這種民間的文化更能讓歷史駐扎人們的心底。余華用《活著》從另一個角度來詮釋了生命意義內涵。福貴,用自己堅韌的精神與命運作斗爭,成了余華眼中的生命意識的代言人。他有農民所擁有的堅強的意志,他能看透人生活的哲理。他是在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告訴世人活著的意義。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他并沒有頹廢不堪,而是變得無比堅強。
“福貴”這一形象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刻畫得足夠經典、足夠令人感動,余華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感情。余華也從這個側面展現了一段中國歷史上的荒誕可笑,義正詞嚴的批斗地主運動被余華變成了歌頌地主。這也是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
四、《一個地主的死》中的“死”
上一節我們提到余華對地主形象尤為鐘情。《一個地主的死》塑造的也是一個令人感動不已的地主形象。與《活著》不同的是,《一個地主的死》中王香火死于民族大義,是“英雄式”的。這是一篇故事情節簡單的中篇小說,地主王香火自愿帶著日軍走到孤山,并且抓住機會讓人拆了所有的橋梁將鬼子困在孤山,自己最后也犧牲了。他父親接到兒子的噩耗,也死在糞缸內。香火在死時喊了一句,“爹啊, 疼死我了。”若是別的英雄,一般都是豪言壯語,而王香火卻是“爹啊,疼死我了。”人們的意識中英雄必定不會使用這樣的語言,這也不會是英雄所要表現出來的形象,但是讀者卻會認為王香火是個英雄。這種平凡、普通的英雄形象更能讓人們接受,更能讓人信服,更顯得真實。死與生是相反的兩方面,而人在不知死亡何時降臨的時候仍然不畏懼死亡的存在,并且能夠直視死亡的存在,這就是人道主義精神。王香火“死”的價值是存在于 “民族大義” 之中。這就與福貴的 “生” 不同,福貴的生是個人化的。
《一個地主之死》沒有描述戰爭的殘酷,只是寫了主人公王香火的愛國之情。王香火沒有認真鉆研過愛國主義,英雄氣概。但是他還有人性基本上的良知和正義感。他愿意獻出自己的生命盡自己所能去挽救身邊的人。人心的丑惡與善良在文本中交織出現,《活著》是一部正氣歌, 帶給人向上的力量。 《一個地主的死》則更多的反映出人心的冷漠與黑暗社會中人生活的麻木與困苦。小說中王香火是一個地主,這是被百姓所唾棄的,從沒人會認為他會是一個英雄。但是,王香火不同于一般的地主有那么多惡習,不膽小怕事,當他看到日本兵進村并強行人民帶路甚至殺害性命時,他毫不畏懼地走向日本兵,主動給他們“帶路”,最后死于日本人的刺刀下。這樣的王香火,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英雄,但就是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更貼近人民的內心。
五、結語
余華的這兩部小說《活著》和《一個地主的死》都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解釋人存在的價值。都體現了人的兩個方面——“生”和“死”。而人生的這兩大方面究竟是什么樣的內涵和意義,都是靠個人本人去體現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一大特點摒棄大事件大人物大英雄的描述,在這兩篇小說中得以完整體現。而余華也借助于自己的小說進行關于人生的思考,關于為何活著,為何死去的哲學思考。
參考文獻:
1、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英]羅素.論歷史[M].何兆武,肖巍,張文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1.
3、余華.活著·韓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