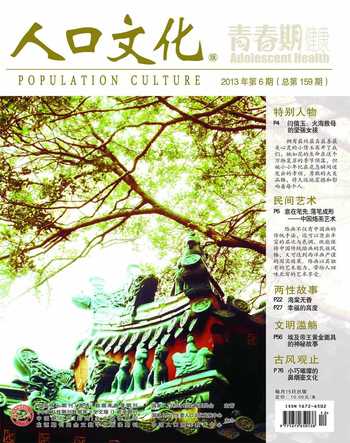尋找中國最美鄉村
張艷庭

真正的旅行是一種尋找。而我們此行所要尋找的,就是“中國的最美鄉村”。通往它的路,應該就是一條土路,路旁流著清澈的溪水,種植著金黃的油菜。
真正找到婺源“中國最美鄉村”的美之所在,是在思溪延村。這是相距不遠的兩個村落。在同行的人乘車去思溪的時候,我和同行的一位畫家選擇鄉間小路,步行去了延村。做出這個決定,并非是一種標新立異的特立獨行,而是在水泥路和一條溪流邊的鄉村小路,在乘車與步行之間本能直覺的選擇。鄉村的距離概念,讓我可以更加相信自己的腳,相信自己的本能和直覺。如果說城市讓人對自身的本能加以懷疑,天性加以禁錮的話,那么在婺源,這個號稱最美鄉村的地方,人與自身的關系恢復到了更為自然親和的狀態。當雙腳踩在泥土之上,人并沒有離旅行的目的地更遠,而是離它更近,離旅行的本質更近。
真正的旅行是一種尋找。而我們此行所要尋找的,就是“中國的最美鄉村”。通往它的路,應該就是一條土路,路旁流淌著清澈的溪水,種植著金黃的油菜。美國詩人弗洛斯特在詩歌《兩條路》里寫道:“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我的人生從此便不同。”而在這里,這句詩可以翻譯為: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便走進了真正的鄉村,而不是一個純粹的旅游景點。
溪水清澈碧綠地流動著。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在婺源,有許多條這樣的河流,繞在一個個村莊旁邊,為村莊提供水源,也提供清澈與寧靜。是流水聲提醒了我這里的寧靜,而在城市里,是汽車的馬達聲、鳴笛聲、臨街店鋪聒躁的歌聲提醒我要為自己的內心保留一份寧靜。在這里,我不用刻意為之,溪水自然就把身體中的噪音沖走。除了寧靜,它帶給我的還有清澈與充盈。這種清澈與充盈不僅僅是因為溪水流經了金黃或碧綠的田野,倒映了古老的村落,更重要的是,這溪水仿佛是與它們一體的,而這里就是它的發源地。用朱熹的詩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來形容這些溪水再合適不過。這不僅是因為詩、景、情的完美契合,還因為朱熹的故鄉就在婺源。雖然他人生中大部分時光都在福建度過,只回過婺源數次,但故鄉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無法從人生中抹去的。如果說游子是河流的話,那么故鄉就是它的源頭。那么這詩句中溪水的源頭,甚至這首詩的源頭,應該就是婺源的這些溪流了。
溪水的清澈不光清洗著我關于河流的記憶,也在清洗著眼前油菜花的金黃。因為這種清洗,我遠離了北方土地的廣袤以及與之同在的干旱。在北方,映襯油菜金黃的是田野無盡的土黃。在這里,則成了水的嫩綠。嫩綠與金黃,組成了春天在這片田野上的色彩譜系。而緊挨著田野的村落建筑,用它宣紙般的白構成了這片彩色田野的底色。白墻是徽居的一大特色,在婺源的整個行程中,白色的墻壁幾乎無處不在。尤其是一些新建的房屋,那些陽光下耀眼的白幾乎呈咄咄逼人之勢。而在延村這樣的古村落中,那些白色的墻壁經過雨水長年的洗滌,色澤已經柔和許多。雨水不僅洗去了它的白中刺目的部分,還為它涂上了一層歲月的色澤。在婺源那些白色墻壁的背景下,雨水的顏色似乎呈現墨綠色。墻壁上那些經它繪制的水墨畫就是證明。而雨水經年累月的沖洗,讓這幅水墨畫更像是歲月的真跡。
步入延村,就像是步入了一幅立體的水墨之中。與之前去過的一些村落不同,這里不僅古居保存得完好,整個村落的布局也完好如初。沒有新房與舊居的強烈對比,也就沒有了直接從現代一步跨入古代的突兀與生硬。老房子之間都是由一些窄窄的小巷間隔與相連,宜于步行,宜于仰望著夾在高墻間的藍色天空——如果是雨天,它就是真正的詩句中記載的“雨巷”;當然對于一個陌生的旅人來說,還宜于迷路。也許對于一個現代旅人來說,只有通過迷路,才能真正到達這座古老的村落,到達它氣質的核心。
許多現代村莊,經過集體主義與重利主義的雙重改造與洗禮,布局往往會格式化,通常是由一條大路貫穿整個村落,數條小路橫穿村落。所有房屋院落都被這些筆直的道路統率而一覽無余。私人空間——院落與公共空間——大街之間沒有緩沖地帶。而且所有私人空間都在公共空間的統領中,體現了鮮明的秩序。但在延村,代表私人空間的房屋院落,都是獨立的,院落與院落之間的聯系也是曲折婉轉的,沒有一個統一的秩序能夠統率這些院落。這些曲折的小巷即是證明。
走進這樣的院落和房屋,對于它的獨立性會有更深的感受。除了白墻黑瓦,高高的馬頭墻是徽居的另一大特色,或者幾乎可以說是代表特色。它的功能不僅僅有實用意義上的防火和裝飾意義上的美觀,一個同樣重要的作用是遮蔽。就像那些曲折的小巷遮蔽了院落的大門一樣,它同樣從高處遮蔽了與鄰居之間的視覺往來。這樣,不管是在地上,還是在空中,它都保留了自己的獨立性。但它卻不拒絕天空自身的窺視。天井就是這一只專門為天空預留的眼睛。即使最為狹窄局促的房舍中,都為天井留下了空間,即使只是“一線天”。因為天井的存在,院落、房屋中的人可以直接與天空交流,從更高的意義上來說,接受天空的審視。此外,它還通過天井接納天空的祝福——雨水。學者張檸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民間文化離不開“福祿壽喜”。不例外的是,通過天井接納的雨水在民俗意義上就擁有財富的意味。這在主人身份多為商人的古徽居中,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即使從農業角度來解釋,也符合農耕文化對人與自然溝通的重視。而發端于朱熹理學的風水學對這種溝通更加重視。天井即是最符合風水學的一種建筑樣式。雖然有將自然神話的嫌疑,但風水學在客觀上還是強調建筑和自然融為一體,人居回歸自然,使整體環境美化,居住者更加舒適。從現代建筑學的角度來看,天井也是一種獨特、美好、充滿智慧的建筑形式。而我在歸來之后的詩作中,這樣寫天井:“雨水從天井落下/就是大地接住了天空/庭院接住了水的一次流淚。”這樣在居室中與天空、雨水的親近,對于一個居住在北方城市的人來說,是可望不可即的。似乎是因為如此,庭院和雨水在詩句中都具有了人格色彩。拋卻各種學說的專業角度,這種建筑樣式本身也為如何“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提供了范本。
如果說天井溝通了人與天空、雨水的自然關系的話,那么徽居內的磚雕、木雕、石雕則溝通了人與萬物之間的審美關系。這些雕刻內容涉及人物、山水、花卉、禽獸、蟲魚,無不錯落有致,玲瓏剔透,栩栩如生。在對于徽雕的介紹中,我看到它豐富的題材:云頭、回紋、八寶博古、文字錫聯,以及各種吉祥圖案世間萬物,人倫物理,幾乎都可入雕。雖然我所看到的雕刻內容有限,但那些把有限的內容賦予無限精美的雕刻技藝,似乎彰示著它可以承載內容的無限。于是這些雕刻就似乎彰示著一個房子就可以擁有一套獨立完整的審美體系,彰示著房子主人高雅的審美趣味。
與這些雕刻相互輝映的,是那些懸于正堂左右的楹聯。楹聯的內容彰示著儒家倫理和對詩書、自然的崇尚與喜愛。這樣的楹聯我在許多古鎮的深宅大院中都見到過,而在這些小小的村落之中,這些楹聯的內容并不絲毫遜色。婺源有“書鄉”之稱,自古文風鼎盛,自宋至清,出進士552人,著作3100多部,其中172部入選《四庫全書》。這些楹聯佐證了這里的文風之盛,彰顯了書鄉風范。
由這些細節構成的獨特的徽居,讓我久久地留連忘返,踱步品味,想著數百年前,這里居住著怎樣的人,他們過著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儒家理論的重視,決定了大多為商人的徽居主人,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崇尚詩書的理念。也許有許多人只是附庸風雅,但同時,應該還有更多真正的文人,他們在讀書之余耕種,“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文致典雅的居舍居室與周圍的田野都鐫刻下了他們的身影。他們像陶淵明一樣,踐行與創造著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的耕讀文化。這種文化影響深遠,我在許多地方的老宅子里都看到過“耕讀傳家”的字眼。而婺源的這些小村落,幾乎是這種耕讀文化的一個樣板。它們完美地承載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文化夢想。初到婺源時,我感覺這里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態,讓我恍生世外桃源之感,而現在,它們又在文化上構成了一個真正的桃源。
歸來后,我在書籍中找尋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時,遇到了辛棄疾。他在仕途失意后,曾隱居在江西上繞二十余年,把上饒帶湖的新居命名為“稼軒”,堅持耕讀,也寫下了大量農村生活的詩詞。婺源即屬上繞,雖然他沒有直接居住在婺源,但居住的環境應與婺源的這些村落相似。于是在這些村落中默誦辛棄疾是情景相合的。“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這首《西江月.夜行黃沙蜀道中》是詞人最具代表性的詞作,而詞名中的黃沙,即是江西上繞的黃沙嶺。地點是基本照應的,只是時間上不對,我們在春天來到這里,也沒有能夠在這些村落中住上一晚。但這些詩詞依舊穿越幽幽時光隧道,仿佛成為了我對婺源記憶的一部分。
(編輯 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