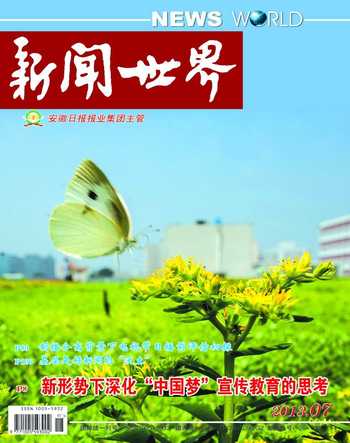丁玲編輯思想初探
柴勝松 王曉霞
【摘 要】丁玲是作家,也是編輯大家,編輯生涯跨越半個世紀。其“扶植新秀,海納百川;以筆作槍, 為文學而文學;團結作者,為人民服務”的編輯思想更是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關鍵詞】丁玲 編輯 編輯思想
丁玲,一個時刻與新中國命運交織的女性作家,一個在四萬萬同胞尚未覺醒之時,奮起抗爭的女性。丁玲是一名偉大的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用自己的文學才華豎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丁玲亦是一位偉大的編輯家,其編輯思想影響了一代中國文人的發展。
扶植新秀 海納百川
不斷發現和培養新人,為更多的懷有文學夢想的人搭建平臺,一直是丁玲編輯思想的主流。1931年,丁玲在出任《北斗》主編時,十分重視和提攜文學新人,甚至這一度成為丁玲主編《北斗》的一項重要工作。這一時期,許多“新人”的地位都是在《北斗》上確認下來的,像艾青、葛琴、楊之華等著名作家、詩人的處女作也是均在《北斗》上發表的。除此之外,《北斗》還專門設置專欄為新人提供創作園地,同時不斷給予他們創作上的指導。
在解放區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時,丁玲繼續堅持了這一編輯思想,在其主編不足7個月的時間內,發表了三十幾位新作家的處女作和成名作,這在報紙的文藝副刊史上是不多見的。注重培養新人,作為丁玲編輯思想的重要部分自始至終貫徹于丁玲的編輯生涯。
大度和寬容是丁玲編輯思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編輯應該具有廣闊的胸襟,可以胸懷萬物,容納百川。在丁玲早期的創作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丁玲獨特的女性獨立意識和對當時封建殘余禮教的反抗痕跡。在解放區,其創作的《“三八節”有感》和《在醫院中》中,我們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丁玲骨子里的獨立意識和自由意識。
丁玲在編輯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時,不同作家的作品在雜志中廣泛發表,既有魯迅、瞿秋白、田漢等左翼戰士,也有葉圣陶、冰心、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等左翼的朋友或與左翼不無沖突的自由派作家。在《北斗》發表的作品中,既有時代精神強烈的沉雄之作,也有描繪生活感觸的淡雅之筆。丁玲的大度與寬容還表現在她主編的“文藝”欄能夠容納不同思想、不同風格的文學創作,其所營造的自由討論、平等交流的藝術氣氛,以及通過征求讀者意見來決定辦報取向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藝”欄的發展。
以筆作槍 為文學而文學
作為一個在五四時期獨立成長起來的新女性,丁玲一直沒有失去自己的主體意識。“我們現在要群眾化,不是把我們變成與老百姓一樣,不是要我們跟著他們走,是要使群眾在我們的影響和領導之下,組織起來,走向抗戰的路,建國的路。”這種自覺的主體意識與對文藝功能的清醒判斷,使其在當時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中仍堅持著對文藝藝術性的執著追求。
辦刊自由,為文學而文學。丁玲晚年創立的《中國》,便是為文學爭取發展空間的一次嘗試。創刊階段請求銀行貸款,刊物及其它出版物一律自負盈虧,不要國家補貼,并考慮實行集資認股等,這在當時是“旁逸斜出”的,但這卻為刊物爭取了很大的自主權。
時刻注重文藝的政治性追求是丁玲編輯思想中可以說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地方。早在《紅黑》雜志這一“出版的夢”破滅時,丁玲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作為編輯,也應有和政治家一樣的從政治上看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文學有時候也具有流派政治的問題,文學期刊對于反映民主疾苦,喚起民族斗志也具有非同一般的進步意義。
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的丁玲一時間去除了身上所有的自由主義的痕跡,開始默默為革命而奉獻自己的微薄之力。在編輯《北斗》的期間和參加左聯其他活動的過程中,丁玲也逐漸加深了對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認識到自己過去那種“單干”方式是不可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對于個人奮斗與社會革命、寫作與其他工作的關系,丁玲都有了新的認識:“我覺得單寫小說是不夠的,我要腳踏實地地干真的革命,我把社會看作一架機器,革命是這機器的動力。像這機器的一個齒輪那樣工作,是必要的。”這一編輯思想,也在這一階段形成了雛形,即文藝與政治密不可分,文藝是政治的武器。
團結作者 為人民服務
注意稿件的社會功能,是丁玲貫徹黨“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在編輯領域的特色表現。丁玲在擔任《解放日報》文藝欄主編時,《解放日報》就刊登了不少涉及解放區包辦婚姻、干部修養、兒童教育、民主與建設、知識分子情調、官僚主義、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等諸多問題的稿件。一時間“文藝欄”成為了當時“解放區生活的一面鏡子”。
1951年,丁玲在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的發表《為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斗性而斗爭》一文,我們同樣也可以感受到丁玲這一編輯思想:“編輯要時刻心系人民群眾”、“聯系群眾,是刊物的首要的任務”、“編輯應該把今天人民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提到我們刊物上來,站在人民的立場,用新的人生觀去分析,以教育人民”等等。
也許是飽嘗艱難困苦,深知宗派主義對文學發展的不利影響,晚年的丁玲一直倡導文學界的大團結。她更希望文學界能呈現一派團結共進的局面,因而不懼以一己之力極力營建。《中國》的創辦便是其為實現文學界的大團結,推動文學的良性發展做出的最后努力。
在1985年1月出版的《中國》創刊號中,丁玲用期刊的性質再次強調了這一編輯思想:“我們辦的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數人的刊物。”、“我們辦的雙月刊《中國》認真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搞宗派門戶,不排斥任何人。老作家,老詩人,現代派的作品,我們都發表。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革命新文學優良傳統的同時,有選擇地介紹其它各種現代形勢和各種流派,只要他們確有藝術特色,不但無害于讀者,還能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
兼收并蓄,打破宗派門戶,容納多種藝術風格,丁玲,終其一生都在實踐自己的文學理想。《中國》是她最后的努力,是她晚年編輯思想、文學理想的實現。
作為作家,逝去的丁玲留給我們太多遺憾;但是作為編輯,其卻留給了我們不盡的財富。縱觀丁玲的一生,其編輯生涯跨越了整整半個世紀,盡管每一次出任主編的時間都很短,但其留給我們的編輯思想至今都有著非凡的意義。
(作者:柴勝松,皖江晚報記者;王曉霞,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傳播學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