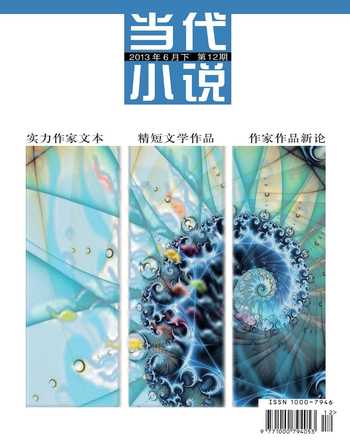城里城外
張凌云
一
“圍在城外的想沖進去,圍在城里的想逃出來”,這是錢鐘書《圍城》中一段著名的話。“圍城”也成為一種象征,其內涵早已遠超原本狹義所指的婚姻,而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成了一個眾口相傳的俗語。
現在,我在周而復始的循環往復中,真實地做著城里城外的游戲,在生命中將圍城的定義反復詮釋。
工作在一座城,家在另一座城。工作是一座大城,家是一座小城。周五從大城回到小城,周日從小城奔赴大城。我在兩座城之間不停做著鐘擺,一會城里,一會城外,在城里,也在城外,小城是大城的城外,大城亦是小城的城外。高速公路把時間變得很短,大部分時間都屬于城里,只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屬于城外。
我曾經無比眷念那座大城。那里曾經承載著我的青春和夢想。那里怒放著那時花開的大學季節。從懵懂青澀的鄉下少年成為天之驕子的那一刻起,我便與那座大城結下了不解的人生之緣。四年匆遽的時光并不能抹去我濃郁的大城情結,相反,在歲月的積淀中它明亮如夜航時的燈塔,在失意或挫折的時候,在消沉或倦怠的時候,我每每會想起那個夢開始的地方。假如一切重新來過,或許,假如我仍然呆在那座城市,一切將會如何演繹,將會出現怎樣意味深長的變化?
我曾經早已厭倦那座小城。當年大學畢業,從大城分配到小城的那一刻起,我不曾料到,旅途中會留下如此漫長的定格。這里,風平浪靜,安謐整潔,不會有拼搏夢想的波瀾壯闊,也沒有人生遭際的大開大闔,每日只需劃出機械的軌道,便可過上富足無憂的生活。光陰的模板日復一日,十幾年間,曾經風華正茂的學子竟似一位心將退休的老人。但表面的平靜擋不住骨里的桀驁,始終有一種愿望在上升,上升,沖破這樊籠,打破這微瀾的死水,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二
時光的年輪藏著不可言說的密碼。我從大城飄到小城,又從小城再回到大城。陌生的道路在腳下重新拼接,關于大城失落的記憶又變成熟稔,通衢小巷,在思索的丈量下恢復出過去的模樣,并順著時代的節拍與周圍的建筑風景一起拔節生長。
然而,當度過了最初的興奮期,在嘈雜的時空部落里作為蟻族而忙碌打拼時,我磨平了理想的鋒芒,忘記了曾經的憂傷,我恢復了一個也許一開始不曾離開就會存在的角色,掌聲和榮耀并不屬于你,欽慕和嫉妒也不屬于你,你和這個城市的數百萬生靈并無二致,平凡普通而不引人注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為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摸爬滾打。你并沒有因為大城的存在而使自己多上一圈光環,你只是日益龐大的城市機器里一顆最普通的螺絲釘,僅此而已。
所以,當我一次次隨著周末的大巴,返回我戶籍所在地的那座小城時,我必須重新審視考量這座在名義上依然屬于我的城市。相比大城,小城是清靜的,整飾的,沒有大城的喧囂與擁堵,也沒有大城的繁華與蕪雜。你可以說它沒有大城的視野空間,但它卻有著大城不具備的宜居從容。如果說大城是花園里眾人聚焦的牡丹芍藥,小城則如水濱靜靜綻放的一朵野花,它安詳地擁有自己的美麗,在清寧中享受時光的流逝。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我在城里看世界,世界也在遠方不動聲色地看著我。
城市是什么,大城小城又是什么?城市是我們相對鄉村的棲身之所,城市是我們離開故土的尋常選擇,城市是我們追逐繁華,追求夢想的地方,城市是我們的狂歡與自豪、感傷與頹唐相互交集的地方,城市也是我們的個性凸顯人格異化,走向自我的另一面甚至反面的地方。
人,應當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如是說。這個繽紛繁麗的世界,選擇自己的詩意棲居并不容易。城市亦或鄉村,大城亦或小城,種種的選擇糾結著復雜的生存構圖,城里城外,是一道難以言盡的歌德巴赫猜想。
三
雨果曾經說,“城市會使人變得兇殘,因為它使人腐化墮落。”也許這句話有些偏激,但某種意義上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中心存在的種種弊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東方還是西方,的確有不少人身體力行,以各種方式嘗試著逃離城市,回歸鄉村的舉動。
梭羅是一個著名的范例。——“文明改善了人類的房屋,但并沒有同時改善居住在房屋里的人”,他在遠離城市的瓦爾登湖邊搭了一間小屋,獨自居住了兩年零兩個月。而這也極大地侵害了他的健康,他成為了一位殉道者。以梭羅為榜樣的葦岸放棄了北京的大都市生活,選擇了昌平小縣去觀察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同樣成為了殉道者。葦岸的朋友,詩人黑大春久居北京城,但他在當時荒涼的圓明園一帶過著結廬而居的生活,是一個城市里的隱居者。
如上,無論城市鄉村,小城大城,我們的棲居之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內心存在怎樣的城堡,或者,是怎樣的圍城。
圍在城外的想沖進去,是因為企慕城市的繁華與光鮮,直白地講,是城市背后相應更易獲取的名利和榮耀。圍在城里的想逃出來,是因為城市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或者有些人想走一條發達的捷徑,卻發現現實遠比夢想殘酷,不管努力進取的,小心謹慎的,還是蠅營狗茍的,最后都萌生退意。這就是現實版的圍城。
而我們為之困惑,或活得不快樂的源泉,正在于我們內心有這樣一座城堡,我們人為地構筑,并不斷小心加防這樣的圍城。
地理原本沒有界限,是我們主觀地強化了城里城外,以及大城小城的分野。當作為物質阻隔的城墻幾乎不復存在,當城鄉一體化的步伐空前加快,城市與鄉村的差距日趨縮小,我們仍然在心中固執地堆砌著城堡的塊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地位身份的象征,是睥睨周圍的資本,當然,也是有著更多機會,更易走向成功的舞臺。即便作為在夾縫里生存的草根,作為一個屢遭打擊的失敗者,也會在心底涌動一種本能的自傲。城市情結,從根本上說,是等級觀念的自然延伸,是炫耀虛榮的現實載體,同時,也是失敗者尋找理由的藉口,包括殘留最后一絲尊嚴的最好偽裝。這是一座看不見的城堡,它封閉,內斂而戒備森嚴,似一口幽幽的深井,藏著變幻不定的臉譜和太多的都市欲望。
如果能推倒我們心中的城堡,掃平越筑越高的圍城,那么一切將會廓然開朗。我們到底在追求什么,想要什么?我們是在追逐自己的本心,還是讓自己的本心隨波逐流,在各種名利場的角逐中蒙蔽了暗塵,甚或迷失了方向?
“城市也認為自己是心思和機緣的造物,可是兩者都支不起城墻。你喜歡一個城,不在于它有七種或七十種奇景,只在于它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
這一瞬,我想起了卡爾維諾。
四
我用一種全新的視野去觀察,去感悟屬于自己的城里城外。
“心好像一扇厚重的城堡之門,沒有外面的鎖,只有里面的閂,別人在外面怎么使勁踹,也不如里面的人自己輕輕一撥。”一位詩人這樣說過。現在,我努力打開了那道門閂。
在高速公路飛馳的汽車上,我一遍遍欣賞著只可能屬于城外的風景。歲月更迭,春秋代序,從層巒疊嶂到一馬平川,從楊柳吐翠到寒煙生水,大自然恩賜給我們目不暇接的瑰麗長卷。我由一個普通的觀察者,漸漸成長為一位半入門的地理學者。我觀察著寧鎮丘陵的種種變化,觀察著山巒平原的界限分野,觀察著樹木花草的生長凋零,觀察著大地萬物的陰陽代謝。我發現著力與美,發現著盛與衰,發現著萬紫千紅的璀璨,發現著蕭瑟蒼涼的厚重。
我獲得了一個與城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發現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獨具的地理氣質,發現了鋼鐵水泥叢林之間存在的細微差別,盡管它們在地緣上也就相距一兩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從平原向丘陵的過渡地帶,在炎夏的視野里可能沒有區分,而在嚴冬卻井然有別。平原地區更溫和,更潤澤,即便是落葉樹,光禿中也透著一絲秀媚,譬如梧桐,葉兒要么落盡,要么泛著黃與紅的雜色。至于山,多是裹著一層常綠樹妝,如松竹之類,讓人自然聯想到南方。丘陵則呈現出另一種風貌。成排的楊樹將光禿的枝丫指向森森藍天,遠處的山巒則褪盡了綠色,披上一層青灰色的外衣,猶如一塊巨大的鐵石。若是遇到梧桐,則多見鐵繡紅的樹葉干縮成一團,卻擠在一起不肯掉下來。這些場景,像極了北方。在同樣緯度的江南,僅僅在由東向西的數十公里間,卻可欣賞到迥然有別的風景,讓人不得不感佩造化的神奇。
城外讓我想起了往事,想起了童年,想起了許多遙遠的記憶,想起了一直追尋卻未曾到達的遠方。初春,青翠一片的視野里,陽光安靜地灑落在林梢之上。暈黃的光圈,讓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獨自前往一個陌生的城市,自信,而滿懷憧憬。盛夏,從喧嚷的都市抽身而出,當蓊郁的綠樹排闥而來,當風聲和蟬鳴撲面而來,一種久違的清涼感油然而生,也許,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金秋,看層林盡染,看欒樹變幻出迷人的色彩,綿延在看不到頭的長路上,忽而心中一動,我童年的某個地方,正是夢想能在這樣的小山丘上,做著永不厭倦的游戲。殘冬,冰封的小河,高遠的天空,令我想起了家鄉的原野,表面的岑寂之下,一季季輪回著春天和希望。
所有的這些,都是久居城里的人們無法體察,無法共鳴的。城外,或者鄉村,是城市的乳娘,是城市和它的游子無論走得再遠,也會默默將之掛念,并隨時敞開懷抱歡迎歸來的地方。
五
我依然在大城和小城之間做著規律的鐘擺。
不過,我的心境已經平和,我不再浮燥不安,焦慮彷徨,我開始學會用一個支點,搭建城與城的平衡,搭建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這個支點,自然是一顆平靜的心。這個世界,你必須知道自己真正具備的東西,同時也能夠得到的東西。你得學會選擇,學習放棄,學會做人生的減法。攀比可笑而不明智,恰如一根盤旋而上的凌霄花,硬要纏上那并不存在的高大喬木。許多時候,努力并不能獲取相應的回報,各種無謂的犧牲,侵蝕了我們的心智,鈍化了我們的銳氣,使我們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在一地雞毛間看著夢想隨風飄散。
我學會寬容和汲取。我平等地看待身邊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個村落,感謝它們對我的包容,同時,也汲取著它們給我的營養。它們是我,也是眾人的母體,我只是一個渺小的孩子,我無權挑剔,或者報怨什么,我能做的應當是學會遮蔽風雨,自由健康地成長。
我愉快接受著大城小城不同的賜予。在大城,我站在一個更高的視域和更廣的空間,盡可能融入這個時代。我珍惜眼前的一切,努力工作,將挑戰自我當作修復理想的盛大狂歡。在小城,我享受著時光的寧靜和家人的團聚,在閑暇時,在散步中,認真作著生活哲學的思辨,并寫下各種各樣的文字,那是屬于我的最可寶貴的財富。
心中的柏林墻已經拆除。掃蕩了所有的城里城外,大城小城的阻礙,今天,未來,無論走到哪里,走向哪里,我將自由馳騁在心靈的牧場上。那里一片豐饒,生長著從未有過的嶄新希望。
責任編輯:小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