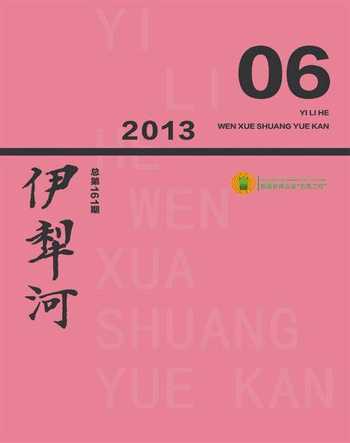伊犁紀行(六章)
李勇
汗血寶馬
馬的種族中的寵幸。梟雄的坐騎。烽火的種子,戰爭的誘因。一團團奔跑的烈焰,燃燒在典籍里。汗血,綻開奇幻的花,傳遞——
速度與激情;榮耀和傳奇。
阿哈爾捷金,最純正的貴族血統,可以追溯到異域的土庫曼斯坦。鎮國之寶,國徽和幣面上驕傲的圖案。古老的一脈,逶迤三千多年。
哦,神秘的家譜,游走在漫漶的歷史中,分蘗的一支,遺落在蒼茫的天山腳下,成為烏孫部落的驕傲。
武帝尚武,張騫西使;可汗征伐,鐵蹄拓疆;河西走廊的風緊,大宛國的命懸……
哦,天縱驕子,在西域的史冊中馳騁,汗和血演繹傳說;竹簡或者羊皮卷上銘記史話。
哦,珍稀貴族,悄然現身,又神秘消失,像草原上捉摸不定的風。
在西天山,在昭蘇大草原,在種馬場,它們恍如從傳說中被贖回現實,帶著遠古的氣息。
棗紅、純白、黑褐、淡金……神話賜予的色澤;高大、英武、神氣、敏捷,上蒼成就的杰作。毛色細膩,皮質油亮,在陽光下如綢緞般光滑,透著健康和活力;曲線優美,身姿輕盈,修長的四肢若靈巧地鼓槌,隨時準備擂響大地;鬃毛舞動烈烈西風,汗水蒸騰,氤氳了天邊的霞彩。血色攫取一叢叢閃電的心跳。
我面前的它們,亢奮,焦躁,不時用前蹄刨著地面,揚蹄長嘶的剎那,從它們的眼眸中,我讀出了火種點燃的激情,仿佛昔日的榮耀和輝煌又重新回到了它們的身上,恰如驗證一道神秘的出征指令。
——哦,王者歸來,它們期待的矯健英武的騎手,如今都在哪里?!
草原石人
或閉眼沉思,或圓睜怒目,或抿唇頷首,或遠眺發呆,輪廓逼真,線條鮮明……
這些石人,散布在昭蘇草原,蒼茫了整個亞歐草原。
它們有一致的方向——面向東方。為的是從太陽升起的地方重新溫習生命鮮活的意識,汲取源源不竭的力量?
它們有謎一般的身世——從何而來,接受了誰的旨意,以這些形態守望著青了泛黃、黃了泛青的草原?
神秘的源頭,只有歲月的風聲,順流而下……
晦暗的史冊上,突厥汗國游走于《北史》、《隋書》的文字間,游走于西域大地。馬蹄丈量疆域,箭鏃劃定屬地,刀劍角力權威。鐵流滾滾,煙塵彌漫。二百八十多個春秋,演繹一個帝國的興盛和衰亡。
塵埃落定。馬背上的雄心灰飛煙滅。草原依舊。
逝去的亡靈,在薩滿巫師的口中超度,陰陽兩界的溝通和詮釋,惟有雕鑿的石人為證。
在昭蘇草原舒展的背景下,這些形態酷肖的石人,櫛風沐雨,孤單、肅穆,突兀成詭異的符號。
哦,神奇的遺址,生命的磁場,冥冥中還在傳遞能量——
延續自然的古老輪回,炫耀曾經的顯赫戰功,昭示權力和尊嚴的威儀,寄托眷戀家園的情愫,祈福部族繁衍和興旺的愿景,祭拜先祖和英雄的莊重儀式……
輕撫這些沉寂的石人,不堪歷史的冰冷;觸摸這些鑿刻的印痕,猶感生命的犀利!
“巴力巴力!”,“巴力巴力!”
神秘的源頭,只有歲月的風聲,溯流而下……
細君公主
一曲《悲愁歌》,瘦了歸鄉路。
武帝霸業,大風起兮;漢室和親,權謀通變。一個王朝江山社稷的重量,忽然間就壓在了一個纖弱女子的肩上!
漢室、烏孫、匈奴,三方角力,兩相聯合。權力的籌碼,制衡的秘器,穩固大漢家業的基石,竟以一個芳齡女子一生的幸福作為抵押,來換取武帝經國大業的實現!
是細君的榮幸,還是漢室的悲哀?
金枝玉葉的女子,帶著贖罪的復雜心情,開啟了一條萬里和親之路。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五載春秋,不通語言,遷就習俗,忍辱負重兩嫁烏孫王,成為祖孫兩任夫人。
哦,細君,細君,故里成夢,惟心傷悲夜難寐——
心曲托付琵琶,思念遙寄黃鵠。
一縷香魂呵,最終枯萎在烏孫古國的夏塔草原;幾抔黃土喲,聚攏最后的歸宿。
流水白云為知音,綠草鮮花作芳鄰。
而不到一年,一名叫解憂的漢室女子,為了漢家大業,又一次踏上了和細君相同的路。一條長長的灑滿血淚的和親之路。
解憂靈犀,可知孤苦一生無以為伴長眠塞外的細君公主,有夢相托乎?
喀拉峻
莽莽蒼蒼的草原。五花芳甸。王的游牧地。離天堂很近。
雨在前面帶路,風在后面推搡。河水的弦子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捻著。旋轉的山路,每一次暈眩,都是一輪美的歷險。崎嶇慣為平坦鋪墊,不經煉獄之苦焉能接近天堂?
直到躍上高臺,躍入喀拉峻的草海——
總以為人跡罕至之地,美無人認領,其實,美早已名花有主——
烏孫王的御用草場,如今是哈薩克、柯爾克孜牧民的夏牧場。
天山的臂彎下,這一片懸空的遼闊草原,坦蕩如砥,氈房點點,畜群如繡,沒有什么秘密可以藏住。
視野在這里抻長,胸襟在這里放大。
綿延的雪峰是屏風。變幻的流云是彩帶。杉林墨綠深沉的心事很遙遠。鷹是天空的畫師,它努力在盤旋中領受神諭劃出完美的曲線并隨時準備讓天空帶走。
馬蹄嘚嘚,有少年策馬馳過,紫外線親吻的臉色,黧黑,健康;炊煙裊裊,圍欄前的狗吠傳得很遠,換回幾聲慵懶的牛哞。
草色入簾青,眼簾擋不住洶涌的青色;山光聚夕輝,柔和的光線給這里涂抹上一層塵世的溫馨。身處此境,無蝸居陋室之局促,有高蹈穹廬之曠達。
草是這里真正的主角。紫花苜蓿、大麥草、燕麥草、蒲公英、狗尾巴草……上百種牧草仿佛舉行聚會,繁茂,奢華,盛大,雜色掩映其間,如毯,如錦,如一個人獨處時無邊地緬想。它們密集、勢眾,以集團軍的力量占領每一處平緩的山巒、溝谷,攬進畜群,泊起氈房,搜集雨水、陽光和傳說。
五花芳甸。王的游牧地。離天堂很近。
風吹草低,不諳世事的羊們,從草浪中抬起頭,用純凈無辜的眼神,打量冒然闖入的我們。
夏 塔
隘口。古道。秘境。
一條細若游絲的路,在西天山的皺褶間攀援,穿針走線,在絕壁上飄蕩、延伸。
夏塔,蒙古語“沙圖阿滿”的轉音,階梯之意——是通向天上之山的梯子么?
仿佛喧嘩之后的沉寂,盛開之后的衰敗。歲月回眸,往事幽暗。
驛站。墓群。古城。石人。歷史的遺物,泊進廢棄的時光。
絲綢之路,在史冊上蜿蜒。一根敏感的神經,竟會藏在如此遙遠幽僻之處!
險峻的通道,貌似去往天堂的窄門,伸向天上之山的脊梁——雪峰凜然的木札爾特達坂。哦,“弓月道”,唐玄奘西行翻越“凌山”之徑,連接南疆和北疆的重要孔道——夏塔古道喲!
幾十公里的狹長畫廊,獻出驚世美景,令人目不暇接。兩岸重巒疊嶂,狀如翠屏。仰望雪山,云纏煙繞,俯視河谷,漫坡蒼翠,谷底雜花生樹,綠葉繁花,漿果滿枝。白浪翻滾的夏塔河奔騰其間,如門童,如向導,揖客引路。牛在山坡吃草,羊在峭壁跳躍。風雨剝蝕的木屋如褪色的童話。在狹窄的山間彎道,牧人趕著畜群和我們豁然相遇……他們或許就是赫赫有名的烏孫和突厥的后裔?
夏塔,莽闊的天山深處的一條長長的峽谷,循著階梯來到這里的人,恍如處在去往“天堂”的一個驛站。古道又像一柄彎刀砍向木札爾特達坂,但刀刃太短,沒有貫通。或許,這是上帝隨手留下的一個小小的瑕疵,又似有意制造的一個障礙——
前路漫漫,充滿兇險。真心取經的人,都將通過這條古道修成正果;那些抽身而返、淺嘗輒止的人,就讓他們回到喧鬧、舒適的世俗生活中去吧。
詩人安鴻毅
察布查爾縣城。白楊樹下的寧靜院落。
沙瓤西瓜。錫伯大餅。剛出鍋的冒著熱氣的玉米棒子。我們圍坐在一張小木桌前。
他懷里抱著一把曼陀鈴,談南京大學期間的往事,談北京通州的生活,談收藏、繪畫,間或嫻熟地彈撥一段曲子助興。我們聽。
“回思往事,恍如流螢。”我們捕捉流螢拖曳過的余光。
在畫室,我們看他的畫作。四尺或者六尺的宣紙上,他畫《釋迦摩尼本生像》、《羅摩衍那》、《衛鞅夫人》、《漢唐仕女》、《虢國夫人春游圖》,也畫《香妃》、《弘一法師》、《荀慧生》、《胡風像》、《松尾芭蕉》;畫《古西夏》、《敦煌》、《徽班進京》、《巴米揚大佛》,也畫《風景》、《鳥巢》、《卡提布拉克的秋天》、《威海·月色之美》……黑、紅、黃、藍、粉……抽象的線條,寫意的筆法;國畫的意境,油畫的神韻;鮮明的色彩凸顯充沛的情感,大膽的布局張揚亢奮的個性。如曝如寒,淋漓酣暢。
我們看他的收藏:徐悲鴻的《嘉陵江邊的篝火》、吳作人的《八達嶺》、潘玉良的《自畫像》、吳冠中的速寫、洛夫的書法……
他游于藝——詩、書、畫、樂;他心有所托——“愛情、生命和生——死/我撫摸到了心的邊緣/寂寞、歌、深淵中的深淵/火/我撫摸到了拯救的邊緣……”
故鄉是根。療傷之所。傷,來自看不見的內心,來自瘋狂旋轉的頭顱!“我的宇宙多么混亂——我的愛多么混亂/我的沉思多么混亂”;“我遠離人群——人群遠離人群/我拋棄城市——我向災難開一次槍……”常年漂泊,他感到累,從車水馬龍的北京抽身而返,回到伊犁河畔,錫伯風情的家鄉,好似水手回到港灣。
“水邊堪小立,岸上好長吟。”他是畫家、收藏家,但本性是詩人。他不乏對生命終極的表白:“如果死亡通過了美/我會消失一千次/它們注入我內心的節奏/風,草原,穿過平原的路 我的身體”。
無疑,他的畫就是他心境的寫生;他的詩就是他情感的剖白——
“一切都剛誕生——/鮮花和芳草/人的命運/我迷住了自己/深厚 寂寞 僥幸/我迷住了它們/露珠和俠客 植物和云彩——/成熟的吻/我在干干凈凈的文字里/行走如魚/我剛剛迷住了門/就愛上了它的豐盈/我剛剛迷住了死/我就幸運地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