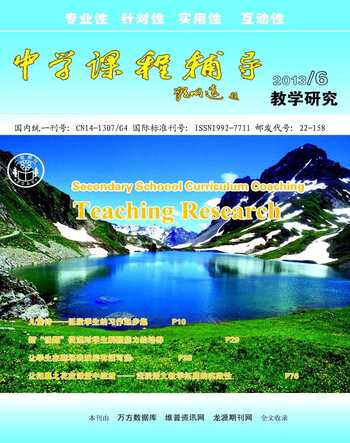由《孔乙己》中的“笑”說開去
王恩波
魯迅的小說《孔乙己》,整體氛圍本來極為壓抑,有了笑聲便特別刺耳,甚或讓人憤恨至絕望。這些貫穿全文的“笑聲”是作者匠心獨運的藝術,頗值得研究。
在小說里,都有哪些人在“笑”孔乙己,又為什么要“笑”他呢?
首先要說的是咸亨酒店的掌柜。這掌柜本是一副“兇臉孔”,可是見了孔乙己,就每每故意問他的丑事,引人發笑,即使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也不放過。這樣,在酒店掌柜的周圍就是一群笑臉了。然而掌柜緣何要取笑孔乙己呢?文中交代,取笑他是為了“引人發笑”。孔乙己同其他短衣幫一樣,是花錢買酒的顧客,為什么待遇就不同呢?對于掌柜來說,除了小市民的庸俗、刻薄之外,欺視孔乙己罷了。穿長衫的主顧是不敢取笑的;短衣幫呢,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和收入,而且恐怕還很有一些力氣。得罪短衣幫除了生意上受損失外,還有潛在的引發沖突的危險。相比較而言,孔乙己就很可欺了。他只是有了錢才來買酒喝,不能算常客,有時還要欠賬,況且十九文銅錢于經濟無損。最重要的是孔乙己軟弱可欺,軟弱到連為自己狡辯都不會,所以只能受“欺視”了。掌柜盡管不是地位很高,但也算的上是中間階層了(至少在小說中是),欺負弱小或許是彼時這類市民的本性吧。
“我”也會跟著笑幾聲。但都是為了排解無聊,“附和”著笑的。這“附和”便有些講究。首先是附和誰,當然是要看掌柜的臉色。《紅樓夢》里賈母一哭,媳婦丫鬟都必須要哭的,察言觀色,順遂主人心意的做法駐在每個中國人的根里。“我”自然要討好掌柜,保住自己的職務,至少也要做到“識臉色”吧。當然也附和眾人,聊以輕松。
尤為刺耳的是短衣幫的笑。這是一群做工的人,繁重的勞動,貧困的生活和低賤的地位使他們一旦“散了工”,閑暇下來,就會極度的空虛無聊。這類人的特性是喜好聚伙找樂子。習以為常之后,就會麻木。這種情形下,出風頭挑事的有之,圍觀“打醬油”的有之。何況孔乙己在他們眼中是不倫不類的人,取笑他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但是有一點,因為孔乙己“讀過書”,他們絕不會視孔乙己為幾類,所以他們對孔乙己是發自內心的排斥。對孔乙己的遭難,只是漠然而已。
至于那些長衫客,自然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隨眾人哄笑,但是在心里對孔乙己的鄙視和冷笑是可以想見的。
孔乙己一出現,總是引來陣陣哄笑。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可笑之處,該不該笑呢?
僅從小說中看,孔乙己確有可笑之處:
笑他偷竊挨打,笑他說話迂腐,笑他雖然讀書卻無以進學,笑他無謀生手段卻又好喝懶做,笑他性情軟弱、遭人欺負而無力反抗,更笑他身為下賤卻自命清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然孔乙己身上笑點多多,想讓人不去笑他都是難事。而孔乙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卻是出奇的好,眾人的譏笑固然使他難堪,但是要說他是被“笑死”的,卻也言過其實。
其實,究其根源,還應該是性格決定命運。
先來看看“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句話。“唯一”,說明是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在今天讀書無用考試誤人的論調也時而有之,和諧社會中不和諧的事件也時而有之,無論多么優越的社會制度也救不了孔乙己這樣的人。也就是說,社會形態的土壤可以引導群體意識,卻不能決定個體的命運走向。孔乙己在當時也只是個特例而已。在那時也有積極追求個人進步的人和尋求社會變革的人。所以不能把個人性格的形成都歸罪于制度和社會的弊端。現代科學還認為人的性格跟其血型有關呢。但是人的命運發展和性格有關卻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孔乙己是一個特殊的人,就會有獨特的性格。不妨設問,孔乙己自己認為應該是“站著喝酒”的人,還是“穿長衫”的人呢?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說:那些“站著喝酒”與“穿長衫”的人,誰對孔乙己的認同感更多一些?
前一種問法較易回答,孔乙己“站著喝酒”是為經濟條件所迫,他放不下的是“穿長衫”的書生裝,因為這裝束意味著他是文化人——和做工的粗人不同,至少接近上流社會。即使不具實在的地位,也要擺擺身份架子。這是他的虛榮心在作怪。
對于第二種問法,我認為“穿長衫”的人對孔乙己的認同感更多一些。短衣幫對孔乙己只有無情的嘲笑,連對他的被打折腿和不知死活都表現得異常的漠不關心,可見短衣幫對孔乙己是絕對的排斥,絕無可能把孔乙己歸在他們的陣營中。而“穿長衫”的對孔乙己則表現出一定的認同感。他們肯定孔乙己“讀過書”的身份,賞識他的“一筆好字”,為他提供生活來源。只是因為孔乙己自己太不爭氣,不僅不求上進,還不顧圣人之道,偷竊他的雇主,免不了要受到責罰。今天路人見到小偷尚且切齒,何況丁舉人之流也算照顧了孔乙己的生計,可是孔乙己把仁、義、禮、智、信的圣人之訓全都違背了,這一番責打便不會留情。是否可以說,短衣幫嘲弄的是孔乙己的落魄,而丁舉人之打,卻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呢。孔乙己是讀書人的敗類,做不通學問,連誠實守信的基本準則都丟了。統而言之,孔乙己的悲劇源于他個人的不爭氣,眾人所笑,也大都是笑他的性格和為人而已。
孔乙己是那個時代的多余人,受人嘲笑是免不了的。然而作者對他所塑造的這個形象又是什么態度呢?
首先,我認為作者絕沒有嘲笑之意,而是在冷峻的雕刻著一尊塑像,背景是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科舉制度土壤下的長衫客和短衣幫。他們齊聚咸亨酒店,而柜臺外面就是孔乙己的雕像。那是一尊沒有血肉的木塑,線條深刻而又生硬。這尊像的形是孔乙己,靈卻是作者自己。魯迅是最善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孔乙己的身上,總會有魯迅自己的影子。
魯迅是那個時期比較早覺醒的人之一,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而深深的憂慮著。在寫作《孔乙己》的一九一八年,社會動蕩不堪,那是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手握重兵、有實際權力和能力的人都在搶地盤、營私利,國外勢力也在不斷加深對中國的蠶食。這時的魯迅不過一介書生,徒懷濟世救民的理想,可是面對殘酷的現實,個人微弱之力實在難有作為。所以他寫《孔乙己》,除了與病態的社會戰斗以拯救世人的靈魂外,也反映出文人報國的無奈與艱辛。“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這是魯迅在《新生》雜志夭折之后的感受。魯迅還說“此后,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期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沉淪了一段時間后,魯迅感到“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于是開始寫文章,但“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而悲哀的原因是“一間鐵屋子里熟睡的人,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悲哀,而有人大嚷起來,驚起幾個較為清醒的人,這些不幸的少數者就要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魯迅正是少數遭受苦楚的人之一,內心有著深深的憂慮與悲哀。如孔乙己這般的不可救藥,還有什么改變的希望可言?只有將求索路上深深的挫折感借由孔乙己表現出來而已。所以我說,《孔乙己》的主題,也要從作者身上發掘,對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毫無意義,要反映的正是作者心中責任愈大愈覺艱難的感慨,以及文人救國力所不逮的艱辛與無奈。
孔乙己式的人物于人無爭,于社會卻是大害。今天的教育要培養出什么樣的人來,當像魯迅一樣警醒,不重實踐,紙上談兵,弄虛作假……種種不良風氣都該改一改了。
(作者單位:福建省晉江市南僑中學 36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