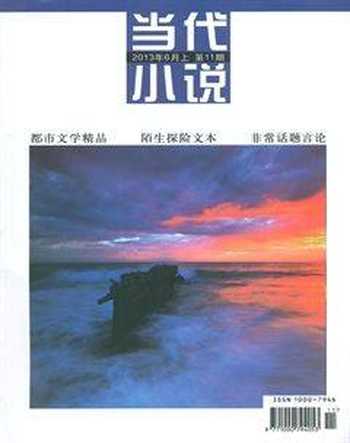認干娘
李立泰
小時候,除夕娘領我認干娘。
干娘是家南坑邊小場院兒的石磙。
那時不知道為啥認干娘,有娘再認個石頭磙子干嘛?娘不叫瞎問,只管上供磕頭就行。
除夕夜,家家“嘭啪”的放鞭炮燒紙上供,供的有列祖列宗、老天爺爺、財神爺、灶王爺灶王奶奶,請先人和各路神仙保佑我們來年有好收成,保佑全家平安,保佑老人身體健康,孩子有個好的前程。
供品有炸丸子、藕夾子、方豬肉、雞,好像沒供豬頭。母親煮好了餃子,盛在三個碗里也放在供桌上,父親在天院里老天爺爺供前燒紙,屋里供桌前燒紙,磕頭。
然后母親提著提籃,籃里放一碗餃子,一雙筷子,一打燒紙,領我去認干娘。
萬家燈火映照鮮紅的春聯。幾乎家家拉天燈,天燈就是自制的燈籠,也有玻璃罩子燈,在院子樹上拴上滑車兒,拉到樹頂。天燈上還拴幾枝松樹枝,寓意松柏長青的意思。伴隨鞭炮的炸響,全村過年的喜慶氣氛開了鍋。沿途遇上好幾家人提著供品互相上供的。
我跟母親來到小場院兒,這兒黑乎乎的,站立著幾棵高大的楊樹挺瘆人,我頭發根子挓挲起來。
母親領我走到大石磙跟前,放下提籃,供奉好餃子,燒紙。我給石磙干娘磕頭。娘念念有詞,我忘記娘說的內容了。
自從認石磙干娘,我對石磙重視起來。后來上學了,路過小場院兒,我就給干娘行注目禮,有時走過去看看干娘身邊干凈嗎。若有雜草、柴火、磚塊兒啥臟東西我就拾掇了。叫干娘身邊利利索索。
為什么認干娘是大了聽娘說的。因為在我前邊有個姐姐,一歲多生病,買不起藥喂她,扔了。扔了就是死了。扔到家北破窯碴子里。母親失去頭生女兒的悲傷,揪心疼,母親撕心裂肺地哭。她好多天吃不下飯,瘦得走路都沒勁兒。
為了叫我長得壯,就認個干娘保佑我,和母親一起護著我茁壯成長。
所以我對干娘頗尊重,年年除夕夜去給干娘上供,燒紙錢、磕頭,愿干娘顯靈保佑母親和我及全家平安。這項儀式一直持續到生活困難時期的三年大饑荒。
大饑荒最殘酷那年,過年吃不上餃子,也穿不上新棉襖,沒錢買鞭炮,全村死氣沉沉,幾乎沒有鞭炮聲,沒有歡聲笑語,人們沒勁兒家家戶戶轉悠著磕頭了。
就是那年大年初一早晨,公社書記還把我村全體社員集合到戲園子(公社劇場)里開會。
公社書記穿著皮領子大衣,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仍高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歲!”
社員們無精打采,大家穿得破破爛爛的像群逃荒的災民,全村社員就我院中一位剛結婚的新媳婦嬸子穿了件新棉襖。
公社書記不高興了,說大家沒有大躍進的樣子,沒干勁,沒精神,不像大躍進時代的公社社員。他唱高調:過了臘月二十九,吃了餃子就動手!他不讓社員們休息天,全部攆到地里干活。
天寒地凍、冰天雪地大過年的能干什么活啊?!就是叫你活受罪。
北京“中央七千人大會”后,糾“五風”,因為他以刮五風搞女人名聞全縣,把他弄到縣獸醫站指導優良豬配種去了。
那年沒給干娘上供,但我初一早晨跟娘說,去看看干娘。我走到小場院兒,大隊副書記的兒子正耀武揚威地騎在干娘身上和幾個隊干部的孩子做游戲。他們吃得五飽六足的自在。
我們雖然挨餓,吃不飽穿不暖,但要保持我和干娘的尊嚴。
我氣不打一處來,大喝一聲:下來!
這群大小隊干部的孩子吃得雖不白白胖胖,但面色紅潤。
他們的爹貪污隊里糧食,能吃凈面干糧,在學校里屙的屎是黃色的,就是鐵證!我們社員的孩子心里正有氣。
他騎在石磙上置若罔聞,沒下來的意思,根本沒把我的命令當回事。
我上去抓住他:下來!沒聽見我喊你!一家伙把他拽下來。
那家伙兒“哇”的哭了。
小孩子跑著散去,有個告訴了我母親。
母親說我闖禍了!拉我給大隊副書記賠不是。
我說:娘,他騎我娘。沒理。我不去。那次沒聽娘的話,惹娘生氣了。
娘自己去書記家賠禮道歉。咱得罪了書記有好果子吃?你考學他不說好話能考上嗎?母親自己去的。給書記說我怕孩子騎石磙冰涼,凍著。立泰不懂事,態度不好,心是好心。
書記還是說得不錯,是人話,小孩的事,沒咱大人的事,不用管他們。
不過糾“五風”書記因為貪污盜竊經濟問題下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