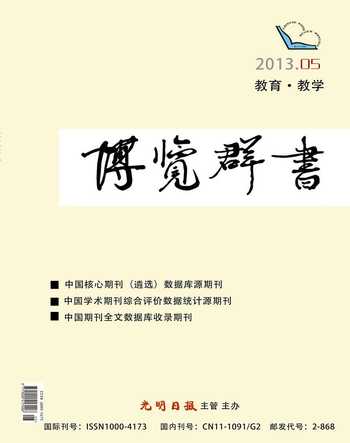劉慶邦《神木》的“審丑”藝術探微
馮琦
摘 要:劉慶邦《神木》將形式丑和內容丑完美結合,在美與丑的辯證關系中巧妙地實現美丑轉化,作品閃爍著神性指引和人性希冀的火光。從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四個方面觀之,劉慶邦《神木》表現出的審丑藝術,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劉慶邦;神木;審丑特質;審美轉化;審美價值
“短篇小說之王”劉慶邦被親切地稱為“民間代言人”,他是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煤礦題材小說鐘情于“審丑”,最具代表性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中篇小說《神木》。這部作品曾獲得“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多項殊榮。而“丑”作為與“優美”、“崇高”并列的審美范疇,并非一種客觀的物理存在,而是一個“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它有一種‘意義的豐滿,是在審美活動中生成的”。正如葛洪在《抱樸子·博喻》所言,“貴珠出于賤蚌,美玉出于丑璞”,丑給人帶來意義的豐滿之感,在一定程度上比美更富有表現力。
一、《神木》中丑的審美特質
(一)形式丑:底層的符號
張法和王旭曉在《美學原理》中提到:“形式是對正常事物的偏離或者變形。”形式丑往往會與外形丑相聯系,這種丑不涉及精神丑,是感性的認識。《神木》中人物形象來自底層,他們衣衫襤褸,灰頭土臉。宋金明的道具,“一個用塑料蛇皮袋子裝著的鋪蓋卷兒,一只式樣過時的、壞了拉鏈的人造革提兜。提兜的上口露出一條毛巾,毛巾贓物得有些發黑,半截在提兜里,半截在提兜外耷拉著。”這一段描寫,讓讀者在臟污的行李中感受到了形式丑。作品中這樣的描寫不勝枚舉,作者通過感性材料形成形式丑,這個層面的丑是底層人民的符號。
(二)內容丑:人性惡的咒語
波德萊爾《惡之花》對社會的丑惡極盡描寫之能,從惡中提取美,毫不留情地揭露社會的陰暗,詩中充斥著腐尸、蛆蟲、毒蛇等令人作嘔的意象,他曾說:“我的靈魂,像沒有桅桿的破船,在丑惡天涯的海上飄蕩顛簸!”[2]波德萊爾可謂是西方現代丑學、丑藝術的先聲。《神木》中作者將丑的事物無所避諱地一一呈示出來,盡其所能地對傳統的審美理想進行顛覆和破壞,內容丑與形式丑的結合。兩個謀財害命的惡人本是普通挖煤民工,偶然間發現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謎底。作者詳細寫了兩次辦“點子”的經過,尤其是第一次,二人殺死元清平干凈利落的血腥場面讓讀者觸目驚心,在內容丑、精神丑的表現形式中吟誦出一段人性惡的咒語。
(三)丑的審美轉化
《神木》中的丑的表現并非單一的,而是把丑作為一種逐漸轉化的動態過程,丑與美在辨證統一的關系中逐漸契合。小說的題目“神木”是神性的審美符號,對“煤炭”的審美化轉化。也正是由于神性的緣故,黑暗骯臟的煤窯被附著上了一層神性的是色彩,使得原本的丑在冥冥之中增添了一種宿命的味道。樹葉到化石再到煤炭,這是自然界“死亡——再生”的轉化模式,這其中蘊含了“死得丑惡”到“生得唯美”的審美轉化,在生死轉化中暗含著神性的指引。劉慶邦曾寫道:“我給小說起名《神木》,也是強調任何物質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質的神性,我們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會陷入盲目狀態。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會走出自然的泥淖,逐步得到升華。”[3]《神木》就屬于這里所言的酷烈小說,劉慶邦毫無避諱地書寫著底層人民的生命狀態。
二、《神木》中丑的審美價值
在大眾媒體的大肆渲染和推波助瀾之下,出現“審丑泛濫”的局面,有些作家作品打著“文學審丑”的幌子,殊不知早已進入了“惡俗審丑”的誤區。然而,“文學審丑”的背后蘊涵的是對復雜人性的深刻思索,對底層小人物的親切關懷及對個體生命精神的痛徹反思。《神木》中丑的所具有審美價值可從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活動的四要素進行闡述。
(一)世界:現實世界的反映
文學來源于生活,是對現實生活的直觀反映。“‘丑由于發掘和顯現實際生活中某些人的丑惡的人性而生成的意象(即成為美),從而具有一種意義的豐滿。”[4]此處所言的“丑”的意蘊是通過發掘和解剖人性的丑惡,來深刻反思某個群體或者整個社會的黑暗、腐朽和混亂。劉慶邦在報紙上看到礦工在煤礦上打死同伴訛詐撫恤金的報道,震驚不已,他萌生了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的想法。原本被苦難淹沒的受難者自身成為制造苦難的劊子手,現實世界的苦難成為異化人性的罪惡道具。
(二)作者:個人價值觀的表達
作者力圖展示冷靜客觀的筆調來書寫故事,可是在作品中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作者個人價值觀的表達。《神木》作者在講述這個罪惡故事時,流露出對社會價值觀的失衡現象的深重擔憂,以及人類對金錢的崇拜和渴求泯滅了良知的丑陋行徑的控訴。故事結尾處王明君(原名趙上河)與張敦厚(原名李西民)同歸于盡,并且讓王風(原名元鳳鳴)向窯主索賠兩萬塊,囑托王風要他“回家好好上學,哪兒也不要去了”。王風事后并沒有向窯主訛詐金錢,作者在黑暗的故事中保留著人性救贖的期待。
(三)作品:藝術空間的延拓
“把美和丑都擺在美學的范圍里并論時,就是承認美和丑同樣是一種美感的價值”“美、丑一樣是美感范圍以內的價值,他們的不同只是程度的而不是絕對的。”[5]正如前文所說,美的事物的表現力是有限的,丑的事物具有更為廣闊的表現力。《神木》表現了底層民工掙扎于前現代與現代、后現代社會的夾縫之間,遭受資本殘酷盤剝,人成鬼、人變獸的人倫慘劇。
(四)讀者:復雜人性的反思
丑的意象被讀者更為深刻的理解和接受即是“審丑作品”的最大功效。尼采說:“藝術使我們想起了獸性生命力的狀態:藝術一下子成了形象和意志世界中旺盛的生命肉體,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過拔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獸性的功能——增強了生命感,成了興奮感的興奮劑。”[6]在個體生命意識不斷強化的當今社會,《神木》使讀者重新審視人類獸性生命力的原始狀態,充分認識到人性的復雜性,并對復雜的人性作出深刻的反思。
丑是最富審美現代性的范疇,劉慶邦的《神木》深入挖掘丑惡的否定性價值,以丑來發掘人性中非理性的力量,以酷烈的逾越來打破美的常態夢幻,讓人類在原始生命本能的丑惡行徑下無處遁形,在無處遁形的羞愧中睿智地穎悟和深刻地反思。
參考文獻:
[1][4]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58.367.
[2]朱立元.西方美學范疇史·第三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363.
[3]劉慶邦.給人一點希望[J].北京:十月,2004(05).
[5]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158.
[6][德]尼采.權力意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