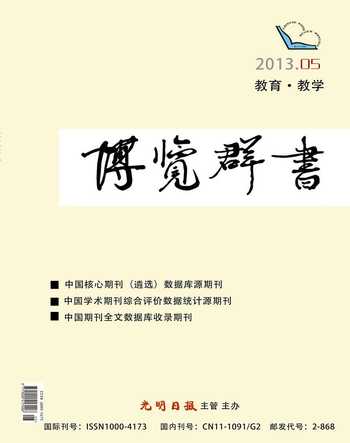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觀
摘 要: 杜亞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傖塘鄉(今上虞市長塘)。原名煒孫,字秋帆,又署傖父。他的思想龐雜深刻,在20世紀初期的文化論戰中他被攻擊為守舊派,但他對待中西不同文明形態上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 ,如今看來卻是穩健而有理性。他不僅支持西方文化的引進還提出在輸入西風文化時所要堅持的標準以及對中西文明利弊做出評判,這對我們思考當今不同文明的交流仍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杜亞泉;中國文明; 西方文明
1911(宣統三年)至1920年(民國九年),杜亞泉掌《東方雜志》筆政,前后共九年。他出任主編后,刷新內容,擴大篇幅,使之成為當時具有影響力的學術雜志。除此之外,他還勤于著述、翻譯,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等各方面,內容龐雜而思想深刻。后人曾評價他“其對于人生觀和社會觀,始終以理智支配欲望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結合為最后目的。先生實不失為中國啟蒙時期的一典型學者。”蔡元培說他“以科學方法研求哲理,周詳審慎,力避偏宕”。
然而后世對他的評價卻是毀多譽少,甚至將他視為落伍者,但今天再看來杜亞泉是一個堅持理性的學者。他對中西文化的差異有著他自己冷靜的思考,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迷亂之現代人心》、《何謂新思想》、《差等法》等文章中作者都有所闡述。因為他堅持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為我民族文化發展的本位,曾受到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激烈批判,也導致一場大的東西文化論戰。我們暫且不去評價那場論戰到底誰對誰錯,只對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觀作簡要分析。
首先看杜亞泉對兩種文明性質的判斷,“蓋吾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通過對東西文化的細致比較比較,“西洋社會,一切皆注重人為,我國則反之,而一切注重自然”“西洋人之生活為外向…而社會文明皆由人與人之關系發生。我國人之生活,為向內的…求其勤儉克己,安心守分…”,“西洋社會內,有種種團體…亦為競爭之結果”,“西洋社會,既以競爭勝利為生存條件,視勝利為重而道德次之…我國社會,則往往視勝利為道德之障礙”,“西洋社會,無時不在戰爭中,其間之和平時期,乃為戰后之修養期,戰爭為常態。我國社會,時時以避去戰爭為務”。他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而且他認為兩種文明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地理根源,且孰優孰劣需以所取標準而定,也就是說他認為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各有利弊。一戰前他曾說“吾自與西洋社會接觸以來,雖不敢謂西洋社會,事事物物,悉勝于吾儕,為吾儕所當效法,然比較衡量之余,終覺吾儕之社會間,積五千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風化之塵埃,征結之所在,不可不有以擴清而掃之”;戰后他又感慨“自歐戰以來,…吾人對于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懷疑之意見,而吾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業上表示其信于吾人。則吾人今后,不可不變其盲從之態度,而一審文明真價值之所在。”
杜亞泉堅決支持西方文化的輸入,至于如何輸入還要看他對文明評價的標準。他認為“精神文明之優劣,不能以富強與否為標準,猶之人心地安樂與否,不能以貧賤為衡”。在他看來“科學僅為發達經濟之手段,茍目的已誤,則手段愈高,危險亦愈甚。西洋社會之經濟目的,與東洋社會截然不同。”文明有其社會歷史性,盡管西方社會在科學技術、經濟、政治等方面著實比我們進步得多,要想我們也進步必須靠學習西方先進的地方。但是我們的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倫理道德型的社會,在中國人的觀念里“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如果西方文化無節制的輸入,那么西洋社會的弊端(重物質輕道德)也會隨之而入。那么唯一辦法就是中西文化各取所長,“在實現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學的手段,實現吾人之經濟之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實現吾人理性的道德”。
再看杜亞泉的東西文化調和論,相對陳獨秀那種疾風暴雨似的取代論顯得更穩重、更理性。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觀是從終極人文關懷的角度去思考。在杜亞泉看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是落后于西方,所以他不遺余力的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翻譯外國著作;但是不是引進西方的文明就能解決問題。杜亞泉對文明的評價標準是不同于陳獨秀的:他不以富強與否、貧富貴賤為衡,以心之安樂與否為準,他所關懷的是人超于物質以外的精神滿足感,是一種終極關懷。杜亞泉始終強調的是道德或倫理道德,東西文化各有優劣,應各取所長;同時更強調中國社會的優點可以彌補西洋社會的不足。盡管他們的物資生活優裕、政治生活民主、文化生活豐富,但是他們的欲望也隨著物資增長而膨脹,欲望的膨脹競爭的壓力便大,如此人總是生活在“狂躁”中。而中國社會一直靠倫理道德平衡社會,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保持這種平衡力確保社會的穩定。這樣看來,文化調和并不是單純的保守。不得不承認杜亞泉在東西文化上的深邃和理性,“兩社會之交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為勢所必至”。在現代社會種文化交流與融合趨日盛,各取所長仍不失為必要且理性的做法。
然而就像杜亞泉的反對派曾指著過的,杜的不足和缺點同樣也留給我們很多教訓與思考。盡管他承認東西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但他還是過分夸大文化的相對性,而忽視了差別的絕對性。東西文化的調和論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實施,以致表面看來像是不倫不類。尤其是在那個年代,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且飽受凌辱,他的文化調和論就很難具有說服力和可接受性。
參考文獻:
[1]蔡元培.杜亞泉先生遺事.蔡元培全集 .第7卷[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2]許紀森、田建業.杜亞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3]許紀森、田建業.杜亞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4]許紀森、田建業.杜亞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5]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J].東方雜志.第13卷第10號,1916年10月.
[6]杜亞泉.迷亂之現代人心[J].東方雜志.第15卷第4號,1918年4月.
[7]杜亞泉.迷亂之現代人心[J].東方雜志.第15卷第4號,1918年4月.
[8]許紀森、田建業.杜亞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作者簡介:陳立華(1987-),女,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2級教育碩士研究生,專業學科教學(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