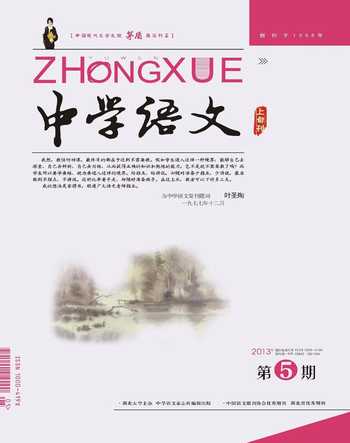小人物的“大”勝利
朱前珍
小人物是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作品中不二的主角,不管是進入高中教材的《流浪人,你若來斯巴……》中的“我”;還是《在橋邊》中的那位傷兵;以及《天天過圣誕》中那位有戰爭后遺癥的嬸嬸;《遺囑》中那位深受存在主義侵害的士兵;《扔東西的人》中那位包裝公司的小職員等等,他們是清一色的小人物,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對自己的命運沒有自主權。如果說有什么理想和志向,那也是受法西斯蠱惑而萌生的荒誕可笑的想法,比如《流浪人,你若來斯巴……》中的那位傷兵,胳膊和腿都成了炮灰,還聽到炮聲的悠揚悅耳,夢想陣亡將士紀念碑上刻上自己的英名。他們不僅僅是戰爭中的受難者,更是戰后廢墟的承受者;面對物質的匱乏,《天天過圣誕》中的嬸嬸有了一種特殊的癖好,必須每天過圣誕,不然她就發狂,盛夏里家人也必須陪同她穿著棉衣捂著棉帽裝扮圣誕樹,在戰爭迫害中扭曲的心靈最終摧毀了戰后生活的家園;生活在戰后的德國的小人物們得面對疾病,饑餓,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貧瘠。廢墟可以重建,但是心靈的廢墟是個例外。
伯爾在《九點半鐘的臺球》里象征性地把人分成“水牛”和“羔羊”,“水牛”是軍國主義者、納粹分子,是不愿回憶過去的當權者;“羔羊”是受迫害者,流亡者,回憶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伯爾戰爭題材的小說中,“羔羊”的柔弱無助,被摧殘、被戕害是小說的主旨。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發現伯爾小說中的小人物的形象正悄然改變,不再是任意被宰殺的,無奈呻吟或迷惘的“羊羔”,而成了有反抗能力的“斗士”,大聲疾呼,奮起抗爭,這一重要轉折表現在長篇小說《九點半鐘的臺球》(發表于1959年)之中。這樣的改變也體現在《在橋邊》這篇短文中。和表現戰爭題材的作品相比,這些作品中的氣氛不再使人有壓抑感,小人物們面對社會的壓迫,面對占統治地位的各種社會準則和要求也不再束手無策,逆來順受,而是表現出拒絕、不屈服和反叛的精神,我們不妨把這看成是伯爾在為這些小人物探究追求個人幸福、完成自我實現的可能性。
《在橋邊》中的“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形象:“我”是個傷兵,在“他們”的安排和施舍中度日,“他們替我縫補了雙腿,給我一個可以坐著的差事”,然而,看似得到了照顧和優待的“我”并不領情,“我”消極怠工,吊兒郎當,謊報數據愚弄“他們”,并以此為樂。“我”是個卑微的小人物,表面上只有服從安排,聽命安排,為保住飯碗而做著自己厭惡的枯燥無聊的工作。然而“我”又可以耍些花招,輕易地玩弄“他們”。“我以此暗自高興,有時故意少數一個人,當我發起憐憫來時,就送給他們幾個。他們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里……”
然而,“我”對“他們”的嘲弄并沒有給人帶來痛快淋漓之感,這些反抗是微不足道的,這些勝利是自我安慰式的阿Q式的勝利而已。“他們”高高在上,不了解戰后人們內心的痛苦,也不了解人們內心的掙扎和抗爭,所以“我”的這種抗爭只能更加突顯“我”內心的痛苦罷了,有人說,反諷是抵抗陰郁的有效武器,那么,反過來說,人們潛藏在心底的嘲諷,恰恰彰顯了自己內心的陰郁。
沒錯,其實“我”仍只是個遭受戰爭摧殘的,處境堪憂的小人物。反諷藝術的運用,只是人們內心宣泄不滿的途徑而已。首先,“我”不能瀟灑地拂袖而去說不干,畢竟“我”還是有賴于這樣的一份工作,有賴于“他們”的照顧而存活。其次,“我”還是得在表面上討好“他們”,“我懂得,怎樣喚起人們對我有誠實的印象”。當“他們對我進行檢查”時,我還得表現得很賣力,“我像發瘋似地數著”,向主任統計員示好。說白了,“我”的命運還是掌握在“他們”手中,不管內心如何不滿,“我”還得屈從,“我”得好好干,才有機會調去數馬車,才有機會去看“我”心儀的姑娘。
但是,無論如何,“我”之類的小人物自我意識已經覺醒,已經開始吶喊,已經開始為自己的幸福抗爭了。他們不只是滿足于戰后社會生活由困頓而復蘇的轉變,而是更期待人的自由不被侵犯,更期待精神家園的重構。
當一個民族從希特勒時代的狂熱和恐怖中醒來,才發現歷史留給他們的是毀滅性的災難,是國土上的廢墟和心靈上的廢墟。殘酷而嚴峻的現實,使一些人由于種種原因回避它、粉飾它,伯爾卻是執著于現實,去探索民族悲劇的成因,以及療救它的處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伯爾在文學中的表現,是一個民族在狂瀾既倒中自我拯救的悲壯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