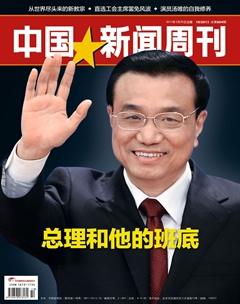深圳工商登記“變法”
閔杰
3月1日上午9點,72歲的香港居民李經文來到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羅湖區碧波辦證大廳。這一天是深圳實行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天,在深圳生活的李經文想要替朋友辦一個“鄉里好小吃點”的營業執照。
10點13分,李經文把營業執照拿到了手上。認真到近乎有些倔強的李經文看了看表,總共用了1小時13分鐘。“放在以前,起碼需要20天,”李經文說。他覺得還不夠過癮,當場決定再給自己辦一張,不到半個小時,他又拿到了一張“世界美協文惠進出口商品服務中心”的個體工商營業執照。
總是隨身攜帶相機的李經文很開心,讓工作人員給自己拍了照,并發到了自己的微博上。他在微博中說,“我僅用1小時13分就拿到了營業執照,且不收任何費用,這在香港也做不到。”
工商局的“玻璃門”
3月1日碧波辦證大廳的經歷讓李經文印象深刻,李經文曾在香港、江蘇等地多次開辦過企業,對中國大陸工商登記工作的繁瑣之處十分了解。
就在此前,同樣在深圳市場監督管理局羅湖分局,李經文也遭遇了注冊的尷尬,“我要注冊一個進出口商品技術服務中心,由個體戶來搞,這里沒有過先例。名稱核準就很麻煩,一次又一次,折騰的人想發火。”李經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他看來,注冊資金、場地審查和各項前置審批是擺在很多創業者面前的“三座大山”。
按照此前的辦證流程,名稱核準只是整個繁瑣的辦證程序中的第一步。核準后,要到銀行開設公司臨時賬戶,并找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驗資報告,最后憑驗資報告去工商部門辦理名稱核準。
“注冊資本實繳登記”是另一道門檻,按照2006年《新公司法》規定,注冊資本存放在銀行驗資賬戶,在公司取得營業執照前不得動用該筆資金。這無形中提高了公司設立的資金門檻,降低了資本利用率。
“過去企業辦證確實很難,有個說法叫‘玻璃門看似容易,實際很難,主要是門檻太高。”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袁作新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言。
“人們說工商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確實存在個別現象,但‘事難辦的癥結不在工商部門。”袁作新說,成立一個外資企業要跑幾十個公章是事實,但大都在前置審批部門,工商注冊只是最后一個環節,“結果對執照難辦的不滿情緒都堆在了工商部門”。
羅湖分局企業登記注冊科副科長李麗華舉了一個例子,“深圳市萬象城要辦一個卡拉OK廳,要提交衛生、環保、文化、消防四個前置審批許可的證件,企業把所有證件都辦下來,花了幾個月時間不說,最頭疼的是,四個證上的地址寫了四條路。”

萬象城恰好處于四條路的交叉地帶,原則上寫哪條路都不算錯,但一旦將來出現問題,工商登記部門就可能被追責。李麗華說。
“我們只能委婉地勸說企業去把地址改成統一的名字,可是人家好不容易把那些證辦下來,已經很難了,還要再去改一次,怎么能不生氣?”
“現在大不同了,按照最新的登記程序,他們可以先辦營業執照,其他審批部門再根據營業執照信息進行審批,就不會再出現類似問題了。”李麗華說。
寬進嚴管
按照深圳市人大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深圳市從3月1日起,全面推行新的商事登記制度。
“計劃經濟下制定法律法規,是把企業和人都預設成‘壞人,要通過制定制度,把人和企業管住、管死。”袁作新表示,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制定任何法律規章,應該把企業和人看成是好人,打開市場大門,再進行寬進嚴管。
“過去注冊資本‘三虛一逃的現象非常嚴重,虛假注冊、虛假材料、虛假場地、抽逃注冊資本非常普遍。”袁作新說,很多企業就去找中介公司墊資,一方面讓中介公司從中牟利,另一方面也給注冊部門提供了尋租空間,容易產生勾結。
“問題這么嚴重,不管是人員意識問題還是廉潔問題,都說明制度有問題。”袁作新介紹,在“新政”下,深圳的工商部門只登記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再登記公司的實收資本,也不再收取驗資證明文件和注冊登記費。這意味著開辦公司,無須再為注冊資本發愁。一個形象的說法是,只認繳1元的注冊資本,在理論上都是完全可以的。

另一個明顯變化是,個體工商戶、公司等營業執照上將不再記載“經營范圍”這一項,可以自由選擇增減經營項目。用袁作新的話來說,此前的規定很不合理,就像一個人出生前就必須決定自己將來是做什么的,取得出生證之前就要取得律師證、會計證等資格證明。
在李經文看來,目前深圳的商事登記改革已經趕上甚至超越了香港,“雖然香港的門檻也很低,但注冊和變更都要收取很高的費用。登記費要2000多港幣,名稱、法人、地址等任何一個事項的變更都要收取幾百甚至上千港幣。”
“我們的制度借鑒了香港的不良企業‘除名制度,但更加完善和人性化,是建立了‘黑名單即經營異常名錄,給違規企業‘緩刑期,避免誤傷。”袁作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動了誰的“蛋糕”
新政推行并非易事。袁作新說,方案征求意見時,相關前置審批監管部門的阻力很大,甚至有點“舌戰群儒”的意味。
“以前審批和營業執照互相捆綁,所有部門都已經習慣了,總希望發營業執照的時候為審批部門把一道關”。 袁作新說,原本由工商部門配合進行的監管變成了最后的兜底,僅僅是一處流程的改變,恰恰是在回歸法制,誰審批誰監管。
新政還不可避免地動搖了一個群體的飯碗——注冊會計師。深圳市注冊會計師協會曾表示,當前驗資證明和企業年檢審計業務占深圳市注冊會計師行業業務收入的80%以上,部分會計師事務所甚至達到了100%。如果取消,對注冊會計師行業而言不亞于“滅頂之災”。
這一度讓注冊會計師行業“如臨大敵”,甚至有上街抗議的傳聞,而袁作新則全程參與了“談判”。在袁作新看來,深圳需要出具審計報告的企業不到10%,卻養活了將近10萬會計師從業人員。“利用政府資源和企業來養活整個行業,本身是不對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談判的結果是,取消驗資證明文件,而新政中也吸取了注協的部分修改意見,例如引入注冊會計師對股東承諾的事項進行專項審計,以確定其是否履行了承諾。
另一個吃“工商”飯的行業——中介公司比較樂觀。《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羅湖分局嘉寶田辦證大廳樓下看到,這里依然活躍著很多中介公司業務員,他們名片上的內容大都相似:全國大額增資3萬~3億,代理工商營業執照一條龍服務,提供房屋租賃合同,代辦環保、消防、衛生等。業務涵蓋了從前置審批、驗資、辦照到變更的所有環節。
深圳市一家代理公司的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政對中介公司確實影響很大,但來辦證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政策細節,“不是不需要打資金了,只是暫時不用驗資證明了,以后該繳多少還是要繳多少,否則怎么向別人證明你的資金實力”。在他看來,新政并沒有“消滅”這個行業,只是把很多程序推后了,中介公司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與行業利益的博弈相比,對改革者而言,真正的難題在于敞開大門之后,怎樣才能“讓好的企業如魚得水,讓不良企業寸步難行”。
“一個重要的制度設計,就是要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平臺,把違法違紀企業的信息通報給全社會,通過社會監督來限制企業。”袁作新說,外界把新政看成完全沒有門檻,甚至看成開辦“皮包公司”“違法企業”的樂土,是純粹誤解。改革后皮包公司后果會更慘重,因為所有的信用記錄都會對公眾公開。
這套信息公示平臺還處在建設階段,袁作新預計,整套系統將于年底前建成使用,而在過渡期,將整合原有政府信息平臺的部分功能作為替代。
在袁作新看來,以信息公示、監督手段取代行政檢查和處罰手段,是整個監管制度的改革方向,不過,這樣一套全新的系統,如何有效替代原有的行政手段而發揮效用,以及如何與全國各地原有的市場監管環境相銜接,仍然需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