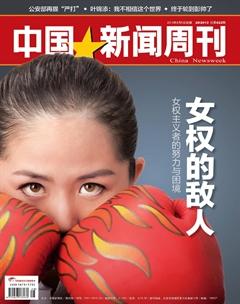暴徒心理不宜過(guò)度解讀
周郁琦
媒體對(duì)暴徒內(nèi)心情感的點(diǎn)滴渲染,都能暗示受眾去改變他們的看法。有時(shí)候,媒體和意見領(lǐng)袖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出適度的“冷漠”與“止步”。
機(jī)場(chǎng)出口爆炸,馬連道家樂福砍人,光明樓金鳳成祥爆炸……近日,公共場(chǎng)合暴力事件頻頻發(fā)生,不免讓人感到有一股戾氣積聚升騰,如同拉開了槍栓的槍支——種種惡相逼問(wèn)我們:“中國(guó)到底怎么了?”
媒體對(duì)于每一次暴力事件的揭示都不遺余力:哈爾濱殺醫(yī)案的背后,是十六歲少年與爺爺從農(nóng)村進(jìn)城治病的艱難;廈門公車爆炸案的背后,是上訪無(wú)門的陳水總的種種無(wú)奈。然而,促使罪犯向無(wú)辜者揮起屠刀的,難道僅僅是社會(huì)不公嗎?
哥倫比亞大學(xué)的心理學(xué)教授羅伯特·海爾曾經(jīng)做過(guò)實(shí)驗(yàn),喜歡虐待、生性殘忍的人在辨識(shí)富有情感意涵的詞匯與一般詞匯時(shí),腦波無(wú)明顯差異,而普通人的腦波則表現(xiàn)出不同。進(jìn)一步的研究說(shuō)明,前者負(fù)責(zé)辨識(shí)字的語(yǔ)言皮質(zhì)以及負(fù)責(zé)賦予字義的邊緣系統(tǒng)的連接出了問(wèn)題。正因如此,他們的情感較常人淡薄,在面對(duì)痛苦時(shí)不會(huì)引發(fā)焦慮,甚至對(duì)于恐懼沒有感受。犯罪心理學(xué)研究表明,那些暴力犯罪者,通常是這種缺乏同理心的人,他們無(wú)法為人設(shè)身處地著想或同情別人,亦很難受到良心譴責(zé)。
除了缺乏同理心,陳水總等人所表現(xiàn)出的還有一種反社會(huì)人格。當(dāng)他們?cè)庥錾鐣?huì)的不公,并且長(zhǎng)期處于社會(huì)邊緣孤立無(wú)援之際,情緒就很不穩(wěn)定,脾氣暴躁,自我控制不良。在貝克的認(rèn)知三聯(lián)癥中,邊緣人格往往具有負(fù)性自動(dòng)思維。他們對(duì)自我的認(rèn)知往往是“我是個(gè)失敗者”,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沒人關(guān)心我”,對(duì)未來(lái)的認(rèn)知“我不會(huì)有任何成就”。可以說(shuō)反社會(huì)人格多受情感沖動(dòng)支配,一次偶然事件就容易誘發(fā)其報(bào)復(fù)心理,犯罪動(dòng)機(jī)較模糊。殺人、報(bào)復(fù)無(wú)辜者的行為是他們不能得到滿足與欲求的表現(xiàn),以此獲得代償性的滿足。
當(dāng)殺人者以殘酷無(wú)情的方式處置無(wú)辜的陌生人,是否還值得同情呢?曾經(jīng)的弱者,面露猙獰,行兇成魔。任何看似情有可原的事由,都無(wú)法抹去殺害無(wú)辜的犯罪事實(shí)。而那些對(duì)暴徒內(nèi)心世界和背景過(guò)度側(cè)寫的媒體,已經(jīng)姑息了以暴制暴的氣焰。這種看似悲天憫懷的全面關(guān)注,讓善良疲倦,讓兇戾前行。
在大眾傳媒中,為了達(dá)到傳播的高效,往往傾向于簡(jiǎn)化推理步驟,這使得大量以同情和模糊類比為出發(fā)點(diǎn)的情感判斷得以冒充和代替理性分析。媒體深挖暴徒的背景,以大詞和背景替代事件本身和當(dāng)事人的行為邏輯,這不是從因果出發(fā),而是從情感的偏見出發(fā)。
受眾再遇到此類暴力事件,也會(huì)依賴這一路徑,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如果一個(gè)人在冷靜嚴(yán)肅的時(shí)候能完成四步推理,那么當(dāng)他置身群體之中,或受到大眾傳媒的轟擊時(shí),往往只能完成兩步推理。理性就這么在喧囂和群情洶涌中被邊緣化。
另外,大眾傳媒受時(shí)效性影響,往往具有片段性和碎片化特征,這給憑空想象和感情用事留下了空間。尤其是經(jīng)過(guò)二次傳播,微博上的意見領(lǐng)袖憑借自己的主觀性評(píng)價(jià)令事件在輿論中醞釀發(fā)酵。一些中國(guó)公眾遇事即以對(duì)抗、斗爭(zhēng)和陰謀論解讀不夠充分的信息,這種思維定勢(shì),也是盲目同情施暴者的觀念土壤。
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對(duì)暴徒內(nèi)心情感的點(diǎn)滴渲染,都能暗示受眾去改變他們的看法。曾有媒體探訪殺醫(yī)的李夢(mèng)南老家,對(duì)他那間破舊的屋子拍攝了許多照片;也有媒體拍過(guò)陳水總在廈門借住過(guò)的地方,確實(shí)差強(qiáng)人意。經(jīng)過(guò)這些藝術(shù)化的處理之后,文字圖像毫無(wú)疑問(wèn)有著神奇的力量。
我理解過(guò)度側(cè)寫的媒體是為了替弱者聲張正義,把丑陋不堪的社會(huì)問(wèn)題暴露出來(lái)。但是,一如前文所述,過(guò)度地使用煽情技巧,或輕率地作出價(jià)值評(píng)判,并不利于受眾群的理性思考。有時(shí)候,媒體和意見領(lǐng)袖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出適度的“冷漠”與“止步”。
與此同時(shí),讓制度分析的學(xué)者、心理學(xué)家、社會(huì)觀察家、思想者等出現(xiàn)在大眾媒介中,把他們對(duì)突發(fā)事件的反思、對(duì)社會(huì)不公的批判、如何消弭問(wèn)題的探討等傳遞給受眾,似乎更有裨益。警示社會(huì),引導(dǎo)社會(huì)大眾的思考,顯然是比煽情更重要的媒體職責(zé)。
社會(huì)制度的缺陷有賴于全體社會(huì)成員從觀念上進(jìn)行改變。著名思想家哈耶克的文明演化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社會(huì)的不公正即道德的喪失,需要的不是法制規(guī)范的增補(bǔ),而是人們內(nèi)心中對(duì)于道德規(guī)則的遵守。除了在我們自身內(nèi)化之外別無(wú)他法。法治于心,公正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