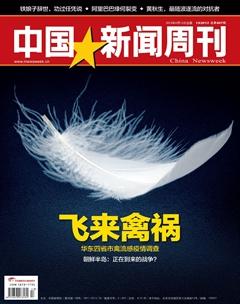產業空心化面臨破題
周政華
4月6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會上,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感嘆,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強國。現在沿海的勞動力越來越貴,好多老板要么把廠子搬到孟加拉,要么搬到中西部省份,要是產業升級沒跟上,弄不好就要出問題。
魏建國說的問題,也是本屆亞洲博鰲論壇的“圓桌討論”討論最為熱烈的兩個話題:如何進行產業升級,以避免制造業空洞化。
2012年,中國人均GDP達6100美元,已步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列,此前35年間低成本的競爭優勢(例如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長期偏低)已經不再。在這一背景下,唯有產業升級一途。問題是,產業升級過程中,受全球供應鏈重組和國內人力資本不足的掣肘,中國工業“高不成、低不就”漸成顯性,產業空心化正在撲面而來。
低不就
在數年前最鼎盛時,曾經生產了全世界70%的打火機,數百家皮鞋廠一年賣出的皮鞋夠13億中國人每人分一雙。被喻為“小狗經濟”的溫州,儼然是世界工廠中最繁忙的車間之一。
然而,繁榮未能持續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曾經機械轟鳴的溫州,皮鞋廠一家接一家倒閉,曾經一心干實業的老板們,陸陸續續地開始投資礦山、林地,搖身一變成為西裝革履的風投人士。IT之都東莞也留不住臺資企業,樟木頭鎮空出來的廠房越來越多。最終,成都和鄭州,取代深圳東莞,成為富士康、聯想等IT巨頭的生產主基地。
當下中國制造業正面臨著國內和國際雙重轉移。
從宏觀數據看,隨著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北上,長三角、珠三角最先遭遇“產業空洞化”沖擊。一組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可以佐證:中西部地區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2011年比2004年提高了8.4%,經濟增速上,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東快西慢”格局,在最近四五年漸漸變成了“東慢西快”。
國際產業轉移也發生了變化。歷史上,全球發生的三次產業轉移,都是單方向的由上而下的轉移,即由經濟發達國家向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而這次轉移出現了雙向特點。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為主的中小制造企業由中國向越南、緬甸、印度等勞動力和資源等更低廉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而同時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業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引導下回流。
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國際上的這些變化,導致導致中國原有的競爭優勢正在逐步削弱。
依靠廉價勞動力搞簡單制造業的老路子已經走不通。浙江省人大財經委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012年7月,60%以上的溫州規模企業選擇了減產停產。
不僅僅是溫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4月6日在博鰲透露,最近由他牽頭組織的一次全國范圍內小微企業主抽樣調查顯示,84.1%的小微企業主,在最近一年內,曾考慮或已經“暫停生產線、減少業務”。
高不成
面對當前成本上升、產能過剩等困難,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秘書長李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該機構進行的2012年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多數企業家選擇了產業升級和進入新行業。
但是,具體到每個細分領域,該如何升級,也常常讓企業家們摸不清頭腦。
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有一次和保育鈞談話時感嘆,現在民營企業都知道,不搞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就是等死;搞了產業升級,就是找死。為什么?看不出清方向,因為“有時候,你走了一步就是領先,但走了三步,就會成為先烈”。
4月6日,在博鰲“產業空洞化:制造業的隱憂”圓桌討論會上,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則直接指出當下產業升級的核心問題:核心技術缺失。
董明珠認為,制造業空洞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一些貼牌企業就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到沖擊,因為它們在開始建設期間眼光短淺,只看到了近期企業利潤,并沒有做出長期規劃。
盡管溫州的鞋機企業超過百家,占領了全國60%的市場,成為繼臺灣地區、意大利之后的第三大世界鞋機生產基地,但其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價格低廉和大規模生產上,產品主要以模仿為主。
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溫州的皮革、制鞋機、塑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值增長一般都沒有超過10%。而當地醫藥、電氣等科技含量高的行業都實現了年均15%到30%的增長。
科技含量較低,也是整個中國制造業的通病。
以當下進入破產潮的光伏行業為例,早在2011年,世界光伏組件公司排名前十的,有8家是中國企業。但是在賽維、尚德這些國內光伏標桿企業中,其太陽能電池生產的關鍵設備,絕大部分來自國外供應商,進口設備費用約占企業設備費用的80%。

4月6日下午,由中國最高級別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編寫的國內首份《2013中國產業升級研究報告》稱,中國的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依然較弱,目前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依靠勞動力價格優勢,承接了全球低中端產業的轉移,付出了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
由于缺乏核心技術,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長期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盡管經濟增長在最近三十年平均超過9%,但是勞動生產率并未實現同步增長。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在2012年超越日本,但是上述報告指出,201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日本的4.37%。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對人力資源投入的不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4月7日在博鰲論壇致辭時,說道亞洲的土壤未來必須施加肥料才能保證能夠真正的孕育出“亞洲夢”,諸多“肥料”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對“人”這項資本進行投資。
無獨有偶,在當天的另外一個圓桌討論上,當談及人口政策問題時,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說,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要想保持經濟活力,除了保證相當數量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外,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勞動力的技能,這需要持續對其進行投資教育。
導向何方
一個國家的產業轉型還依賴于政府的有效引導。日本、韓國、臺灣,這些東亞近鄰實現經濟起飛,產業升級時,背后都離不開政府的推動。
日本就是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在過去半個世紀,一步步實現了兩次大產業升級。熟悉國際經濟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現在是中國產業升級的最好時期,政府應該把握好這個時機,引導產業升級,實現“中國夢”。
很多地方政府也從心里意識到,唯有產業升級才有出路。
2012年,溫州市政府開始強化“以畝產論英雄”,哪些產業能夠在單位土地上創造更多的產值,就引入哪些產業。對原有的皮革產業,進行高端產品提升。年內,溫州還出臺實施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3大新興產業培育方案,并且還計劃發展激光與光電產業集群、電動汽車產業建設。溫州等地政府組織民營企業家去歐洲招募人才。
比溫州更早進行主動產業升級的是廣東。早在2007年,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曾告誡說“如果東莞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不久,廣東開啟了“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進行低端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
保育鈞發現,一些地方政府所出的發展規劃,都很雷同,比如有些中西部城市,本地一沒高等院校,二沒有自然資源,但就是要發展生物醫藥,軟件園。
中央政府該如何支持?博鰲產業空心化分論壇上,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洪斌認為,政府層面首先要重視制造業的發展,在結構減稅和金融上支持制造企業;第二,把資源要素向制造業傾斜;第三,要創造好的環境,如知識產權保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