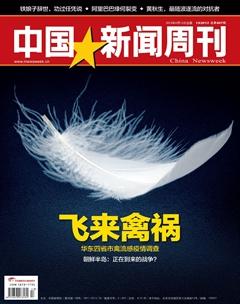“核武器是不可放棄的國寶”
蘇潔
三年前的11月11日,在平壤一家豪華酒店的飯桌上,朝鮮大使對齊格弗里德·海克爾說,“明天,你們將有大發現!”第二天,在寧邊鈾濃縮工廠的巨大廠房里,海克爾一行看到了令人驚嘆的一幕:整齊排列的2000臺現代化離心機。
站在二層控制站的望臺上,海克爾問陪同的朝鮮技術人員,“這是巴基斯坦(懷疑和巴基斯坦“核彈之父”卡迪爾汗的黑市交易有關)生產的嗎?”對方給出了顯然早已準備好的答案,“所有材料均在國內生產。”3個半小時的考察,對方一再強調,“我們原本不想展示,但領導授意如此。”
這是齊格弗里德·海克爾最后一次訪問朝鮮。回國后,他給白宮提交了11頁的技術報告,并表示,“這些設施看起來是民用核能,但也可生產核彈使用的高純度濃縮鈾。”
從2004年起,作為美國頂尖核物理專家,齊格弗里德·海克爾每年都會以非官方身份被邀請到朝鮮參觀核設施。2010年后,他沒有再登陸朝鮮。對于朝鮮而言,海克爾向美國傳達朝鮮核實力的“信使”作用似乎已告一段落。而40多年的核物理研究經驗則告訴海克爾,“朝鮮的威脅越來越近了。”
2013年4月以來,朝鮮半島周邊一天一個新動態,讓世人眼花繚亂。
4月2日,朝鮮對外宣布將重啟5兆瓦石墨減速反應堆;3日,美國宣布將在關島部署一套反導系統;4日,朝鮮對美國發出警告,發動核打擊的行動已經獲得批準;同日,韓國媒體稱,朝鮮把一枚疑似中程導彈的物體運向東海岸地區,而美國更是派化學部隊重返韓國。據新華網消息,外媒關注到,中國也向中朝邊境增兵,日本宣布對朝鮮的單邊制裁延長兩年,韓防長表示將武力保護在朝韓國人。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連日來也不斷呼吁,“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已經升得太高,請朝鮮不要再發出核威脅。”
戰爭似乎“一觸即發”。
此時的海克爾正在休寫書假。通過助理,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轉達了自己的態度,“如果平壤動用核武器,除非金正恩準備好了面對政權的覆滅。”
對此,長期關注報道金氏家族,并為金正恩兄長金正男撰寫傳記的《東京新聞》編集委員五味洋治也表達了審慎的態度。“4月15日是金日成的誕辰,金正恩即使在此時發射導彈,也不可能裝載核武器。”五味洋治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金正恩的動作,僅僅是威脅而已。”
戰爭真的來了?善于給人意外的金正恩仍吊著外界的胃口,但他顯然暫時無意解開朝核問題之結。
“在世界實現無核化之前,朝鮮不會走無核化道路。”金正恩的表態,讓“朝鮮棄核”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各方較量中,逐漸淪為口號。
代號“家具工廠”
2013年2月12日,農歷大年初三。中國人還沉浸在過節的氣氛中,距中國北部100多公里的朝鮮邊境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上午11點,中國地震臺網發布消息,在朝鮮北緯41.3度,東經129.0度發生了4.9級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
當天,韓國軍方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經韓國防部確認,朝鮮正在進行當量為10千噸左右的核試驗。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的當量約16千噸。
一切跡象表明,朝鮮第三次核試驗成功了。
朝鮮外務省發言人則隨即提醒,這次核試驗是應對美國敵朝行徑采取的“自衛措施”。
對朝鮮而言,這次“自衛措施”還算成功。“證明朝鮮有實力把核裝置小型化,從而用火箭運載。而第一次試驗僅證明朝鮮可以制造核裝置。”海克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海克爾提到的第一次核試驗,發生在2006年。當年10月9日,伴隨著咸鏡北道吉州郡附近的一場3.6級的人工地震,朝鮮首次“安全、成功地”完成了核試驗,并成為世界“核俱樂部”的第八個成員國。如今第三次核試驗后,朝鮮更是進一步通過法律堅定了“從質和量上鞏固核武裝”的信心。
這一步,朝鮮走了半個世紀。
在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張璉瑰教授眼里,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朝鮮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援助,使朝鮮的人均GDP超過同期韓國。然而潛心發展經濟不是朝鮮國家元首金日成的目標,“統一朝鮮半島”不能只靠經濟。
首爾國際危機研究所的東亞中心主任丹尼爾·平克斯頓認為,朝鮮發展核技術,不僅源自領導層的統一目標和自保心理,也是朝鮮人“民族主義情緒”的需要,對他們來說,被殖民的經歷仍記憶猶新。
早在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后不久,金日成就在一次非公開會議上表示:“朝鮮雖然國家小,但別國擁有的東西都應該有,包括原子彈。”而后來叛逃的朝鮮勞動黨前書記黃長燁也曾證實,“金日成認為一旦有了核武器,首先可以鎮住韓國,而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時,也可以防止美國干預。”
1955年,在金日成的主導下,朝鮮在平壤建立了第一個核物理研究所。
這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也給了朝鮮發展核技術以機遇。
1952年和1960年,英國和法國先后試驗核武器成功,讓蘇聯感到鞏固自己陣營實力的緊迫。于是,扶持金日成建國的蘇聯,自然成了朝鮮發展核技術的“導師”。
196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朝鮮建立寧邊原子能研究基地,并完成了首個重要核設施的建設:輕水反應堆IRT-2000。最初,朝鮮要求在兩國的往來文件中,將建設輕水反應堆的計劃代號為“家具工廠”。而這種絕對機密的研究,也始終在地下進行。
不過,朝蘇兩國間這種被張璉瑰描述為“最初是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合作”的援助計劃,卻逐漸演變成對蘇聯地區利益的威脅,以及美國和朝鮮周邊國家的擔憂。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在古巴部署導彈的蘇聯面對美國的強大攻勢,最終不顧古巴反對,撤走了導彈、飛機等軍用設施。這一冷戰期間的著名對弈,讓朝鮮意識到即使蘇聯也不可靠,開始“自主掌握國家命運”。
1974年,朝鮮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1985年,在蘇聯的壓力下,朝鮮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但拒絕接受檢查。僅一年后,朝鮮建成了寧邊5兆瓦級石墨反應堆。
從此,寧邊這個位于平壤以北約130公里的小城,和它致力發展核武器的祖國一起,上了美國“支持恐怖主義”的黑名單。
1989年后,朝鮮經歷了最焦頭爛額的一段時期。先是蘇聯解體,朝鮮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援助(唯一的好處是朝鮮招到了數十名前蘇聯的失業核專家);接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1994年去世,朝鮮經歷政權更迭;同年,朝鮮開始遭遇連續四載的自然災害。
盡管如此,朝鮮并未停止核研究的腳步。到20世紀末,朝鮮相繼建成了6個核研究中心、3座二氧化鈾轉化廠、兩座研究性核反應堆、一座核電試驗堆和一個核廢料貯存場。探明的可供其發展核技術的鈾儲量為400萬噸。
美國的角色
今年3月31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新的戰略路線:經濟建設和核武力建設并舉。
而會后公報的內容則重新強調了核武器的地位:“核武器是國寶,不是拿美元兌換的商品,也不是談判桌上的政治籌碼。”
隨著技術和時機的成熟,核武器逐漸從朝鮮的幕后走到臺前。而“國寶不是拿美元兌換的商品”的表述,似乎也透露著美國在朝核問題上的重要角色。事實上,最初將朝鮮核武器公之于眾的正是美國。
1989年,美國通過衛星照片拍攝到寧邊的核處理工廠。從照片上看,反應堆正在運行,其冷卻塔上方有蒸汽冒出。美方因此確定,朝鮮正在研制核武器。
美國隨即指控朝鮮發展核武器,將消息通知蘇聯,并要求檢查到寧邊檢查。朝鮮矢口否認研制核武器,并拒絕檢查。由此引發了美朝之間的第一場核危機,美國表示,隨時準備“精確打擊朝鮮”。
“第一場核危機奠定了美國在對待朝鮮問題上的基調:搖擺不定,但基本是制裁和強硬。當時的布什政府缺乏一個清晰的戰略目標,充滿機會主義。”梅爾文·古德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古德曼所描述的90年代初的布什政府,正面臨著蘇聯解體后,如何在亞洲重新定位的問題。前美國國務卿貝克1991年發表于《外交》雜志上的文章顯示,當時的美國將朝鮮半島核擴散定義為“亞洲穩定的頭號威脅”。
張璉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朝鮮問題的談判桌上最初是美朝雙方,然后是韓國,之后才逐漸加入其他國家。”
經濟制裁并沒有讓朝鮮垮掉,這讓美國政府不得不放低身段。而處在經濟崩潰邊緣的金日成政權也開始試著合作。
在美國表示愿意從韓國撤出所有戰術核武器,并允許朝鮮視察其在韓國軍事基地后,1992年,韓國和朝鮮最終簽署了《關于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
與此同時,朝鮮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訂了《核安全保障措施協定》。并從1992年5月起,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6次檢查,結果是未發現朝鮮研制核武器。
好景不長。1993年初,美國恢復了同韓國暫停一年的聯合軍演。隨后的3月12日,朝鮮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中斷與韓國的無核化會談。
此時,克林頓剛入主白宮不到兩個月。克林頓的選擇是:經濟制裁,同時做好戰爭準備。而朝鮮則硬碰硬地下令讓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視察員離開寧邊。
就在彼此劍拔弩張的時刻,克林頓接到了美國前總統卡特的電話。“1994年6月1日,卡特總統打電話給我,說他愿意到朝鮮去一趟,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我不反對他去朝鮮,因為評估報告顯示,一旦發生戰爭,雙方都將損失慘重。”克林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在卡特與金日成密談后,當年10月,美朝雙方在日內瓦簽署了《關于朝鮮核問題的框架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將協助朝鮮建設兩座發電能力為1000兆瓦的輕水反應堆,于2003年完工;在輕水反應堆建成之前,美國每年向朝鮮提供50萬噸重油。作為交換,朝鮮凍結寧邊核反應堆并封存燃料棒。
協議達成后,克林頓內閣的外長佩里不由松了口氣,認為協議把“該地區從戰爭的邊緣拉了回來”。第一次朝核危機就此化解。
“這次危機給朝鮮的啟發是,依靠反應堆制造钚彈不僅技術落后,而且設施龐大露天,美國間諜衛星盡收眼底。”張璉瑰說,“之后朝鮮轉而鈾濃縮辦法制造核彈。”
迫切渴望核技術的朝鮮在失去了蘇聯援助后,于90年代末期將目光轉向巴基斯坦。
1997年,美國媒體開始大量報道朝鮮用導彈技術交換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離心機)技術。
盡管當時巴基斯坦總統發言人庫雷希予以否認,但2004年被軟禁的巴基斯坦“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則指稱,朝鮮在90年代末期支付了至少350萬美元給巴基斯坦換取重要的武器技術。
“如果卡迪爾汗的交易是真的話,它大大推動了朝鮮的核技術。據我的觀察,朝鮮很難在短期內完成大規模的離心機制造。”海克爾表示。
各種傳言甚囂塵上,1998年8月,美國衛星再次拍攝到“地下核設施”的可疑照片。與此同時,朝鮮試射了一枚大浦洞1型遠程導彈,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后落入太平洋。
這一舉動引發美國強烈不滿。11月,美國要求無條件視察朝鮮寧邊地區。面對美國拖拖拉拉的核電站建設進度,朝鮮要求美國在視察前給予3億美元補償,遭美拒絕。
美國最終前往朝鮮視察了可疑核設施,但未發現證據。作為回應,朝鮮于1999年5月宣布退出朝美核框架協議。
此間,美國智庫成立審議小組對克林頓對朝政策進行了全面審議,結果認為,美國應該展示與朝鮮“合作”的誠意。
1998年和1999年,美國為朝鮮提供了價值分別是1.6億美元和1.4億美元的食品援助。而在1996年,美國的食品援助僅為約1500萬美元。
1999年9月17日,朝鮮承諾暫停試射導彈4天后,克林頓宣布部分取消對朝鮮長達近50年的經濟制裁。這一舉動被《紐約時報》稱為“朝鮮戰爭以來放寬對朝制裁的最廣泛行動”。
美元起了一定作用,但真正帶來朝核問題轉機的,是朝韓的“二金會晤”。
不斷擴大的談判桌
2000年的朝韓“二金會晤”,金正日展現出了難得的和平態度。
當年的6月13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和韓國總統金大中在朝鮮舉行了歷史性會晤,并簽署了《南北共同宣言》。宣言提出了“和平統一”,而這個朝韓關系發展中的里程碑,也讓金大中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宣言簽署后不久,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即抵達平壤進行訪問。
然而,歷史性會晤余溫尚存,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
當時,小布什政府在掌握了朝鮮在國際市場上采購核技術的證據后,隨即將朝鮮列入“邪惡軸心國”名單。而面對遲遲不見動靜的美國援建輕水反應堆,金正日命令拆除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控設備,驅逐監控人員,并于2003宣布正式退出《核不擴散條約》。
就在這一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了。
“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并很快捕殺了薩達姆,讓朝鮮不得不采取新策略。朝鮮原本想進行朝美兩國會談,但遭到了美國拒絕,最終形成了六方會談的局面。”張璉瑰說。
于是,2003年8月,在中國的參與和推動下,朝核問題第一輪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參與國為朝鮮、韓國、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會談的共識之一是“朝核問題要分階段、并行地、概括性地解決。”
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六方會談“是形勢使然,也是中國主動的意愿。”
從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六方會談共舉行了六輪。其中,第四輪會談取得了實質性進展。2005年,與會各方達成的協議中,朝方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
但數年來,朝鮮對六方會談“若即若離”,并終于在2009年4月發表聲明,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將按原狀恢復已去功能化的核設施。這期間,朝鮮的核技術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2006年和2009年,朝鮮先后成功進行了兩次核試驗,正式擁核。朝鮮巧妙地渡過了安全瓶頸期。”張璉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朝鮮在2009年的第二次核試驗,發生在其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的一個月后。而這也直接引發了外界所稱的“第三次朝核危機”。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認為,當時韓國總統李明博的“鷹派”態度,是導致半島局勢緊張的原因之一。
2007年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以來,一直淡化前兩任總統實施的“陽光政策”,認為“陽光”不僅未遏制核武,反而損害了韓國利益。于是走實用主義路線的李明博,在對朝態度上轉而向日本靠攏。
“從2000年到現在,日本在朝核問題的態度基本上是最強硬的。朝核、導彈和綁架三個問題捆在一起都要解決。一個不解決,都不結束制裁。”劉江永說。
2011年,利比亞戰爭爆發,美國介入。同年10月,卡扎菲被殺。
國際環境的變化,讓金正日開始轉變策略,重新嘗試對話。此后,在多方推動下,2011年,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金桂冠應邀訪美,開啟雙方兩年以來首次高級別對話。10月,朝美雙方再次在日內瓦舉行對話。同年,金正日還輾轉訪問了俄羅斯、中國和蒙古。
就在人們認為有望重啟六方會談時,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
接棒剛一年的金正恩,依然是核問題的強硬派。除了第三次地下核試驗的舉動外,去年12月,發射第二顆“光明星3號”衛星。
今年4月1日,在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上,金正恩宣布通過“進一步鞏固自衛核國家地位”的法律。核武器這個國寶,他暫時是不準備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