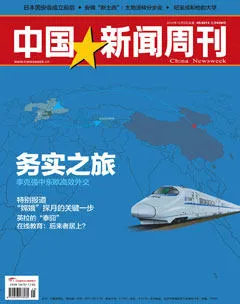合作社的新挑戰

2013年一號文件公布那天,64歲的哈爾濱欣躍三莓果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陳海龍非常興奮,他看到了那句或將改變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方向的一句話:“抓緊研究修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
如同所有投身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人們一樣,陳海龍對于修法的期盼由來已久。事實上,同樣的議題也早已進入北京決策層的視野。
“現在的合作社都是比較專業的,比如西瓜合作社,草莓合作社,西瓜、草莓之外還種糧食的怎么辦,允許發展綜合社不?法律上沒有聯合社,出村出縣行不行,允不允許聯合社?”3月21日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專業社與聯合社之外,合作社法修訂中還要解決一些優惠政策的落實問題。
伴隨著城鎮化腳步的加快,農業人口的加速轉移,農業專業合作社的合縱連橫亦變得緊迫起來。
抱團闖市場
陳海龍是哈爾濱市賓縣綜合職業教育中心退休教師,已有十幾年探索合作社發展的實踐經驗。賓縣綜合職業教育中心1995年成立,此后一直嘗試把農民組織起來。但由于沒有經營實體為協會提供有效服務,幾次嘗試都沒有成功,陳海龍經常被農民問到:“加入協會能給我賣大米嗎?”這讓陳海龍意識到,要想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就得解決農民增收問題。
1998年12月,陳海龍從東北農業大學引進了黑加侖品種,成立了“賓縣農村專業產業協會”,并引導農民種植,后來又陸續引進了紅樹莓、美國黑莓、藍靛果等漿果新品種。2002年7月24日,“賓縣黑加侖合作社”成立大會召開,但在工商局登記未果,在民政只能登記為協會。2005年3月1日,合作社最終在哈爾濱市農委注冊登記,并更名為“賓縣欣躍農業合作社”。
“由于沒有法律支持,不被社會接受,政府某些領導參加合作社會議都不敢以公職身份,先表明是個人身份。”陳海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合作社準備吸納更多成員以便發展壯大,但合作方公司突然單方中斷合作,壓低黑加侖果價錢,并提出來年不再給合作社賣黑加侖。合作社彼時尚無獨立經營資格,遂陷入困境。
合作社法誕生前,大多數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都像陳海龍領辦的合作社這樣,歷經各種艱難曲折而輾轉求生。這些合作經濟組織,最早出現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家庭聯產承包制興起帶來的農業產業調整中,獲得經營自主權的農戶,迫切需要通過社會化服務解決進入市場的各種困難,比如生產經營規模、技術水平、市場信息、營銷渠道等。與此同時,農村社區組織的服務功能卻不斷弱化,各級政府涉農部門遂開始推動新型社會中介組織發展。然而,這些以協會形式存在的合作組織,法律主體地位并不明確,因而發展受限。
2007年7月1日,《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始擁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和市場主體地位。陳海龍他們很快就到工商局重新登記,定名為“哈爾濱欣躍三莓果業專業合作社”,一改此前求助企業的方式,用黑加侖、紅樹莓鮮果加工罐頭成功,又陸續研發果醬、果酒、果汁飲料等產品投放市場,開始獨立走上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的道路。
就在陳海龍的合作社逐漸走上正軌的同時,全國各地在工商局注冊的合作社迅猛增長,截至2012年年底已達68.9萬戶,差不多接近于全國行政村的數量。“最近5年的發展量,相當于之前28年各類合作經濟組織總量的3.7倍,全國大體平均每個月增加1萬家。”2012年7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經驗交流會上表示,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勢頭強勁,但目前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
資金困局
各地喜見合作社數量不斷飆升,單個合作社卻又面臨規模小、競爭實力偏弱等發展瓶頸。
武漢市東西湖區八屆人大代表韓忠翔在2010年的調研中發現,全區71個合作組織,普遍存在嚴重缺資的情況,即使有少量資金也僅供維持合作組織自身運轉,甚至存在許多有名無實的“空掛社”。兩年后,該區人大執法檢查時,資金困難仍是檢查組要求解決的首要問題。
哈爾濱欣躍三莓果業專業合作社,也深受資金匱乏之困,以至于產銷一體化經營發展異常艱難。“加工廠需要投入,市場開發也要投入,合作社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陳海龍說,“我們是認真按合作社法原則辦社的,感覺合作社法沒有勁,除了明確企業與合作社的關系和允許不超過20%的非農身份參與合作社以外,其他的似乎沒什么感覺。”
陳海龍甚至漸漸覺得,這些問題遠非一個合作社組織本身能夠解決,更多彰顯的卻是合作社法與現實之間的沖突。
事實上,農民能夠投入合作社的資金往往有限,有些地方已經嘗試以土地使用權入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但農民以土地使用權入股,一旦發生合作社債務清償,農民又不可能以土地清償債務。
不僅如此,現行法律也沒有涉及合作社的融資、資金互助等功能,再加上大多數合作社起步階段抗風險能力很差,難以從正規銀行得到貸款。黑龍江的陳海龍就因為合作社沒有抵押物,無法得到銀行信貸,最后求助于民間借貸。而《中國新聞周刊》在湖北武漢接觸到的一位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人,設法辦了二三十張信用卡取現周轉,目前已經累計負債七八十萬元,只能依賴民間套現公司幫忙養卡。
湖北省京山縣經管局的調查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縣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453家,其中有90%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具備產權資格證,金融機構對部分合作社的成員只能以“專業合作社+農戶”的形式發放少量的小額信用貸款。因此,民間借貸就成了該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
為了解決資金緊缺難題,不少地方在實踐中嘗試引入社會資本。武漢市東西湖區八屆人大代表韓忠翔,就在2010年分析該區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現狀時建議:“條件合適的合作組織(尤其是沼氣工程等公益性項目)可以嘗試通過股份制、引入風險投資或投資基金等方式,引入現代管理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內部管理控制體系,將潛在的社會資本導向農村產業化經營,形成以社會資本為主導、銀行配套、政策支持的融資模式。”
現實中,社會資本進入合作社后,往往輕易就掌握了話語權和收益分配權,而農民淪為附屬,這與合作社的“民辦、民管、民受益”原則背道而馳。
3月17日,湖北省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指導辦公室調研員王于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包括企業化、公司化、個人化傾向,他舉例說:“比如,有一些生產加工和流通企業,為了采購或出售自己的東西,把客戶變成社員,利潤自己拿,給社員的優惠也只是一種說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也發現,現在經營不錯的合作社,其實很多都是按照股份公司來運營的。“實際就是股份公司。”徐小青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將是未來法律修改亟須考慮的問題,比如,大規模資本進來行不行,農外資本、工商資本進入門檻怎么設立?
規范難題
“農民專業合作社頒布5年多來,全國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68.9萬個,是成績,還是誤區?”陳海龍根據自身經驗和觀察認為,這其中存在嚴重的規范運作問題:“有誰能提供這些合作社中,有多少合作社以其成員為服務對象,提供了多少給農民返還盈余的服務?有多少是國家對合作社的扶持資金拉動注冊登記的?”
陳海龍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合作社基本原則的核心,是社員擁有的所有權、控制權和受益權。現行法律規定,合作社實行一人一票制,成員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決權,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份額,要求按成員與本社的交易量比例返還,剩余部分才能夠按照出資額等進行分配。
在實際運作中,“一人一票”的決策機制往往難以落實,通常是核心成員起關鍵作用。各地一直有大戶領辦、控股或主導的合作社存在,核心成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能人”,他們無論在最初的產權建構、制度設計上還是日常管理決策中都擁有著突出的影響力。武漢市農業局在2012年7至9月份的調查中發現,武漢市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大戶能人領辦。
武漢市農業局主管合作社的深加工處處長高申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合作社的單一出資人占有股份甚至高達百分之八九十,這就與合作社法規定的農民至少應當占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并且實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決策機制相違背。
前述武漢市農業局的調查就發現,雖然依法登記注冊的合作社都有比較規范的章程及有關制度文本,并按規定設立了理事會、監事會、社員大會等機構,但實際運作中大都流于形式。

不規范運作的結果是,農民的利益往往很難得到保證。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崇光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分四次對湖北、四川、重慶、湖南、陜西參與“農超對接”的合作社進行了實地問卷調查,發現2008年達到了合作社法對合作社盈余分配要求的只占被調查合作社的23%,而2009年這一比例進一步下降到13%。不僅如此,其中還有30%的合作社盈余返還比例在30%以下,不到合作社法規定的盈余返還比例的一半。
“合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怎樣才能讓農民真正得到利益?”李崇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應該建議全國人大對合作社法執法運行情況進行檢查,并形成一個定期的具有約束力的制度。
然而,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在武漢市農業局主管合作社的深加工處處長高申東看來,更深層次的矛盾在于合作社法關于出資結構的要求過于理想化。
“實踐中要達到規定的要求比較難。”高申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戶、能人自身的能力和資源,對于合作社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根據合作社法的規定,出資和分配辦法量化到能人手上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十幾,利益機制相對薄弱,這就導致操作起來很困難。
不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認為,世界上所有合作社都沒有資本說話的,都是成員說話。“現在碰到的這些原則性的人與資本的問題,這些與現實的矛盾,到底怎么辦,還是需要調研、觀察。”徐小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現實與法律的矛盾中,一批合作社開始休眠。
武漢市農業局主管合作社的深加工處處長高申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亦表示,雖然合作社總量已經達到一定比例,但現在也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下一步怎么規范提升是很大的問題。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初步做個估計,現在的合作社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是一般的,還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運作。”
走向聯合
盡管矛盾重重,陳海龍領辦的哈爾濱欣躍三莓果業專業合作社,一直按照合作社法的原則和方向不懈努力,但他始終覺得步履維艱。
通過與荷蘭合作社高度專業化對比,陳海龍發現哈爾濱欣躍三莓果業專業合作社的誤區在于,由合作社自身提供產前、產中、產后包括加工、運輸、銷售的全程服務,既做不好也做不到。
“原因是違背服務專業化的客觀規律。”陳海龍認為,一個合作社提供生產全過程服務的道路走不通,應該確認合作社“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的專業性。
陳海龍的反思,折射出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另一困境。由于農民專業合作社大多主營一種特色產品,同時又有地域限制,這就造成了在生產或者銷售過程中需要與其他合作社合作。然而,現行合作社法并沒有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做出明確規定,這就給合作社之間的合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也不利于合作聯社的建立和推廣。
“這些年已經出現了聯合社,法律上卻沒有這個內容,登記上就會出現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合作社研究院院長孔祥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聯合社跟專業合作社又有很大的不同,并不能簡單等同于一般專業合作社,他說:“聯合社的問題很緊迫,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解決不了,必須要通過修改法律來解決。”
好消息是,在今年的一號文中,首次出現“農民合作社”的提法,并要求“引導農民合作社以產品和產業為紐帶開展合作與聯合,積極探索合作社聯社登記管理辦法”。“去掉了‘專業兩個字,這個概念更科學、更全面。”孔祥智說,但這勢必會增加立法難度。
事實上,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逐漸由種植養殖業向加工、勞務、運輸、信息、資金、技術和銷售等眾多領域延伸,農機服務合作社、鄉村旅游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等從事二三產業的合作社快速發展,合作聯社已經廣泛興起。湖北省天惠種植養殖專業合作社聯社理事長韓波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很多合作社覺得自身力量小,希望聯合起來,而聯合社以整合資源,提供服務為目的。”
至2012年底,北京、江蘇、湖南、黑龍江、遼寧、山東、四川、重慶、山西、海南、江西、新疆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出臺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地方性法規,已明確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組成聯合社。
3月21日,陳錫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年內修法仍有難度,但要抓緊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