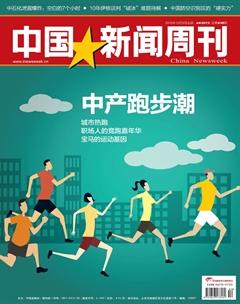“疑罪”從誰?
韓永
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下簡稱《意見》)。分析人士認為,這是最高法院在密集地為冤案平反、為個案正義頻繁吹風后,最終將自己“關進了制度的籠子”。
細心人士注意到,《意見》的簽發日期為10月9日,比公布的日期早了43天。《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幾位專家認為,《意見》之前在等一個面世良機,而這個機會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對司法改革有一些堪稱“顛覆性”的安排。

如何證明“證據的非法性”?
多位業內人士在受訪時表示,《意見》令人鼓舞之處,是摒棄了一些文件中常有的抽象與宏觀,其內容非常具體,且很有針對性,沒留下多少自由裁量的空間。
一位希望匿名的某中院刑事庭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產生冤假錯案的原因非常復雜,“若非真正動真格,很難有實際效果”。
這位法官說,冤假錯案產生的核心原因,是在證據不扎實的情況下做出了判決。這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很常見。曾經有幾位刑事庭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他們承辦的刑事案件中,證據真正確實、充分的比例非常低。“一年難得碰上幾個這樣的案子。多多少少都有點瑕疵。”
這些瑕疵在偵查階段就已經出現。尤其是一些輿論高度關注的案子,偵查機關從一開始就承受著“限期破案”的壓力。比如在對張高平、張輝案的反思中,浙江省高級法院提到,在發生命案后,社會上人心惶惶,上級會對這類案件進行督辦,時有層層下達限期破案死命令的情況發生。時間緊、壓力大,刑訊逼供于是應運而生。
一位縣級刑偵大隊的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所在縣的刑偵大隊,一線的辦案人員不到10個,接到的刑事案件卻一個接著一個,每個辦案人員平均分到每個辦案的時間很短。在偵破手段的局限和上級破案的壓力下,刑訊逼供就在所難免。
近些年,偵查機關獲取證據的手段出現了“升級版”。《意見》就提到了其中的幾種:凍、餓、曬、烤,以及疲勞審訊。《意見》規定,通過這些手段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
但在實踐中,這些帶有瑕疵的證據到了法院后,卻要經歷各種復雜的現實考量。首先,這些證據的“非法性”很難被證明。一方面,偵查機關在使用這些手段時,會有意識地避免留下證據;另一方面,處于偵查機關完全控制下的犯罪嫌疑人,沒有任何舉證能力;此外,法律對在審訊中使用錄像的強制規定,也僅限于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
前述不愿意具名的刑事庭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出于取證難的原因,被告人如果在庭審中指控偵查機關對其采取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通常不被法庭采納。
他解釋說,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被告人,會在庭審的時候部分甚至全部翻供。這種翻供,有時候就是一個關鍵的細節。比如在共同殺人案中,被告人說是別人拿的刀,自己沒有拿,而他原來的供述是自己拿刀了。“問他為什么與原來的供述不一樣,他會說公安打他,但又拿不出證據。對于這種情況,庭審中通常不相信被告人。”
《意見》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多位受訪人士認為,要讓這條規定落地,首先要解決被告人的取證問題。
刑辯律師許蘭亭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可以通過規定律師在審訊時的在場權以及當事人的沉默權,來解決這一問題。
枉縱之間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法官對刑訊逼供的違法性心知肚明,卻又對其使用表示理解。法官這一心態背后的邏輯是:他們認為很少被告人會主動坦白自己的罪行;此外,他們也認為偵查機關取證手段雖然非法,但嫌犯的口供大多真實。
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郭自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國幾十年的刑事審判實踐中,對“不縱”的強調力度遠遠超過“不枉”。結果是造成“寧枉不縱”,這就成為了冤假錯案的一個理念基礎。
雖經幾十年司法變遷,有罪推定的觀念依然根植于很多司法人員的內心,并且貫穿于從偵查到起訴、審判的各個階段。
在《意見》發布會現場,最高法院刑三庭有關負責人說,實踐表明,錯誤的執法理念和司法觀念,是導致冤假錯案的深層次原因。“只有徹底糾正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錯誤觀念和做法,才能消除冤假錯案再次發生的現實危險。”
還有一個沒有引起足夠關注的風險,即法律的權威。它帶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后果是,在這些以法律權威為代價的溝通中,司法機關漸漸失去了公信力。
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在今年5月份發表在《人民法院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觀念轉變的方向,即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分析人士認為,沈德詠所言之“天”,意指中國的“法治”。
但受訪人士表示,要從目前的“寧枉勿縱”,轉變成法治成熟國家倡導的“寧縱勿枉”,絕非一日之功。其中除了觀念因素外,還有一些更為糾結的現實考量。
其中的一個現實,是法院與公安局和檢察院之間的關系。前述刑庭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些因限期破案而證據缺損的案件,法院也不敢輕易適用“疑罪從無”。因為這些關注度甚高的案件破獲后,偵查機關都會立功受賞,有的還會升官進爵。而一旦因證據不足被法院判處無罪,偵查機關就會從原來的功臣變成罪臣,其中的尷尬自不必說,公安局長也會因此受累。
而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公安局長兼任同級的政法委書記,是同級法院的頂頭上司。法院如果按“疑罪從無”原則判案,有時就會沖撞了自己的頂頭上司。
檢察院也可能受到影響。中國目前檢察院的考核體系,通常包括“五率”,即無罪判決率、撤回起訴率、不起訴率、抗訴成功率和追訴糾錯率。其中,無罪判決率在考核中所占的分量最重。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省級檢察院檢察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地方的考核指標規定,如果一年中出現三個無罪判決,主管檢察長就要被免職。
基于檢察院與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這種對檢察院的不良影響,有可能轉化為檢方對法官的“公報私仇”,即檢方可能會啟動對法官的調查。而刑事案件往往較復雜,通常避免不了程序上的瑕疵,因此法官也對這種調查有很多顧慮。
協調的風險
不過,在實踐中,上述這種公檢法“多輸”局面發生的可能性小。據受訪法官透露,在遇上此類案件時,政法委就會召集公檢法三家,召開協調會議,為案件定下基調,然后由法院的審委會貫徹執行。此類案件定下的基調,通常是“疑罪從輕”。
這是一個在封閉狀態下運行的過程,外人難知其祥。加上有些案件不公開審理,律師閱卷權也得不到保障,是否“疑罪”,疑問幾何,有時只是外界的一種猜測。聶樹斌案即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在有些對相關各方都事關重大的案件中,為了避免出現無法預知的后果,檢察長會列席法院的審委會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檢察長沒有表決權,但有發言權。
在上述過程中,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從無罪判決可能引發的緊張關系,演變為判決有罪的皆大歡喜。政法委在其中的作用耐人尋味。幾位受訪法官都表現出類似的態度:一方面對政法委的干預有切膚之痛,同時又對其協調作用難以割舍。其中一位受訪法官,在聽到政法委將不再干預個案的傳聞后,第一反應是“這是政法委在推卸責任”。
協調帶來的最大風險,是可能造成冤假錯案。但郭自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還有一個沒有引起足夠關注的風險,即法律的權威。它帶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后果是,在這些以法律權威為代價的溝通中,司法機關漸漸失去了公信力。
當前的司法體制改革,正在努力找回司法的公信力。在《意見》公布之前,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在今年8月、6月和9月公布了有關防范冤假錯案的文件。這四份文件中都提到,要改革現有的績效考核機制。
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對困擾司法公正的很多現實問題,都做出了體制和機制上的安排。其中最有突破性的安排,當屬“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規定要發揮實效,還需要很多的配套安排。比如,省里直管地方法院的財政沒有問題,但對地方法院院長的任命,則需修改相關的法律。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