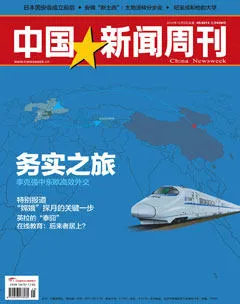引進蘇—27:中國戰機騰飛的跳板
徐焰
近日,新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訪俄羅斯。
習近平訪俄之前,中俄剛簽署了兩份重大軍售框架協議:中俄將合作建造4艘先進潛艇,中國還將向俄采購24架蘇-35戰機。這是時隔近10年后,中國首次向俄羅斯采購重大軍事技術裝備。
近年來,中國航空母艦服役,隱形機試飛,大型運輸機運-20問世。中國航空業的成就,已引起世界矚目。為什么現在中國還要向俄羅斯購買軍機?
如果回顧一下20多年前中國引進蘇-27戰斗機的過程,就可以看出,借鑒他國技術對發展本國科研的重要作用。
同西方合作不成,回頭與蘇聯重續前緣
現代軍事科技的變化,日益體現為“地面問題空中解決”。如今國防建設的頭號重點,正是空-天力量。

筆者從小就對空軍及其戰機有一種天然感情。我生長在位于北京公主墳的空軍司令部大院中,在孩提時便認識50年代中國的一些著名的空軍英雄,并為他們借以創建輝煌戰績的空中坐騎——當時世界上先進的米格戰機而自豪。
中國空軍鐘情于蘇聯飛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舊中國沒有航空工業,新中國成立時,解放軍空軍只有60余名東北老航校畢業的飛行員。在如此落后的基礎上建立空軍和航空工業,只能靠當時的“老大哥”蘇聯援助。
上世紀50年代,蘇聯按半價和成本價向中國出售了4000多架戰斗機,提供了配套的航空工業設備,并派出專家協助建設,使中國能仿造出擁有先進技術的米格-17和米格-19。
19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但赫魯曉夫為了在戰略上重新爭取中國,于1961年又提供了米格-21戰斗機樣品和技術資料。
1962年古巴發生導彈危機,赫魯曉夫抱怨中國對其不表支持,停止了對中國供應航空裝備。
中國空軍依靠蘇援,戰機性能曾一度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但卻存在著內在的脆弱性。蘇聯援華的底線是不涉及飛機設計領域,蘇聯一旦停止供應裝備,中國航空工業科研基礎薄弱的弱點便顯現出來,國內作戰飛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近20年的停滯徘徊期。
毛澤東晚年雖然提出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卻因極“左”的指導思想,無法提升航空業水平,60年代和70年代上馬的十幾種機型,都因技術不過關而下馬。
結果,中國空軍戰斗水平逐步降到世界十強之外,戰機性能還落后于周邊的臺灣地區和印度,保衛國家安全的戰略威懾力量主要靠“兩彈”(導彈、核彈)和龐大且裝備落后的陸軍。
但在邊海防斗爭中,這一威懾卻無太大作用。如南海周邊國家搶占南沙群島時,中國因殲擊機作戰半徑不夠而鞭長莫及,除譴責外難以采取實際行動來制止。
直至80年代前期,中國空軍的主力作戰飛機一直還是仿50年代蘇聯米格-19而制成的殲-6,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到將近30年。空戰中主要靠技術取勝,落后一代的戰機與強對手交鋒,會出現“找不到、打不著”的情形,甚至只能成為敵機的靶子。當時,筆者就常聽一些飛行員感嘆:“現在我們裝備的飛機,給美、蘇的三代機當靶機都不夠格!”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領導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差距。1979年1月18日,鄧小平特別強調:“不管如何,今后作戰,空軍第一。陸軍、海軍、空軍,首先要有強大的空軍,要取得制空權。否則,什么仗都打不下來。”在陸地游擊戰起家的眾多中國領導人中,鄧小平有這樣的認識,可謂鳳毛麟角。
當時,中蘇關系仍處于敵對狀態。中國空軍曾試圖采購英國的“鷂式”和法國的“幻影-2000”戰斗機,但因對方索價太高,加之北約的裝備標準與中國的蘇式標準不同,最終未能談成。
1986年,中國啟動了自主研制殲-10的工程。
同時,鑒于國內科技基礎落后,中國又達成了同美國合作改造殲-8Ⅱ的“和平珍珠”計劃。這一項目在美國啟動后屢遭拖延,至1989年夏天又遭到單方面中止,中方已付出的3億美元投入血本無歸。
也就在1989年,中蘇關系實現了正常化。蘇聯軍方主動提出,愿對華出售先進戰機。這使中方再度把引進先進戰機的希望,投向剛修好的昔日盟國。
不要米格-29,要最新的蘇-27
國際間的武器銷售,從來帶有濃厚的政治性。中蘇關系正常化時,正逢蘇聯國內發生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這場危機卻成為了中方的機遇。
1990年4月,中國總理李鵬訪問蘇聯,雙方簽署了合作紀要,其中包括恢復軍工合作。9月,中國軍事代表團在相隔29年后,再次來到莫斯科城郊的庫賓卡空軍基地,參觀米格-29的飛行表演。
米格-29在80年代是蘇軍裝備部隊和出口的主要戰機,是一種空重8噸、作戰半徑只有500公里的輕型戰斗機。由于米格飛機是中國空軍的老伙伴,蘇聯軍方起初認為,中方會選擇米格-29作為新一代主力戰機。中國軍隊一些人也有這種想法。
不過這一情況報到中國國內,以江澤民為主席的中央軍委卻要求看一下蘇方并未安排的蘇-27重型戰斗機。
蘇-27是蘇霍伊設計局于1970年代后期設計的重型戰斗機,1985年才裝備蘇軍。它1989年在巴黎航展上首次亮相,便以“普加喬夫眼鏡蛇”等一系列高難度飛行動作轟動世界。該機空重達17噸,可載彈6噸,作戰半徑在1000公里以上。可以說,該機空戰性能遠超中國當時所有的殲擊機,載彈量和作戰半徑也超過中國的輕型轟炸機。美國和西歐軍界都承認,蘇-27在1980年代末堪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斗機之一。
此前,蘇聯從未向任何國家出口過這種飛機,中國軍人也只是耳聞其名。中方提出參觀要求之初,未獲同意。
讓中國軍事代表團多少感到突然的是,雙方經過座談,并在宴會上共同懷念過去的戰斗友誼,似乎都動了感情,蘇方人員隨即招待中國參觀了蘇-27戰斗機,還爽快地同意出售。
其實,這樣重大的帶有戰略意義的舉動絕不可能是感情用事。事后知道,此舉是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力主,并得到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同意。
亞佐夫當時是堅決反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后來成為試圖挽救蘇聯政權的“八一九事件”的發起人之一。此時蘇聯軍界不僅希望通過對華軍售獲得收入,一些人還希望在維護蘇聯政權時得到中國支持(實際上此時中國已嚴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而戈爾巴喬夫此時也自感處境不妙,同樣有在政治上向中國示好的需要。
這同1957年赫魯曉夫因蘇共黨內危機同意對華提供核彈、導彈技術援助的情形有些相似。由于有這種政治背景,才出現了中蘇剛恢復軍事關系,蘇方就同意銷售先進裝備的情況。
1990年12月,中蘇雙方在北京簽署了軍售合同。中國首批購買26架蘇-27(其中2架為教練型),總價30億元人民幣。當時的中國還缺乏外匯,合同金額的大部分以以貨易貨的方式支付。
1990年,中國軍費開支不過290億元,扣除維持生活的“人頭費”和日常費用外,一年的武器采購經費不足100億元。蘇-27軍購項目,是當時單項金額最大的一筆開支。
事后證明,中國在經費困窘時仍不買相對便宜的米格-29,而采購較貴的蘇-27,是有遠見的選擇。
從發展戰略看,繼續使用作戰半徑短、運載量小的輕型米格機,只能維持國土防空型空軍。而選擇重型的蘇-27,卻可以帶來空軍發展戰略思想的變化,從此走上“攻防兼備”的道路。
從技術角度看,中國選擇蘇-27作為新一代主力戰機,是高起點的選擇,為加速本國航空工業,尋求到了一條捷徑。
蘇聯都不在了,合同還有效嗎
1991年2月,蘇聯派出蘇-27,來到北京南苑機場,進行了精彩的飛行展示。與中國現役飛機相比,其一流外形設計及超機動性能,至少高出了一個時代。當時筆者問一些飛行員出身的空軍干部有何感受,他們的回答大都是一個詞:震撼。
此次飛行表演,更使中方感到,采購的決定是正確的。
但江澤民強調,要全面引進技術,不能只限于買成品。空軍因此前沒有裝備過世界上第三代噴氣式戰斗機,也沒有此種訓練,便選拔飛行員到蘇聯培訓。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1年8月,蘇聯發生巨變,同年12月,蘇聯解體。引進蘇-27的合同能否履行,一時成為疑問。
幸好,中國貫徹了鄧小平提出的以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定親疏的原則,沒有介入蘇聯的內部爭端,因此,葉利欽主政的俄羅斯聯邦仍承認中蘇武器銷售合同有效。
中國空軍戰斗機代際劃分
第一代 :1956 年,中國首架噴氣式戰斗機殲 -5 投產 ;1964 年,中國首架超音速戰斗機殲-6試飛成功。進入21世紀后,殲-5、殲 -6 相繼退役。
第二代 :1966 年,國產第二代戰機殲-7試飛成功 ;1969 年,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殲 -8 首飛成功。
第三代 :1998 年,中國研制的第三代戰斗機殲 -10 首飛 ;90 年代中國從俄羅斯進口蘇-27戰斗機生產線,改名為殲-11,并于1998年首飛。這標志著中國空軍正從第二代向第三代邁進。
第四代 :隱形戰斗機,已試飛成功。
俄羅斯經濟危機,使得軍方多年間幾乎不訂購新戰機,蘇霍伊公司面臨被收購的危機。主要靠中國的訂貨,該公司才維持了生存,并有了研制新機的資金。據當年俄方報道描述,來自中國的新訂單簽下后,共青城竟是全城徹夜歡呼慶祝。
1992年6月27日,由俄羅斯共青城飛機生產聯合體出產的首批蘇-27戰斗機飛抵中國安徽,裝備了曾在朝鮮空戰中有過光榮戰績的航空兵師。
該機的設備在出口時已有些“縮水”(這是蘇聯出口武器的慣例),但比當時中國空軍的主力戰機,卻差不多先進了20年。不僅中國飛行員由此熟悉了第三代戰機,國內航空界設計新型戰機也得到一個重要的參考品。
1992年12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首次訪華。蘇聯瓦解后,俄羅斯融入西方的想法并未實現,還遭受北約進一步打壓,因此,俄羅斯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使他在這次訪華后宣布,俄中兩國是友好國家。4年后,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戰略合作伙伴”。
中國空軍通過使用蘇-27的實踐,深感其性能優異,認為在國產殲-10未研制定型前,可作為“拳頭”武器裝備軍隊。1995年,中國同俄方談判商定,在沈陽引進蘇-27生產線。
1996年葉利欽再次來華訪問,在氣氛熱烈的宴會結束后向中方宣布:“我們已經決定向你們出售最新的蘇-30。”該型機是在蘇-27的機體上改進而成,其設備更好,且更適合對地、對海攻擊,正好適應了中國在東南沿海軍事斗爭準備的需要。
中國空軍的“井噴”式發展
整個90年代,中國引進了數以百計的蘇霍伊戰機及其生產線(只有發動機俄方堅持由它出口),總花費差不多100億美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金額最大的武器采購。時人計算,這甚至超過了解放后國家對航空工業的總投資。
但如全面分析,這筆錢還是花得值得的。那時,國內航空科研部門和制造業大多還停留在30年前蘇聯援華時的水平,在得不到西方技術而自己研制又非短期能奏效時,只有引進俄方航空技術才是捷徑。
令俄方驚訝的是,中方引進戰機后,不再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樣只是照葫蘆畫瓢式仿制,而是消化其技術并在借鑒基礎上創新。
這個跨世紀的宏大項目,不但滿足了中國空軍升級戰斗機的急迫需要,也為其自行研制殲-10戰斗機贏得了時間,同時為發展第四代戰斗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引進,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空軍的第一次現代化躍進后,空軍歷史上第二次現代化的重要起點。
不出幾年,沈飛從仿制蘇-27開始,邊組裝、邊改進,推出了新型號殲-11B。該機作為航程遠、載彈量大的重型戰斗機,與2004年開始服役的殲-10輕型戰斗機一起,正好可以實現輕重搭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主席佩斯2007年春在鞍山機場參觀殲-11B型機后評價,該機氣動外形與蘇-27相同,但內載電子設備和所用材料已大有過之。俄方試飛員飛過該型機后也感嘆:“這完全是一種新的飛機。”
為了彌補無法制造高性能發動機這一關鍵性缺陷,中國引進蘇-27的同時,開始了國產發動機的研制。經10年努力,終于在2006年推出了“太行”發動機,從而有效地醫治了中國戰機的“心臟病”。
近兩年,中國航空裝備出現了西方以“井噴”一詞來形容的飛躍發展:第四代隱形戰機相繼試飛、殲-15艦載機在航空母艦上起降成功、被稱為“大運”的運-20也研制成功。國際航空界公認,中國自行研制的戰斗機水準已僅次于美俄,而且預警機等技術已超過俄羅斯。
當然,由于中國航空業畢竟起步晚,目前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中俄之間繼續進行軍貿仍有必要。不過,雙方已經改變了當年單純的買與賣的關系,變成合作研制,例如在重型直升機項目上,便是如此。
今天中國航空業的巨大成就證明,1990年代對蘇-27的引進,堪稱當代世界上非常成功的軍售案例。打破封閉的觀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并與自主創新相結合,這正是這一中國軍購史上金額最大的項目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