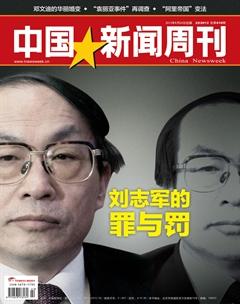中國醫生如何看美國醫療劇
協和生

盡管反映醫生工作的電視劇,前有美劇《豪斯醫生》《急診室的故事》等,但是,《周一清晨》,還是讓人對美國醫生、美國的醫院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在劇中的“切爾西醫院”里,一切都做得太專業、太完美了。換句話說,這部電視劇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理想化的醫院。
“切爾西醫院”里的醫務部主任或者稱之為院長的哈丁·胡頓,在每周周一清晨,也可以是隨時,把醫生們召集到311室。針對這周的病例,對發病率、治愈率、死亡率與錯誤率,進行研討。這位“首腦”對他的下屬,不但會對他們的醫療行為、行醫道德,甚至對他們的私人生活,都提出質詢和指責——只要是他認為可能影響到醫生實施手術的各類問題。在311室里,他對任何人的任何錯誤都毫不留情,甚至挑剔且苛刻。用中國話講簡直“吹毛求疵”。
顯然,這種嚴苛對于“切爾西醫院”每一個人技術的進步、醫療道德水準的提升等等,有十分巨大的幫助。這部劇集就是以這個醫生判官的視角,將醫生在職務過程中的可能碰到問題和爭議分集一一拆解呈現。從而為人們展示了美國人的價值觀:美國醫生如何看待病痛,如何看待生命。
劇中,韓裔的樸醫生分別遇到過兩個病人:一個是因腦神經異常而丟失了樂感的小提琴演奏家;一個是因腦神經疾病而創作欲、創作靈感超常的作家。對于前者,自負的樸醫生,主動請來同為神經外科專家的威爾遜醫生為音樂家操刀,自己在手術室里親自拉琴,幫助患者找到影響樂感的神經,唯恐因為手術一點點失誤,毀了音樂家的職業前程。而對于后者,當患者得知,切除大腦的病變部分,自己思如泉涌的靈感也有可能失去時,拒絕手術治療,樸醫生竟然對此表示了贊同,他放棄了手術。在樸醫生看來,生命的價值不僅僅是活著,而要有價值的活著。
醫生的主要職責是治病,但是,醫生面對的不僅僅是病,更重要的是人;挽救一個人的生命很重要,挽救一個人生存的價值更重要。當然,這是美國人的價值觀。
這部電視劇同時非常直白地把醫生這個行業的風險也展示了出來。劇中的一句臺詞講到,“每天都有醫生被起訴”。一個醫生,你可能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拯救了他的生活和家庭。但是,如果你的醫療行為中有瑕疵,有不規范,你仍可能面臨訴訟。劇情里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完成了一例介入手術,通過切斷腦部一個神經醫治了一位帕金森癥患者。介入手術后,女患者的手不再抖動了,但由于手術傷害了大腦某個未知的功能區,讓女患者同時有無法抑制的性癮。結果,患者和家屬,把她的恩人、那位為她做手術的大夫,訴上了法庭。
中國醫院和醫生做不到的
完美醫院“切爾西醫院”既不在美國東海岸的紐約、費城,也不在西海岸的洛杉磯、西雅圖等美國一流的大城市,而是位于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可是在這樣的一個二三流城市的醫院里,卻能有全世界最好的精神外科醫生,一流的器官移植技術。用該院的醫務部主任的話講“這里的醫生是全世界最好的”。這是中國與美國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中國,不管是一流公司,一流科研機構,一流大學,還是一流醫院,一般都是在一流的城市,甚至基本都聚集在北京、上海這些超一流的城市里。
中國的醫療制度雖規定,對于特殊的病例,對于死亡的病例要進行討論,但是,很多情況下,都是走走形式。一是長者為尊,位高者說了算;二是和諧為本,極少人會提出不同意見,不爭論;三是保全面子,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極少進行批評和指責。事后的檢討極少公開進行,除非是惹上了官司,要進行懲罰。
像“切爾西醫院”這種研討、這種批評與指責,絕無可能。
醫生的風險來自方方面面,責任不到位是風險,技術水平有差距是風險,甚至相互不信任都是風險。每一個醫生面對的都是有著千差萬別的患者,身體條件不同,病因病種不同,每一個人所掌握的技術又是那么的有限,出現失誤在所難免;而面對生命,有時診斷遭遇不信任導致的事故,更讓人扼腕;事故后的訴訟,也只能讓不信任進一步升級。前兩年在北京某家醫院,一個產婦患重癥肺炎,醫生為救腹中嬰兒要求剖腹,但監護人拒絕簽字,造成產婦和腹中嬰兒雙雙死亡的案例。在之后的訴訟之中,家屬找了一些醫生出身的辯護人,找出一大堆該醫院在救助產婦過程的治療問題。他們繞過了該產婦當時已經不可能救活,醫療的焦點在于如何挽救嬰兒的生命、而監護人拒絕簽字的問題,而是抓住醫院方面在產婦的治療過程中的一些處理手段上的不規范和不當。最后,以醫院賠償十萬元結案。
中國醫生在診療技術上與美國的醫生有差距,這是事實。不是中國人不聰明,也不是中國人不努力,環境條件所限。若真如《周一清晨》這部電視劇中展示的一樣,很多醫療問題,很多診治的細節能夠公開的討論、交流,人們有接受指導和借鑒的機會,那么醫療的水平必然能更快地提高。
在中國,開放性的病歷討論都非常不容易,死亡后的解剖分析更是一個禁區,很少有醫院能夠有這種機會,醫生技術水準提高自然受到制約。
而中國醫生的從醫條件,又遠比診療技術上的差距還大得多。這也是環境條件所限。當下,中國的醫生似乎已經成為了“人民公敵”。可當全國各個行業都面臨道德失控的時候,醫生又怎么能夠脫離開其他群體,獨善其身呢?實際中國的醫生并不比其他行業的人更無德,只是他們工作處于人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很難做到平等公平的討論
同樣面對病,如果說劇中美國醫生治與不治的依據,是生命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而讓美國醫生和管理者糾結的,更多地是一些治療的權利問題、法律問題、道德問題,甚至醫療學術問題。而中國醫生治與不治的依據,更多地糾結在兩個字:命和錢。有錢、還是沒錢!治療能不能掙到錢,病人能不能活命。
首先,中國人的價值觀里,活命是最重要的,不管有沒有意義,活著就行!在活命的問題之下,錢的問題似乎變輕了。誰都清楚,一些病癥當下是無法治愈的,那也要傾家蕩產地去治。只要還能夠承受,或者不用花自己的錢,則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地維持著。一位經濟學家曾講到,中國人一輩子的醫療費,百分之七十,都花在生命的最后三個月里了,或許也就是多維持哪怕幾天、幾個月痛苦的生存。沒有人討論這種無效的生存對生存者還有什么意義;更沒有人討論這些無效的醫療花費,可以為多少兒童做心臟矯正手術,讓多少失明、失聰的人恢復正常人的生活。
當然,錢是誰都繞不開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新的治療手段,需要花太多的錢。病人有沒有錢,會成為一個治不治的問題,這在中國和美國都會遇到。否則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也不會把自己的連任賭上,去搞一個全民醫保的法案。美國同樣有太多的人,因為貧困而治不起病。不過,在美國沒錢治不了病不會成為一個道德問題,醫院和醫生不會為此承擔太多的道德壓力;而在中國,很大程度上會變成醫院的道德問題。人們不會譴責無效維持造成的浪費,卻要求醫生和醫院為無力承擔醫療費用的人,承擔更多道德責任。
另外,醫生在錢的問題上受到責難,還在于中國的醫生更關注于醫療的收入,而美國醫生更多的精力在于治病,治好病就行,有病人自然就有錢。這是因為美國醫生的診治費用本來就畸高。看個感冒,只做簡單地檢查,不開藥,都要二百多美元;而美國醫生的收入一般在人均收入的兩倍以上,對此美國老百姓不會抱怨。在中國,醫生診治費極低。看一個病人,幾塊、十幾塊人民幣;大多數醫生的收入維持在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人們還抱怨看病貴。很多人無視醫生的勞動,而只愿意在藥上花錢,在設備使用費用上花錢。
必須承認,在美國,醫生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當醫生也令人尊重。盡管美國的訴訟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多,美國的醫療官司也多的超乎想象。但是,大多數美國醫生還能夠專心致志地提升他們的技術,踏下心來面對他們的病人。一是,美國的法律既保護病人,也同樣保護醫生;二是,美國有保險。醫療保險,讓很多美國人承受了天價的醫療費用,讓醫生不必為收費,為逃費而操心。此外,美國醫生大都簽有醫療事故險。除非重大責任事故,醫生不用自己承擔。
而這部電視劇讓我們真正看到的,是中國人需要再奮斗幾十年或更久去跨越的精神文化上的差距。說起來,這個文化極為簡單和單純,即不帶有任何個人情感和利益的批評與質詢的文化、一種可以開誠布公地批評與探討業務的文化。這是目前我們所極度欠缺的東西。如果能夠讓人們可以心平氣和地交流認識,拋開所謂的面子、地位與身份進行技術、道德的批評與質詢,我們就能夠讓一些差錯、失誤,以及道德層面的瑕疵,得以迅速修正。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退休主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