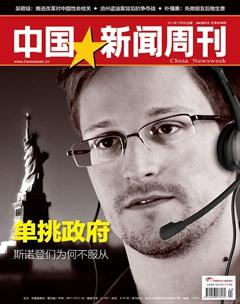健康不平等的解決之道
1842年,英國社會改革家埃德溫·查德威克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最窮的社會階層和上流人士之間,存在30年的預期壽命之差。如今,英國最富裕地區的居民,如肯辛頓和切爾西,他們的預期壽命比格拉斯哥這些最貧窮的城市要高出14歲。
健康方面如此不平等的情況在很多國家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狀況在美國也十分明顯,在美國的某些城市,如新奧爾良,不同階層之間預期壽命的差距可達到25歲。
理解并減少這一健康不平等現象,仍是全世界面臨的主要的公共政策挑戰。這不僅是個道德問題,健康不平等的情況還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成本。但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有爭議的,因此,解決方案一直難以出臺。
健康不平等現象最普遍的原因是基于社會因素,即人們所處的不同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正是因為環境的差異,才導致這種不平等的結果。富裕者更容易獲得促進健康的環境,比如擁有良好環境的優質教育,高質量的住房,安全穩定的工作。而如果越窮者,就越會處于有損健康的環境。
許多理論都吸收了這一基本框架,專家們試圖尋找減少健康不平等現象的不同建議的理論依據,以說服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比如,“社會-文化論”用個體行為的不同,解釋健康狀況的不平等。這種理論認為,窮人之所以健康狀況更差,是因為他們吸煙、飲酒的傾向更明顯,飲食也較為不健康。這一觀點自然地成為定向戒煙服務或健康教育計劃等干預手段的理論基礎。
“物質論”的著眼點更加廣泛。該理論認為,有錢人可以通過優質的教育得到更好的生活環境,更容易通過衛生和社會服務買到更好的健康保障。因此,國家可以通過增加低收入者的低保收入和保證公共服務的全民覆蓋,來減少健康不平等的差異度。
相反,“心理論”則認為,健康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一種心理體驗,即由社會層級差別造成的“劣等人”和“優等人”所導致的結果差異。持這種觀點者提出的解決方案的著眼點認為,貧窮的個人和社區需要感受到自身的價值,進而有能力改變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讓他們被“二等公民”的感覺所吞噬掉,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生命過程論”則將諸多的理論結合起來。按照該理論的主張,社會、心理和生物各方面的優勢和劣勢,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最終積累起來,造成健康的不平等,而這一過程從一個人在子宮中便已開始。因而,該理論要求早期干預,從兒童時期開始,就要讓人走上積極、健康的道路,并組成一個社會安全網,貫穿公民的一生。
對于人群健康的不平等現象的解釋,最廣泛的觀點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派”。該學派指出,健康的不平等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層級結構,以及相應的關于資源分配的政治選擇決定的。這一分析呼吁最徹底的行動:開發一套資源(特別是財富和權力資源)均勻分配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以上這些理論從某種程度上講,都有科學證據的支持,而在決策者決定用哪種戰略思想來減少社會的健康不平等現象的時候,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更大。畢竟,從政治學來講,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更容易和現有的制度緊密結合,并得以有效實施。
比如,其中一些理論的宗旨在于改變對個體行為的干預措施,這種思路對現有權力結構的挑戰,遠比要求大面積的社會投資或改變整個體系要小很多。因此,有意縮小公民健康差距的政府,通常會選擇痛苦相對較小的“下游”干預政策。比如1997~2010年的英國工黨政府就是通過這種路徑而獲得成功的。
但是,這一方法在降低健康不平等方面充其量只是部分的成功。毫無疑問,我們需要更全面、深入的措施。事實上,人類社會在19世紀和20世紀所取得的大部分健康的進步,都是由深遠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帶來的。
總之,一個更趨于平等的社會,才會有更好的公共健康成就。盡管發達國家也存在著健康不平等的問題,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畢竟普遍能夠擁有更好的健康狀況、更長的生命。比如,瑞典和挪威等國家,其最貧困、最脆弱群體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遠遠好于英國和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國家。相比較而言,這些更平等的國家也擁有更穩定、更包容的經濟增長方式,當然也由此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從健康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國家為我們提供了選擇路徑的標本與參照系,進而也提供了一個社會變革的樣本。
克萊爾·班布拉
(作者系英國杜倫大學公共衛生政策教授、沃爾夫森健康和福利研究所主任。著有《工作、失業和衛生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