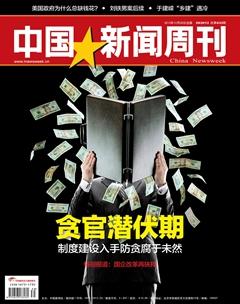辛格訪華:中印加快新一輪經濟合作
徐方清

10月22日晚,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飛抵北京,進行為期三天的訪華行程。僅5個月前,李克強在擔任總理后,首次對外出訪選擇了亞歐四國,印度是第一站,也是停留時間最長的一站。
中印總理上一次在一年中實現互訪還是半個世紀前的事。
1950年,中印建交,印度成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進行了互訪。此后數年,中印關系迎來蜜月期,“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號曾在印度廣為流傳。
“上世紀50年代,中印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在萬隆會議上密切合作,促成會議的成功舉行,雙方的合作在政治外交領域出現了一個高潮;如今,雙方致力于共同謀求發展,(期待)將在經濟、金融這些新領域出現一個新的合作高潮。” 中國前駐印度大使、原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孫玉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工業園”吸引中企投資
此前,印度外交部在介紹辛格此次出訪安排時就透露,中印經貿合作將是辛格此番訪華的重要議題之一。印度媒體報道稱,辛格準備向中方提議,在印度境內建立“中國工業園”,吸引中國企業到印度投資。
這是印度首次專門針對中國企業創設工業園區。此前,印度已設立針對日本、韓國和阿聯酋等國的工業園區,對進駐的企業給予減輕銷售稅等優惠措施。
中國外交部在18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也印證了這個說法。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相關提問時表示,雙方同意重點推進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鐵路及工業園區合作。
“不要把工業園區理解為經濟特區,兩者差得很遠,更不要把工業園區和自貿區相提并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南亞問題專家傅小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印方所提的工業園區其實就是一個外資企業相對集攏的區域,受制于各地方政府的法規和條文,稅收政策上并沒有太大的優惠力度。
擁有兩億人口的北方邦,以及被視為新一代汽車生產基地的西部的吉吉拉特邦等地,是印方希望設立“中國工業園”的地區。印度希望借助于中國企業的資金和技術轉移來刺激國內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升級。
傅小強介紹,印度寄希望于中國企業在“中國工業園”內投資電子產品、電化產品、制藥以及基礎設施等相關產業的生產基地和服務中心。
選擇在人口密集的地區設立“中國工業園”,印度的設想中還有一重考慮——拉動就業。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對外政策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沙塔努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印度政府如今正在推進一項“國家制造業政策”,目標是在2025年將制造業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目前的16%提高至25%,并創造1億個就業崗位。
李克強訪印期間,中印雙方發布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到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只要中印雙方能應對好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個目標還是可行的。” 沙塔努認為。
但作為最近十年平均經濟增速都超過7%的兩大新興經濟體,中印這兩個人口總和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國家,卻在去年遭遇了雙邊貿易額的下滑,從2011年的739億美元回落至665億美元,同比下跌超過10%。
讓沙塔努更擔心的是,中印之間還存在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印度對華貿易赤字嚴重。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逆差國。2012年度,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額約為400億美元,且逆差額仍逐年擴大;而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額仍偏少,約為1.5億美元,不到日本的1/16。
“中國工業園”的設立,不僅將刺激中國企業在印的投資,長遠來看還可能拉升印度出口。在沙塔努看來,平衡中印貿易亦是辛格力推“中國工業園區”的一個重要考量。
作為曾主持印度經濟改革的財長,在2004年入主總理府的辛格,在很多印度人眼里,還是印度最出色的經濟學家。
“新茶馬古道”或助印度走出低谷
孫玉璽說,他在印度當大使的時候,印度就有設立“中國工業園”的意向了,中印雙方也都表示了濃厚的興趣。那是2005年至2007年間。
中國企業也在較早時已開始在印度進行投資,如華為和中興,已在印度投資10余年。不過,這個過程并不順利,中國企業屢屢遭遇“擠壓”。
上世紀60年代中印爆發的一場邊界戰爭,讓印度各界充斥著對中國的安全焦慮和質疑,并使得印度對接受中國投資并不積極。一些正常的、符合雙方利益的中印經貿合作計劃也時常遭遇擱置,而印度方面一些積極推動中印經貿合作的政經界人士,還面臨著“出賣印度利益”“對話軟弱”的指責。
“中國工業園”延擱多年才姍姍來遲,擺上中印政府會談的桌面,和印度國內的這種干擾不無關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直支持深化對華經濟合作的辛格,在這條路上時進時停。
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印后,中印雙方所力推的建設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倡議,亦面臨類似問題和阻力。
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被一些學者稱為“新茶馬古道”,直接相關地區除中國云南省外,還包括孟加拉國、緬甸兩國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爾邦等東北部各邦,總覆蓋面積約165萬平方公里,覆蓋人口達4.4億。
傅小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地緣位置極具優勢的這條走廊直接輻射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幾個大市場,把東亞和南亞連接在一起,對推進地區互聯互通具有重要意義。
這條經濟走廊如能實施,不僅能推動中國大西南的開發,還會促進中國在印緬孟三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在印度前外交秘書埃里克·岡薩夫看來,印度西孟加拉邦也將受益巨大。該邦是印度東部經濟、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與孟、緬及中國西南交往歷史悠久,在印度“東向”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沙塔努所在的加爾各答大學,就位于西孟加拉邦的首府也是印度第三大城市的加爾各答。他指出,四國經濟互補性強是打造這條走廊的優勢,但目前這條走廊覆蓋區域尤其是印緬孟三國相關地區,存在投資環境差、行政效率低和保護主義盛行等問題解決起來頗為棘手。
不過,印度今年經濟陷入低迷,隨著中印政府加大推動力度,借助于中印經貿合作的深化使印度早日走出經濟低谷的思路,開始被更多印度政經界人士和輿論接受。
《印度時報》網站的分析文章指出,當前增進中印兩國經濟關系最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政府目前認為,要提振陷入低迷的經濟,需要將目光投向擴大歐美以外的投資。”印度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所負責人、知名經濟學家拉杰夫·庫馬爾曾呼吁印度更多的印度人支持政府的這一主張。
中印盡力避免負能量的干擾
9月2日,孫玉璽在京出席了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CPIFA)與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ICWA)共同舉辦的首次“CPIFA-ICWA中印關系對話”。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于1949年12月成立,是新中國第一個專門從事人民外交的機構。學會由周恩來總理倡導組辦。成立于1943年的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則是印度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其現任會長是印度副總統哈米德·安薩里。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印期間,在該委員會發表了演講。
“這是中印兩國二軌(民間對民間)關于如何加強中印關系的對話。”孫玉璽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這次會上,與會中印學者都強調了中印關系發展與加強經貿合作的重要性,并認為中印兩國領導人和政府會盡力避免負能量的干擾。“誰要老說中印關系不好,我們這些長期搞中印關系的人就會恨得牙根直癢癢。”
“中印間有太多的正能量,但長時間來,負能量卻一直被輿論放大。”孫玉璽說。
除了不時冒出的“中國威脅”,在每一次中印關系出現積極向好的重要事件時,印度媒體還總有“邊界爭端”的新聞出來。在5月份李克強訪印前夕,“帳篷對峙”事件被熱炒超過兩周,一時間“中國入侵論”在印度甚囂塵上。此番辛格訪華前,印度媒體也就“兩名來自爭議領土地區的印度運動員來中國參賽遭拒”吵作一團。
但這一次的事件未像5個月前的“帳篷對峙”事件那樣引發軒然大波。除了事態本身輕重程度有別,在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對外政策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沙塔努看來,“中印之間已經建立了有效的雙邊磋商和對話機制,并在金磚五國、G20和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中也有頻繁的會面和溝通,這種關系的穩定和成熟度已足夠化解一些小糾紛。” 而五個月前的有些糟糕的情況,和印度政府一開始對事態后果估計不足有關。
2003年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機制建立。兩年后,中印兩國政府簽署《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協定》。是年出任中國駐印度大使的孫玉璽回憶說,該原則確定雙方都不再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解決邊界問題,且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不應讓其影響兩國關系的整體發展。
如今,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已進行了15次會晤,雙方還陸續在解決邊界問題上推出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等一系列機制。
此番辛格來訪,中印探討如何完善工作機制、提高處理邊界問題的能力和效率,并簽署涉及邊防合作等多個領域的一系列雙邊協議,繼續增強雙方抵抗“負能量”干擾的能力;與此同時,中印放寬對中國公民赴印簽證限制,推進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國工業園”構想,還為中印關系的前行注入新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