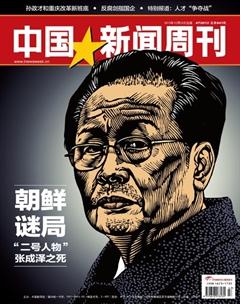公共政策避免留下后遺癥
鄧聿文
北京要提高地鐵票價,天津要對汽車限購和限行,中國這兩大緊鄰的直轄市和將要出臺的公共政策,遭到了廣大民眾的吐槽。
北京2元地鐵票價政策,迄今已經實行了7年。盡管當初是為了奧運會而做出的決策,但因為它確實讓民眾嘗到了政策帶來的益處,所以,從政策效果來看,民眾是滿意的。
而天津對小汽車的限購,居然在宣布次日就開始實施,并且不僅限購,還要限行,這樣的決策,充分顯示出政策制定者的專橫意志,似乎沒有顧及公眾的情緒與意見。
北京提高地鐵票價的理由是,通過價格杠桿分散高峰時段客流壓力,降低大客流風險。據說因為票價低,把大量人群在高峰時段引向地鐵,甚至使那些“可乘可不乘的人,都選擇地鐵出行”,致使人滿為患,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因而要利用價格杠桿作用,將軌道交通人流向地面交通進行分流,有利于城市公共交通結構趨于合理。
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人們在高峰時段選擇地鐵出行,固有票價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地鐵準時。何況,在北京高峰時段非常擁擠的13號線、5號線、4號線、八通線等線路,上下班的潮汐性客流特征非常明顯。對于此種出行剛需,高峰時段要將票價提高到多少才能使人們放棄地鐵而改行其他交通工具?恐怕提價少了無濟于事,多了會引發乘客不滿,也有悖于公共交通的優先屬性。在這方面,一個例子是上海,上海倒是實行差別票價,可高峰時段地鐵同樣擁擠。
至于說低票價會誘使“可乘可不乘的人”選擇地鐵出行,更毫無道理。既然“可乘可不乘”,誰愿在高峰時段擠地鐵遭那份罪受?
所以,北京提高票價的唯一理由,就是所謂補貼過多。據說北京每年補貼地鐵180億元,這個數字確實很大,政府財政補貼不起。出行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需求,尤其很多人的出行是因為工作,因此,將大量財政補貼用在民生基本需求上有什么不好?這不正符合公共財政的目的與性質嗎?而且,像公共交通,具有乘數效應,坐的人越多,補貼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如果說政府財政負擔不起,為什么不減少政府自身其他非必要的開銷而一定要削減補貼,把負擔轉嫁給民眾?再說,地鐵公司說它虧損了那么多,這個虧損是因為坐地鐵的人多導致的,還是政府和地鐵公司的管理不善引起的,地鐵公司的賬本向公眾公布過嗎?
天津限購限行的理由是交通擁堵,這更是個偷懶的理由。天津的交通擁堵恐怕不是今日才造成的,以前采取過何種得力的緩堵措施?如果沒有,為什么一上來就要實行這種限制人們出行自由的政策?北京為治堵,迄今采取了諸如尾號限行、搖號購車、停車費漲價、開辟公交專用線、發展軌道交通等措施,然城區的交通擁堵狀況并未得到緩解,甚至更厲害,這其中的教訓何在,天津應該反思。
最近幾年來,人們看到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怪現象,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價格低了,提高價格;路上堵了,限制買車;闖紅燈了,闖黃燈扣分;房子漲了,限貸限購,等等。政府除了提價、限購外,似乎拿不出好的辦法來。這種政策制定方式,不看導致問題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只在表象上做文章,結果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使問題進一步擴大化或嚴重化。不客氣地說,許多問題,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
因此,可說此種政策制定方式,是一種嚴重的懶政。它反映了政府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實為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低下的表現。
以上述兩類來說,北京地鐵擁擠和天津交通擁堵,根源是什么?首先是全國資源分配不均,多數資源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傾斜的結果。人是跟著資源跑的,哪兒資源豐厚,人們自然往這個地方擁來。其次是城市內部的功能分區和資源配置失衡,這在北京尤其突出。就業功能和居住功能都比較集中,幾個大型的居住小區號稱“睡城”,焉能不堵?第三是公共交通,尤其是軌道交通的建設,滿足不了民眾出行需求的增長。
由于前兩者涉及到既得利益問題,解決起來困難重重,或者超出了自己的權限范圍,于是政策制定者就采取簡單粗暴的提價或限購方式,這種方式最省事,可代價卻是廣大公民受損害。
解決交通擁堵的問題,中長期而言,根本出路在于合理調整城市規劃,在功能分區上做出適當調整,不能因為它難就不去做。而就現階段來說,即使有必要適當提價,也必須廣泛征求民意,在公眾同意的基礎上制定價格,且過程要透明、合理。另外,就是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繼續倡導公交出行,改變路網狀況。
公共政策因涉及到多數人利益,政策出臺更要慎重、考慮周全。考慮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臺的政策、措施向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很可能引起其他城市效仿,盡可能避免留下后遺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