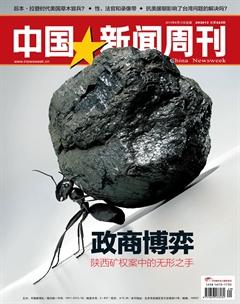后本·拉登時代美國草木皆兵?
徐方清

8月,是美國的度假旺季。
8月1日,美國政府宣布于4日關閉主要處于穆斯林世界的21處駐外使領館,后又增加一處,并將其中19處使領館的關閉時間延長為一周。2日,美國發布全球旅行警告,告誡美國人“基地組織”可能正在籌劃8月發動襲擊,威脅尤其存在于中東和北非。但這一切,并未影響到計劃在國內度假的美國人的既定行程,包括他們的總統。
當地時間8月5日下午,回到白宮的奧巴馬對著媒體的鏡頭微笑揮手,一臉輕松。此前兩天,奧巴馬攜全家在總統度假勝地戴維營度過了今年的生日假期。美國開始關閉22處駐外使領館的8月4日,恰好是奧巴馬52歲的生日。
在動蕩加劇的中東北非,“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使領館如臨大敵,閉館戒備。一直以來,美國就是極端組織的襲擊對象,尤其是9·11后美國不惜發動戰爭進行強勢反恐以來,反恐就是一個永遠的課題。
破天荒的舉動
一年前, 9·11事件11周年紀念日當天,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等4名美國外交官在位于班加西的美國領事館遇襲身亡。
“奧巴馬沒有充分保護在班加西的美國人的生命安全,”當時在美國大選中處于劣勢的共和黨人攻擊火力全開,尋求將此次襲擊事件歸咎于奧巴馬的大意和失察。之前的幾個月里,美國政府多次獲得情報,一些與“基地組織”有關聯的伊斯蘭主義極端分子在距離班加西不遠的山區進行集訓。
共和黨人沒能因此在兩個月之后的美國大選中阻止奧巴馬的連任,失利之后的他們仍就這次“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對繼續掌舵白宮的民主黨喋喋不休。
一年之后,當奧巴馬政府再度接到顯示美國使領館遭襲擊危險增加的情報,雖然總統仍去悠閑地度過了自己的生日假期,卻沒有再像去年那樣對這些情報無動于衷。
在奧巴馬開始度假前,8月3日一早,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主持了政府高層緊急會議,商討“基地組織”可能在8月10日拉瑪丹齋月結束前后發動恐怖襲擊的對策。與會者包括美國國務卿克里、國防部長哈格爾、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以及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局長等。沒有出席會議的奧巴馬在會后聽取了匯報。
雖然美國政府發出了全球旅行警告,共計關閉了22處駐外使領館,并將初定的兩天關閉時間延長為一周,卻一直未透露采取如此大動作的具體原因。
出于安全原因關閉使領館,對于美國來說并非新鮮事,但即便在1977年就開始在國務院從事外交事務的克里斯托弗·希爾看來,關閉從中東到北非的幾乎全部美國使領館,這是破天荒的一次舉動。“反正我是平生第一次見到。”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這位已經年屆七旬、一頭白發的美國前駐伊拉克大使說。
美國此次關閉的駐17個國家的使領館中,有10個國家位于中東地區,包括阿聯酋、約旦、伊拉克、卡塔爾、沙特、阿富汗、科威特、巴林、阿曼和也門;其次是駐北非國家的使領館,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吉布提、蘇丹、毛里塔尼亞以及利比亞;剩余一個則是駐南亞國家孟加拉大使館。
高危時段
9·11之后,憑借對“基地組織”等恐怖勢力的軍事打擊以及美國國內嚴密的安保體系,盡管不惜侵犯隱私的貼身安檢以及無人機反恐頻頻誤殺平民備受爭議,但換來了美國本土再未遭重大恐怖襲擊的太平歲月。
本土之外,恐怖勢力卻一刻也未讓美國心里安寧。早在9·11之前的1998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附近相繼發生爆炸,造成兩百多人死亡,死者中包括美國駐肯尼亞大使館總領事及其兒子等12名美國人,是美國外交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一頁”。
每一年的9月11日前后,美國駐外使領館尤其是位于恐怖勢力活躍地區的使領館,更成為高危時間段。在9·11之后,美國駐外使領館已共計遭受過百余次襲擊,最近的一次,則是去年導致斯蒂文斯等4名美國外交官死亡的班加西悲劇。
對于此次閉館事件,美國政府迄今仍未公布具體所驚為何。美國媒體梳理出兩條主要線索:一條是美國情報部門日前截獲了兩名“基地組織”頭目在電子設備上的部分交談內容,其中提到該組織在巴基斯坦的頭目扎瓦希里下令也門分支頭目在周日(8月4日)發動襲擊;另外一條則是伊拉克、利比亞和巴基斯坦等多個國家近期接連發生越獄事件,都和“基地組織”有關聯。國際刑警組織8月3日發布的全球安全警告稱,僅僅過去一個月,已經有數百名恐怖分子和其他罪犯逃出監獄,其中包括一些“基地組織”的高層。
盡管奧巴馬政府沒有像去年那樣在獲得一些班加西領館可能將遭襲擊的情報后按兵不動,但共和黨人仍就對其不依不饒,稱奧巴馬今年“反應過度”。
“相比被襲擊的嚴重后果,關閉使領館帶來的不便和損失算不上什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美國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的助理政策分析師簡森·坎貝爾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政府的決定不會是輕率做出的,需要權衡多種因素,其中班加西的慘痛教訓,是政府決策者不能不考慮的。
按照美國政府的說法,情報顯示,恐怖勢力此次可能“以西方為目標,不止涉及美國的利益”。不過,英德法以及加拿大都只采取了相對有限的防范措施。英德法目前只關閉了位于恐怖活動最活躍的也門的使館,而加拿大則關閉了駐孟加拉首都達卡的大使館。
更難對付的散兵游勇
8月3日開始,在也門首都薩那的,通往美國駐也門使館的道路已被封鎖,也門安全部隊調出坦克和裝甲車開到使館附近,并部署了少量特種部隊。在宣布閉館的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使領館前,驟然加強的戒備讓這些平常承擔著同所在國政府和民眾進行溝通的使領館一下子森嚴起來,難以靠近。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安全與軍控研究所所長、反恐問題專家李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關閉使領館加強戒備的做法通常是在使領館的周邊又加設一個禁區,會加大恐怖分子實施襲擊的難度。“恐怖分子選擇硬碰硬的可能性很小。”他說。
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議員特德·波質疑奧巴馬政府動作過大,特德·波還是美國眾議院防止恐怖與核擴散委員會的主席。他所擔憂的事情是接下來美國政府要面對的難題:使領館可能遭襲擊的情報隨時可能再度傳來,恐怖分子的襲擊更隨時可能發生,但美國使領館不能一直關下去。
9·11以來,美國通過阿富汗戰爭以及一場又一場“外科手術”打擊清除了一個又一個“基地組織”的重要頭目,重傷該組織元氣,兩年前擊斃“基地組織”頭號人物本·拉登,更是奧巴馬首個總統任期內的備受美國民眾認可的成績。
然而,超過百次針對美國駐外使領館發起的恐怖襲擊讓美國人本土的太平歲月里摻進了一些憂傷與悲愴。這些襲擊的殺傷力通常不大,卻時刻牽動著白宮的神經。讓奧巴馬有些無奈的是,他可以有辦法干掉本·拉登,卻很難找到對付這些“散兵游勇”的良方。
核心領導人接連被美國定點清除后,“基地組織”各地分支顯得更加分散,但體量變小的這些分支卻顯現出更強的自治能力,使得美國追蹤其領導人并進行打擊的難度大幅增加。
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中央情報局資深專家、現任布魯金斯情報項目負責人的里德爾說:如今美國面臨的問題是,與過去相比,2013年伊斯蘭世界的“基地組織”成員和分支數量可能變得更多了,這主要是阿拉伯之春過后的混亂局面所導致的。
紛亂的中東北非不僅給散布在此地的“基地組織”提供了大量渾水摸魚的機會,這里的民眾對于局勢的不滿和憤怒情緒也更多地朝向長期在此“攪局”的美國。
去年,一部褻瀆穆斯林先知的電影激起了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浪潮;今年,埃及再陷動蕩后,美國駐埃及女大使帕特森的畫像印在開羅解放廣場的條幅上,要么臉上被打上了血紅色的大叉,要么扭曲的面部上還寫著罵人的臟話。
讓里德爾最擔心的是,憤怒的人群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了站在“基地組織”一邊,他們在反美立場上找到了共同語言。而混雜在中東世界群眾游行隊伍中的恐怖勢力,不僅其危險難以估量,還會讓美國的無人機和特種兵無從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