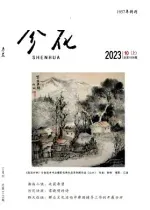凱歌小小說二題
凱歌
聽瑟
洛陽城外。歪脖兒柳下。
爐膛中灼然跳動著藍色的精靈,頑皮而輕盈。鐵錘雀躍著在空中劃過一個又一個圓,空氣中不斷留下一首首鏗鏘的歡歌,讓這個夏天顯得浪漫而熱情。
終于,嵇康放下鐵錘,拍拍衣襟,一屁股貼在青石上,美美地吐出一串舒心的感嘆,眼神直勾勾瞄向天上的白云。
在嵇康眼里,這就是詩,就是生活。每天為詩而生活,又為生活而歌,該是人生最愜意的不是。
涼風不來,樹杈上紫燕的呢喃似乎成了一種聒噪。楚冠帛衣者早已是汗流浹背,滲合著油膩的汗珠沿著紅肥的脖子滑落下來,每張臉此刻扭曲得變了形,個個寫上了問號。
鐘會笑瞇瞇地侍立一旁,不慍不惱,畢恭畢敬。
鐘會是來學琴的,學的是嵇康的《廣陵散》。嵇康有一首曲子,就是《廣陵散》。《廣陵散》世人難得一聞,所以鐘會帶來了千金,還有滿滿一車綾羅綢緞。
顯然,貴公子這次是熱臉貼了冷屁股,嵇康很沒給面子,讓他和他那幫腦滿腸肥的朋友曬了半晌的太陽。最后,鐘會只好帶著他們悻悻地離去了。
袁準也來了,帶著一筐自己的詩文和滿腦子的奇思怪想。在請教了嵇康一些問題后說,我想學《廣陵散》。
聽到這話,嵇康沉默好久,說《廣陵散》柔中藏鋒,將人情和天理攙和其中,聞得人寰塵音,弦外卻是世外之情,是要引進取之士誤入迷途的,就拒絕了袁準的請求。
不久,袁準再訪,仍念念不忘《廣陵散》。嵇康嘆口氣說,世人都是這般癡心,卻不知道一片癡心能否頓悟了這曲中的清風明月,流水高山。
嵇康就擺設了一個琴宴,準備彈奏《廣陵散》。起初并沒有邀請太多的人,但天下仕宦賢達還是聞風而來,包括那位對嵇康又敬又恨的鐘會。
那琴聲初起,宛若游絲裊空,輕曼氤氳,又似情人喁喁細雨,纏綿悱惻,一下子把人們帶入了那種浪漫多情的迷離世界。待琴聲歇而再起,卻似響箭穿空,驚濤拍岸,萬馬奔騰,千軍赴敵……眾人聽得胸中激越跌宕,如醉如癡,待一曲告終,已是眼神迷離,心中恍惚。
嵇康連叫了兩聲袁準的名字說,你看到了什么?
袁準定了定神說,學生見忠義之俠士怒發沖冠,氣凌云霄,為了恪守心中信念,不畏強暴,挺身而前,悲壯至極。
嵇康又問,鐘會先生呢?
鐘會忙起身揖禮說,學生見到大丈夫為了無名富貴,大膽而驅,不論前方是茫茫滄海,還是萬丈深淵,亦當身先士卒,一往無前。
嵇康說,琴為心聲,聞者亦可聞真性情也。袁準之心忠正樸誠,恐難在這天地之間容身長久。鐘會貪念太多,邪氣浸心,以后登堂高室,可忠心侍上,方求富貴周全。
眾人大笑。鐘會咬著牙狠狠地說道,謝先生賜教。
當朝天子聽說了嵇康的風采,幾次招納嵇康做官,都遭到嵇康的婉言謝絕。鐘會乘機落井下石說,嵇康并非無意為官,而是不忘前朝,不愿輔佐晉室天下,若不除去此人,當今讀書人會競相效仿,這天下還不亂了套。
天子下旨,必殺嵇康。
三千多名讀書人慕嵇康才名,集體上書,請求拜嵇康為師,請朝廷赦免嵇康。朝廷不準。
嵇康臨刑前,神色不變,靜靜地望著天上飛翔的鴻鳥,索來古琴,盤腿彈奏了起來,身形似流水高山清風明月下的一棵孤松。
袁準擠在黑鴉鴉的送行人群當中,聽著那悠閑白若的琴聲已是淚流滿面,他終于明白了嵇康所說的話。
不久,手握重兵的鐘會貪心不足,意圖謀反,被手下人告了密,結果自己連同整個家族都被天子誅殺。
袁準領著全家屯歸田園,每當明月高懸,松風送來,袁準就領著兒子盤身按琴,快樂地彈奏起那首《廣陵散》。
彈著彈著,袁準面前就出現了一幅圖畫:清風明月,流水高山。
畫竹
清風流園,蟬鳴夏廊。
知縣搖搭著“天地玄黃”的墨扇徘徊在秀才郭仲的后花園。郭秀才的府第簡單得不過幾問瓦房連成一片,后花園植種的大片大片的青竹在微風中搖曳著婀娜的身姿。
上次造訪,知縣吃了郭秀才的閉門羹,郭秀才說咱一個草野老叟,怎么敢和朝廷的官員攪合在一起,萬一得罪了誰那可是吃罪不起的,還是不見的好吧。二次登門的知縣帶了一大塊兒麻布片兒,裹上干草朝墻里扔了進去。一袋煙工夫,從門里扔出來一只大麻袋,里面結結實實塞滿了草,并附紙箋一封:知縣大人以草野自居,但老叟確是一個大草包,區區門檻是要屈就大駕的!郭秀才還是閉門不見。知縣罵了一聲老犟驢,不覺啞然失笑。
知縣讓人取來筆墨,一筆勾出一幅蘭花圖,遣人呈上。不一刻,一個瘦高清矍的布衣老者大踏步出來,兩眸發亮地吹著胡子喊:鄭克柔何在?哪位是鄭克柔?
知縣笑瞇瞇地上前施禮:草包鄭克柔見過郭仲先生!
郭仲將知縣迎進內堂,將一幅蘭花圖品了又品,嘖嘖地說,早聞鄭克柔的蘭草丹青出手不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
知縣又繪了一幅翠竹圖:小石徑兩側嫩竹成行,綠野盈盈,內問又有春筍萌生,光艷可人,畫上景致正取白郭仲后花園竹林。
郭仲哈哈大笑:好一幅丹青妙筆,若非成竹于胸,豈有這等的功夫!說話間,郭仲神色凝重地在這翠竹圖上提按轉側,粗細頓折,寥寥數筆間,那翠竹竟然儀態萌發,情趣頓生,宛若天成,靈氣與神韻渾然凝聚于一紙問。
知縣看得目瞪口呆,方覺先前之作黯然失色。
此地果真是藏龍臥虎,知縣想著不覺自慚形穢,臨行將郭仲點墨之作要了回去,說要潛心參納。
老妻說,你的名氣也不小呀,干嘛還要學人家的畫呢?
知縣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咱這兩下子算個屁!神韻來自心下,看來勝出這犟老頭兒一頭還得花費上一番心思呢。
衙門無竹,知縣就一股腦兒往郭仲家里跑,每次總要帶上一壺好酒。瞧著知縣如癡如醉地欣賞竹畫,郭仲捋著胡須品酌上一口酒,咂巴著嘴說難得難得。
郭仲的竹確實是出了名的好。每年畫壇的腕兒們都要舉行一次畫宴,畫壇好手們都會拿出自己的得意手筆或私宅珍藏斟討切磋,引得一些附庸風雅的富賈商豪競相購買,布飾門庭,郭仲的竹每次都能賣上個好價錢。
如此,五年光陰過去。
轉眼間,一年一度的畫宴又至,在宴會上,郭仲的畫白當如旭日東升,引得圍觀之人喝彩連連。郭仲當場潑墨而成的兩幅翠竹丹青被本地的幾個鹽商搶購一空,且每一幅開價都是數十兩紋銀。郭仲樂在心頭,臉上不免平添了幾分得意之色。
郭仲正沉溺在眾人的溢美之辭中,忽聽有人大喊“妙哉”!原來有人得了一幅翠竹古卷,眾人正在那里品賞把玩,且不時發出一陣嘖嘖聲。
古人的青竹圖?是宋代的文與可還是元代的柯九思?郭仲瞇起眼微笑著湊上前去。這一瞧不打緊,只驚得兩眼瞳仁放大了許多,那竹鹿角分明,直立云中,竹葉輕搖一側,濃淡一色,疏密有致,似動非動,似靜非靜,全卷不著一個風字,卻處處見風,畫名風竹圖,大有天成之韻,古賢之風。
郭仲看得如癡如醉,心下吃了一驚:畫壇中竟然有這樣的丹青高手,自己竟渾然不知。
在眾人的品咂贊嘆聲中,這幅風竹圖被賣到了五百兩紋銀,第一次超出了畫壇名宿郭仲的竹。
回來的郭仲就病了。家人四處求醫。知縣聞訊匆匆趕來,得知原委后默不作聲。
郭仲再作畫,顯然少了幾分天然神來之筆。每次一提筆,總是顯得有些遲疑和顧慮,眼神中也多了一絲迷茫。
說來也奇怪,那封未曾落款的風竹圖再也沒有在大家面前出現過,眾人也好似忘了那幅古畫,這事兒就像一下子從人間蒸發了一樣。
知縣還是像往常一樣在處理完公務后,提上一壺好酒,屁顛屁顛地去郭仲那里作畫求教。畫到滿意之處,郭仲連聲稱贊,知縣稍有懈怠,畫得有些不成體統時,老頭子便生氣地沖知縣吹胡子瞪眼。
幾年過去,郭仲一日提筆作畫,忽然雙手一麻,整個身子軟癱下去。一病數日,郭仲自知大限已到,安排好后事并囑托家人請知縣前來一敘。
郭仲握著知縣的手吃力地說著話,聲音低得只有知縣能聽到,只有知縣能聽懂,郭仲說,那畫兒……并非古卷……乃當世高手所繪……手筆當在老夫之上矣……日后見過可替老夫向他致謝!
郭仲雙目死死地盯著知縣,溘然而逝。
一代畫師仙逝,畫壇大慟,達官賢士紛紛趕來憑吊。
吁噓哀嘆之后,一切歸于籟寂。知縣在郭仲墳前深深地三個鞠躬,抬頭時已是淚流滿面。知縣說,郭兄呵,你我情同手足,又有師徒之義,如何拘泥了那世俗塵念呢?知縣讓人取來文房四寶,繪了兩幅丹青焚祭郭仲。一幅是蘭草圖,一幅是風竹圖,那蘭草凈雅靈淑,風姿翩翩;那竹高峻挺拔,直聳云端,這一對蘭竹圖大有天成之韻,古賢之風,左側落款:鄭板橋。
(責任編輯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