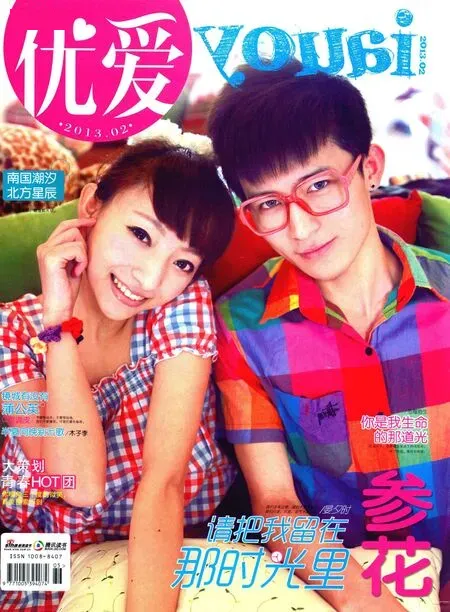草垛的溫度
王善余
我一直以為,草垛是鄉村的標志性建筑,有如城市崛起的高樓大廈,這么說或許有些矯情。其實,四平八穩的草垛,更像鄉村聳起的乳房,顯示著鄉村的活力、尊嚴與榮耀。
的確,草垛沒有樓宇的架勢,就像鄉下人沒有城里人的氣質一樣,“草根”、“一介草民”之類文化人口中吐出的詞,弦外之音不是草與民之卑微嗎?
然而,這不過是居住于樓宇的所謂的文化人的錯覺。在鄉下人看來,草垛是溫熱的,實實在在,觸手可及,豈是縹緲的冷漠的樓宇所能及!
收割碾壓之后,豐滿的麥秸、稻稈交出了糧食,身子干癟而泛著光澤,像產后的母親,一副安詳自足的樣子。盛夏或深秋,人們做完曬糧、入倉、耕種之類的緊要事情,才能騰出時間堆草垛——這意味著一季農事的終結。
堆草垛是男人們的活兒,像是一個神圣的儀式,檢閱著男人們的耐心和虔誠。
父親選了靠樹的空地,猛灌一壺涼茶,勒緊褲腰,揮動草叉,將麥秸或稻草高高堆起。約有人把高,父親上了垛頂,由母親將草遞上去,再接著堆。父親像個建筑師,草垛在父親的腳下慢慢升高。父親舞蹈般地扭著身子,不時抬腳將垛頂踩實、踏平,動作相當柔韌。母親忽然撲哧笑了,說草堆歪了,父親就耐著性子修正,以免日后草垛傾斜或倒塌。
經過一番修整,草垛有了蒙古包一樣渾圓光滑的造型,父親坐在草垛邊一個勁地端詳,有鑒賞的意思了。
家家戶戶房前屋后立起了高高矮矮的草垛,宛如村莊里怒放著的碩大的花朵,既渲染著村莊的心情,也昭示了日月的厚實。村里的老人拄著拐,將軍一樣在草垛間巡視,說父親的草垛堆得周正。
農閑了,人們的熱情向草垛集結。莊稼人倚著草垛圍成一團,說些農事,嘮些家常,身上沾了草屑也不嫌棄。有時連飯也端到草垛處吃,似乎這樣才吃得踏實。月光朗照的時候,情絲縷縷的青年男女,往往在草垛邊完成鄉村式的情感交接。他們含羞的低語,偶爾會被鉆在草垛里的鳥捕獲,鳥帶著這一令人心動的秘密,撲棱棱飛上樹梢……
在農家備受貧困煎熬的時光里,草垛自是不可或缺。
入冬,凌厲的風在草垛上環繞,草垛瑟縮著抱緊了村莊,用綿軟的身體驅趕著堅硬的寒冷。土墻草頂的農舍,顯然成了在困頓中行走的莊稼人的一份憂愁。憂愁中想到了草垛。草揣著陽光,揣著清香,登堂入室,走到葦席下,走到鞋子里,溫暖著清冽的夢和紅腫的腳。
有時,父親還會在草垛下發現驚喜——草垛底藏著一粒粒麥子或稻谷。父親喜出望外,小心翼翼地掀起底層的草,掃出些許糧食,讓母親激動得不知所措。這個發現觸動了全村人,一時間,男女老少涌向鄉場,在草垛里翻找,如同淘金,多少有些收獲。
草垛不像城市的樓宇那樣嫌貧愛富,它安然地坦蕩地守在戶外,沒有緊閉的門,沒有堅硬的鎖,慷慨接納任何需求。比如,張家的煙囪歇著了,就去李家的草垛扯草,李家人斷不會阻攔,只說盡管扯去燒吧。于是,裊裊炊煙氤氳出濃濃鄉情。天寒地凍時節,流浪的乞者極少涉足城市,因為城市沒有多少想頭,就去了鄉村,投奔草垛——那是他們的家。吃飽喝足了,窩在草垛里,浴著冬日的暖陽,瞇著惺忪的睡眼,愜意著呢。
就連牛啊羊啊這些牲畜,也得了恩惠,從草垛那兒飽了肚子,取了溫暖。
草垛以溫柔的濃烈的情愫偎貼著與之相濡以沫的村莊,熱吻著在困厄中跋涉的農人的心,以至,成了一些人生命的歸宿。據說,村里一位老人扯草時就死在草垛里。當時下著雪,老人躺在草垛口,身上干干凈凈的,沒落一粒雪花。上了年紀的人就羨慕了,說老家伙堆了一輩子草垛,燒了一輩子草,末了還是被草垛收了,沒凍著。
時間像是打了個手勢,村莊就變了。人們走向城市,翻開生命新的章節。收割、碾壓、垛草之類的忙碌景象已被時光凍結。草垛和村莊一同萎縮。
站在樓宇的頂端,或攀爬在城市的骨骼上,鳥瞰都市的繁華,仰望深空的蒼茫,那些別卻村莊的人們,是否會騰出時問,用心觸摸村莊,還有草垛的溫度。
(責任編輯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