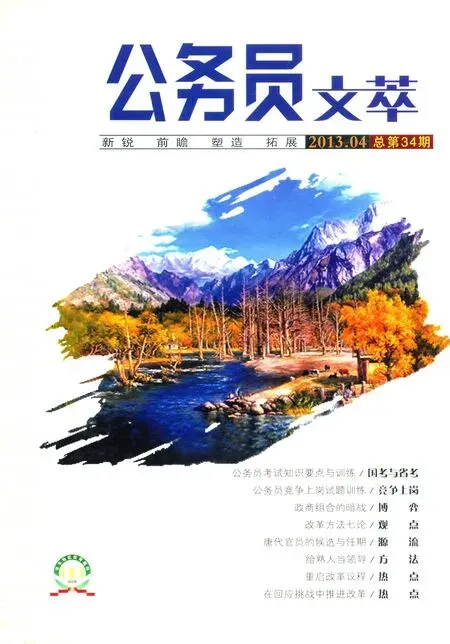新的群體政治與黨的領導
◎石之瑜
新的群體政治與黨的領導
◎石之瑜

以黨護群的時代不再,新時代要求的是以群護黨保護并呼喚黨在制度上轉化成超然的群體象征,領導群眾維系和諧
維護群體與維護黨
近代史上,黨在維系中國這個群體的奮斗中,經歷過無數挑戰,也不斷進行調整。進入多元化時代以后,黨在思想與政策上遭遇的嚴峻挑戰接踵而來,包括有:多元利益之間的相互責任如何安排;不同價值觀的彼此詰難如何規范;黨作為利益與權力主體之性質為何等。一言以蔽之,中國作為群體如何維系、如何調適,正繼續考驗著中國人,也考驗著黨。
在我國,最大的群己關系表現成黨群關系,而黨群關系則表現成干群關系,故每次遇有危機,黨便檢討干部的作風與思想,以確保民主與集中并重,十八大仍延續著此思路。但在進入多元利益時代后,抓緊干部仍不足以維系群。
隨著政治經濟現實的變遷,群體不斷重組,社會成員不斷產生新的自我認識,歷史在辯證中演化,對于既有的群己關系不斷地加以否定。變遷的群己互動終會累積成脫離既有模式的壓力,而要重新建立群己關系,靠的不外乎斗與和兩端,有時通過斗爭,有時通過調整。在建政之初,黨得以建立并領導群體的原因,是仰賴在民族求生存的反帝斗爭中順天應時。之后幾次發生的黨脫離群眾的危機,是靠黨自身的組織重整與精神建設而度過。現在進入多元化時代,群體意識不但日趨模糊,甚至因為自由主義話語的流行而失去正當性,以至于次群體或個人顯得不可一世。自由主義者或謂以美歐民主化取代黨方能維系群體,并消解民族主義,但黨之不存,群將焉附?而沒有群的意識,民主化進程中的內部矛盾即刻會上升成敵我矛盾。可見,認識“以群護黨”的新政治,應是刻不容緩。
黨須作為群體最高象征,傳承精神與制度上的共同寄托
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根據自己的經驗假定,凡不是直接民選的政府必然不得人心,于是訴諸民族主義轉移社會不滿,也因此他們首先建議消弭民族主義,憧憬民主化成為化解國際危機與社會不滿的良方。
從日本右翼在民主體制中崛起的教訓看來,民主與否不是民族主義興衰的栓閥,而日本反華的民族主義根源,更早還可以回溯到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這一點剛好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類似。如此救亡圖存、抵抗強權的民族主義,正是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歷史背景。固然,隨著科學發展觀與和諧世界指導黨的思想與政策以來,民族主義不再具備思想上的生產性,但卻也不是完全失去了作用。
黨作為中國人的群體象征,與民族主義是分不開的,與其照外國專家說黨需要民族主義來鞏固統治的正當性,不如按照自己歷史經驗說是近代史上維系群體的需要,賦予了黨作為群體象征的必然角色。即使在當前政治經濟現實里,黨很難還維持超然,卻繼續是傳承群體意識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多元化時代里這樣的傳承如何演進,是黨的建設必須回答的思想挑戰,在與時俱進的答案浮現之前,民族主義有其臨時功能。
所以,縱使民族主義未必是全球化時代里中國人理解群性的妥適方案,且任何人若想刻意動員民族主義也未必有效,但是更重要的仍然是,群之所系以及因而衍生的對群的需要及對黨的期盼,不容日益流行的自由主義者將民族主義單純貶抑為由上而下的政治操作。認為中國未來只能靠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在臨摹美歐話語之際不察,總是靠抽象邏輯就想將群性抹煞,他們才是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遭到去歷史化與工具化的始作俑者,而使民族主義有淪為純粹政治動員工具之虞。
以整黨、建黨鞏固群體意識的黨,過去似乎總能在危機中自覺糾錯與改革,膾炙人口的例子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何領導群眾,是黨的歷史中貫徹始終的命題。從十三屆六中全會發布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議,到十六大將“三個代表”作為重要思想列入黨章,十六大后接著推動保持先進性教育,再到十七大在黨章中加入科學發展觀,均是從理論、制度與知識上提升干部素質。而其間較少反省的則是,多元化的群眾對黨具有的強烈依賴之心。
群眾不是同質的。2012年春夏之交,人民日報以25篇評論文章,提醒干部認識、注意、包容、妥善處理社會的異質性,尤其警惕將異質思想當成敵我矛盾來對待,避免不當卷入矛盾而背負民怨。對群眾之中存在利益沖突與對社會上存在異質思想,黨能如此坦然面對,謀求合情合理的化解,不啻已是探究新時代群己關系的有益嘗試。但更需要面對處理黨內日增的沖突與異質性。
黨在調解群眾或利益集團間的沖突時能具有威信,其前提在于無產階級政黨沒有采行局部利益立場。改革開放以來,干部身先士卒參與示范而受益在所難免,身居要津上下其手而尋租發跡者不乏其人,權錢交易如魚得水而更上層樓者也并不鮮見,這些均不時重創黨的威信。黨的群眾化與多元化于焉發生,黨內民主的呼吁甚高,與黨的建設并駕齊驅,前者主張改革決策機制,后者重視黨的純潔性。
保持黨的純潔性是當代中國群己關系的基礎。隨著利益多元化與持續改革,這不但是黨的建設目標,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群體未來發展所不可繞過的重要事件。也就是說,在社會利益結構不斷分化、強人領導時代一去不返、民族主義不足以因應內外變局等等形勢中,黨介于如春筍般分化的利益群體與八方流動的社會成員之間,因其所處的歷史脈絡,須作為群體最高象征,傳承精神與制度上的共同寄托。
從權力集中到以群護黨
長期以來,黨的建設主要是在黨作為權力主體的政治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重點常在思想建設與道德建設上。如今十八大召開,黨的建設進一步向制度層面邁進,把政治民主提上議程,首先是深化黨內民主,接著是提高人民民主。唯歷史經驗與港臺經驗顯示,民主對于群己關系的挑戰至巨。是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思索民主如何有助于群的維系。準此,人民民主必不同于自由民主。
黨若是權力的主體,便要在多元利益之間取舍,則民主的含義便至少包含三方面:一是對黨權力的監督;二是對黨決策的參與;三是對黨人事的同意。在實踐上,黨就頗難繼續代表群的整體,甚至黨自身都只能成為程序化的代名詞,而不能成為群。這正是中國近代史與歐美近代史不同之處,亦即不能如后者那樣,因為信仰上帝而能將程序本身當成是認同的對象。
試想,黨若不再是作為權力的主體,則民主化帶來的人事與政策折沖,就不會以黨為范疇,也不會針對黨,如此黨員便不必在利益分配中進行爭取選票的討好與交易。一旦黨作為領導階層調和利益沖突的超然性與純潔性免受質疑,反而能賦予黨至高的道德權力。這樣的道德地位維系了黨作為群體象征的地位,從而能在民主化帶來的媚俗、私欲的政治交易游戲中,滿足群體的文化心理需要,維持社會穩定。
因此,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與和諧世界,指向的不僅只是政策原則,而更是群的維系。唯有充沛的群體意識,才足以緩和民主化帶來的局部與短期思維,保留從大局、從長遠出發的超然性,進而制衡民主競爭的墮落傾向。由于貧富分化帶來的群己關系的流動與變遷,有賴民主化加以釋放梳理,則黨的建設就需要針對民主化來改造自己,以退為進、以虛為盈,以釋放人事與政策權,掌握道德與調和權。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更大的權力意味著更大的責任。相對而言,在黨的思想史中,民主政治是群體政治,更大的權力意味著代表更多群眾。在多元化的新世紀,權力集中的群己關系落伍了,而新的美歐式的民主話語則威脅著群體的維系。以黨護群的時代不再,新時代要求的是以群護黨,也就是群體成員自動認識到社會分化與矛盾,保護并呼喚黨在制度上轉化成超然的群體象征,領導群眾維系和諧。
(摘自《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