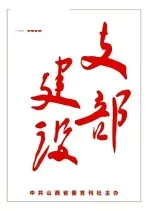政企關系走向何方
王敏
從直接管理、放權讓利、劃槳掌舵到服務型政府,其間經歷了幾十年,伴隨著中國國企改革的每一個腳印,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進程。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政企關系就是政府和國企的關系。
100多年前,德國奔馳之父卡爾·本茨的訓詞“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關系”,在今天仍然是不少企業的座右銘。
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的一席話——“改革越深化,企業家的地位肯定是越來越高,但不能超過當官的地位,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保持安全距離,一定要聽黨的話”——在微博上一夜之間轉載過萬,從另一側面說明公眾對政企關系的關注。
追根溯源,政企關系一直是一曲不對稱的搖擺旋律。
政企關系30年
改革開放的30多年,也是政企關系演變的30多年。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業。政府全面管理企業的人、財、物,通過行政命令和計劃指令對市場和銷售的各個環節實施直接管理。這種體制下,企業完全是政府的附屬,權力直接干預經濟。這樣做的結果,直接導致了計劃的僵化和經濟活力的缺失。
改革開放后,到1993年十四大正式明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市場為資源配置主體、以市場經濟規律為調控機制、政府與企業相對分離的一種經濟運作體制應運而生。這是政企分開最初的呼喚。
在此階段內,國企成為價格雙軌制背景下的改革先鋒。“擴權讓利”讓國企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通過,從法律上明確了國企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
1993年之后的近10年間,國企改革的目標演變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期間,1994年《公司法》通過,從法律上明確了國企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在國有經濟占主導的條件下開展國有經濟的戰略性布局和改組,要求“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而給經營性國企以更大的改革余地。
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意味著國內國外市場接軌的加快,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活動也要遵從國際上普遍的規則和慣例。這就要求中國重新審視自己的政企關系,改變傳統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政府集運動員和裁判員于一身的狀況,構建與WT O要求相適應的運行規則和國際市場經濟社會通行做法相一致的新型政企關系。
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改變了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的局面。2008年,《企業國有資產法》通過,明確了國資委“出資人”的角色。至此,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核心演變為國資委如何定位,表現為如何處理產權所有人、出資人和經營人、監督人的關系。
世界上的政企關系
受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及市場培育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響,根據各國政府處理與企業的關系的方式不同,學者們把世界上的政企關系分為三種:權威關系型、關系依存型和規則依存型。
權威關系型以東南亞一些國家為代表。這種類型的政企關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權,政府各部委的權限未作細分,政府享有很大的權力,而企業對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極小,企業只有直接向最高權力行使影響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如韓國、新加坡等,都是權威關系型的例子。
在這種關系下,政府掌握著國家的資源,政府可以運用自身強有力的主導權,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時比較有利,這在發展中國家實行趕超戰略時,對國家經濟的起飛、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權威關系型的政企關系有明顯的弱點,一是當趕超過程結束而需要進一步發揮企業家精神時,企業的開拓創新積極性早已消失殆盡;二是因為權力高度集中,政治勢力的獨裁和腐敗極易滋生。
關系依存型以日本為代表。其基本特征是各部委之間的管轄范圍有嚴格的區分,而且各部委間存在監督與制衡的關系。企業是獨立的法人,政府通過政策對企業進行誘導和控制,也就是所謂的政策管理。在日本的政企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即企業和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以及以協調局為媒介的職能部門之間的競爭關系。對于企業來說,管轄自己所屬行業的職能部門是接觸政府機構的唯一窗口。政府職能部門一方面,通過規制手段限制新來者進入該行業;另一方面,利用與企業建立的長期關系掌握有關企業的信息,用于政府的決策。這樣,在日本的市場經濟中所表現出的政企關系,就成為一種政府與企業捆綁式的連體關系。
日本之所以形成關系依存型的政企關系,除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以外,關鍵在于它有一套嚴密、有效的組織關系。從政府機構到半官辦的經濟審議會,再到民間的行業團體和企業內部的橫向聯系,形成了一個以民間經濟組織為媒介和紐帶的官民相互聯系、互通信息、協調利益的穩固渠道,既有利于使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實際經濟發展的需要,又有利于經濟政策得到民間企業的響應和執行。顯然,這種“官民協調”的做法,為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創造了條件,這也是戰后日本經濟獲得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關系依存型政企關系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出來。首先,政府和企業之間長期的捆綁式連體關系使政府事后變更規則的可能性增大,結果阻礙了企業事前開展活動的積極性。其次,政府過分地干預經濟,并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必然造成某種官僚制度,使效率降低。再次,各部委間的制衡雖然排除了政治上的獨裁,卻容易產生山頭主義。
規則依存型以美國為代表。這種政企關系的主要特征是各部委的權力較大,但在行使管理權力時,必須以法律為依據。部委間不存在嚴格的管轄范圍的區分,彼此競爭激烈。企業對政府具有比較大的談判力,政府對企業的限制作用很小,不存在行政性的直接干預。美國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在政企關系上,是以市場為主線確定政府干預的界限,政府通常處于市場之外,通過控制市場參數,間接對企業施加影響,政企關系始終保持公平交易的關系。政府的法律、措施完全透明。政府是公共權力的代表,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不與任何企業保持特殊關系,以至于人們稱這種政企關系模式為“政企離散型”的。
與其他政企關系類型相比,美國政府在直接參與市場,擁有經營國有企業的比重上十分有限。即使對國有企業,政府也只在監督和規制方面發揮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作用。如美國對很多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對國私合營的企業實行系統承包經營,由政府作為產品計劃招標人,選擇主承包商,其余運作完全由承包商負責。一般認為,規則依存型的政企關系的弱點是變更規則受到法律的束縛。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認為政企關系存在一種德國式的仲裁關系,即政府獨立于市場之外,為市場內企業間的關系提供裁判等。
從長期和整體看,規則依存型的政府在處理政企關系上比較成功。它強調民間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政府通過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實現資源的配置。它注重對中小企業的扶植,對大型的民營企業聽其自然,而對國有企業的規模進行適當的限制。此種類型的政企關系將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一般職能,與企業經營活動的要求、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及社會公平的要求有機地協調起來,強調市場與政府都可以做到的,由市場來解決,在政府必須干預經濟時也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可見,這是一種更接近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政企關系。
構建中國式新型政企關系
中國的政企關系比較復雜。從直接管理、放權讓利、劃槳掌舵到服務型政府,其間經歷了幾十年,伴隨著中國國企改革的每一個腳印,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進程。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政企關系就是政府和國企的關系。
在國企改革的發端,中國就提出了政企分開。提了幾十年,政企還是藕斷絲連。究竟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一直爭論不休。
在歐債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危機下,“華盛頓共識”(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把鼓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華盛頓共識”指責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崩盤,美國學者福山在“歷史終結論”中提出的所有利益的平衡漸成幻影。面對各國所遭遇的種種困境,構建新的政企關系已成為一個新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世界性發展議題。
長江商學院學者項兵認為,近幾年世界所經歷的種種震蕩,預示著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深刻的結構性變革已經開始: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奉行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當前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矛盾,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著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雙重考驗——世界可能到了一個需要重構政企關系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由此,項兵認為,新一代良性政企關系的基本框架思路應該是,要有效地遏制“政企共謀”,實現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發展。
具體而言,在政府方面,第一,必須建立一套有效制衡政府權力的機制,同時也要確保精英治國。實現這種“忠孝兩全”的機制具有挑戰性,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第二,盡量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政府應更多地關注民生,建立更為完善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公費醫療、免費大學教育、退休保障等社會主義的必備福利項目)。第四,政府還要盡可能為打破階層固化提供條件,使“中國夢”也成為可能。第五,尋找和諧社會與大企業創新之間的平衡。日本基尼系數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社會可謂超級和諧,但這種超級和諧可能扼殺了大企業創新,在日本難以產生谷歌與臉譜這類引領全球的大企業創新。
在企業層面,要更多地關注如何打造偉大的商業機構和培育中產階層。企業家與商人不僅要認真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好,同時要關注為什么做生意。如果企業將做生意的目的局限為追逐財富、光宗耀祖,商業行為就可能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由此可以產生一系列的食品和藥品安全問題。項兵認為,諸多中國企業的這種價值取向問題,已成為中國威脅論的一個主要話題。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前副院長、I M F前執行董事黃范章認為,糾結于“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本身沒有意義,關鍵是分清各自的界限。
黃范章認為,盡管“政府主導”更加突出了政府的主動性、前導性和服務性,但它仍限于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范圍,它不涉入任何經營性領域,這一點非常重要,是任何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它可以彌補“市場失靈”,但絕不會有損于市場機制發揮其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面對“政府主導配置社會資源”的指責,中國必須看到,這是目前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是阻礙市場經濟建設的嚴重障礙,但問題的根源不在于“政府主導”,而在于政府“越位”、“越權”,在于“政企分開”尚未徹底貫徹,在于政府仍掌控與經營龐大的經營性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將經營性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從“政府所有制”剝離出來,徹底貫徹“政企分開”,政府必須忍痛割愛,實行“瘦身”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