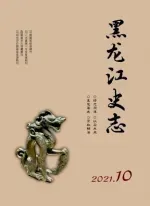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毛澤東對民主執政的探索與實踐
李 文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 思想政治教學部 廣州 510970)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民主執政思想。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是一種理想,實現人民民主是毛澤東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民主又是一種現實,它是一種具體的國家制度,一種工具或者方法。民主應該是什么?現實的民主又是什么?毛澤東在其民主實踐過程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實踐,這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亦有失敗的教訓。
一、人民民主:一個不滅的理想
人民民主是毛澤東民主思想的核心,縱觀毛澤東民主探索的一生,人民民主是其至死不渝的追求。毛澤東曾說:“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1]731毛澤東早年的理想是追求新民和新村,1918年4月,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創辦了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以構建平等友愛的新社會為目標。中年毛澤東則致力于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等原則。從毛澤東早年對新村的追求,到中年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再到晚年“大民主”的實踐無不體現了毛澤東對民主的執著追求。那么,毛澤東心目中民主的應然狀態是什么呢?1936年7月,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說道:“我們要停止內戰,與國民黨和其他黨派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政權,為我們的獨立去進行抗日戰爭”[2]。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及“人民民主”這一概念,把人民作為民主的主體體現了毛澤東對民主的應然理解。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意指人民的統治。相對于少數人或者一人的統治而言,民主顯然是多數人的統治,這是民主的應然狀態。對于“人民”這一概念,毛澤東說:“這里的人民不是指個人、個別人、少數人或單純的多數人,而是指最廣大的民眾或公民群體。”[3]顯然在毛澤東看來,作為民主主體的人民不是幾個人或者一少部分人的政治行為,而是最廣大民眾的集體行動。在人民民主的理念之下,是否意味著任何一個民眾都享有民主的權利?對此毛澤東做出了具體的限定,毛澤東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4]毛澤東在強調民主主體廣泛性的同時,對人民做了限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的范圍是可以“伸縮”的,民眾則被毛澤東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大陣營,顯然敵人是沒有民主權利的。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雖然對民眾做了劃分,但是人民在數量上仍然很巨大。從民主的應然狀態而言,這些人就有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這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顯然很難做到。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如何處理政治精英與人民大眾之間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民主的應然狀態”與“民主的實然狀態”之間的關系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毛澤東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民主集中制:一個現實的考量
人民民主這一理想如何實現,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是毛澤東本人最為關心的問題。毛澤東從現實實際出發,通過民主集中制這一制度來調和“民主的應然”與“民主的實然”之間的矛盾。
民主的應然與民主的實然有著重大的區別。最初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列寧,他說道:“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在憲警到處進行選擇的情形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度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有害的兒戲。所以說它毫無意思,是因為實際上任何一個革命組織從來也沒有實行過什么廣泛民主制,而且無論它自己多么愿意這樣做,也是做不到的。”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如果實現廣泛的民主那就必然意味著千千萬萬民眾的集體行動,試想如果每一個人都各抒己見參與到決策的制定過程之中,這勢必會影響決策制定的效率。不難理解,列寧為什么說廣泛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有害的兒戲。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繼承了民主集中制這一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通過民主和集中的形式來體現人民民主的理念。毛澤東說道:“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形式,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要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毛澤東看來,民主集中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5]在上述論述中毛澤東其實亦談及了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民主和集中本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毛澤東倡導民主集中制,就不得不對這一矛盾概念做出解釋。對于民主和集中的關系問題,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說道:“應當不但看名詞,而且看實際。民主和集中之間,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于中國,二者都是需要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1]383對此,毛澤東還說道:“在人民內部,民主是相對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6]從民主的應然角度,集中制顯然違背了民主的本意,民主是“多數決”而非“一人決”或者“少數決”。但是從民主的實然角度而已,集中與民主這一矛盾則是可以調和的,在一定范圍內德集中是為了更好的實現民主。毛澤東對于民主集中制的關系解讀,其邏輯的出發點就是基于現實的考量。
任何一種政治模式都要處理好政治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關系,民主的本意意味著普通大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民主的這種應然狀態又缺乏現實性,這個時候就要發揮政治精英和政治中堅的力量,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顯然民主集中制就是這樣一座“橋梁”。
三、“大民主”的實踐——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失衡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情結激劇暴漲,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毛澤東逐漸的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毛澤東時而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理想,并按照民主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實踐,跌入了至善論的陷阱;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現實工具,強調民主的工具性,陷入了現實主義的窠臼。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晚年毛澤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民主的應然狀態。在晚年毛澤東的思維中,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人民群眾自己管理國家事務。在這一思維影響下,毛澤東晚年推行了大民主的瘋狂實踐。在1956年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談及了大民主問題,他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在這里毛澤東提及的“大民主”是指西方的民主模式,對于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澤東并不認同,并批評那些主張者說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于“大民主”毛澤東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說:“從我們的歷史上看,陳勝、吳廣揭竿起兵以抗秦,王莽廢子嬰而篡漢,東漢靈帝時黃巾起義,三國之際曹操、劉備、孫權分爭大下,清朝的洪秀全、楊秀清等搞金田起義……等等,是大民主的作法,我們搞革命推翻蔣介石的作法,也是大民主的作法,這次舉行反對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7]在毛澤東列舉的各個大民主作法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共性,那就是大民主是一種受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由千千萬萬群眾直接參與的群眾運動,這種群眾運動的形式可以是激烈的革命也可以是溫和的示威游行。關于大民主的形式,毛澤東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會議上說道:“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有了這種形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領導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形式傳下去,因為它充分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8]不論具體的形式如何,大民主都需要大量民眾的直接參與,這是與民主的應然相吻合的。晚年毛澤東寄望于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來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思想,在其潛意識中民主成了一種現實的工具。
毛澤東所倡導的“大民主”在“文革”期間達到極致,在“大民主”的形式下,廣大民眾積極投身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之中,彰顯了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但于此同時,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日趨狂熱。正如施拉姆所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開宣布贊成巴黎公社式的群眾民主開始,以贊美中央集權的專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終。”[9]晚年毛澤東“大民主”實踐的悲劇在于,毛澤東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時而片面強調民主的理想狀態,時而又強調民主的現實。
四、結論
民主作為一種理想其作用是向現實挑戰,若將民主絕對化就會脫離現實,不是實現不了的天堂,就是實現了的地獄。但是如果僅僅屈從于現實,民主就會成為一種沒有價值維系的工具,從而失去理想的價值引導功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很好的把握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晚年“大民主”的實踐則表明毛澤東把民主理想絕對化脫離了現實實際。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言:“討論民主的時候,最讓我們迷惑的,或許莫過于一個簡單的事實:‘民主’既是指一種理想,又是指一種現實。我們常常劃不清兩者的界限。如果不把理想的民主與現實的民主的含義弄清楚,人們就會各執一詞,不能溝通。并且,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遺憾的是,這甚至在那些對民主的思想和實踐如數家珍的學者當中,也時有發生。”[10]顯然,晚年毛澤東亦沒有劃清理想民主與現實民主之間的界限,這或許導致其“大民主”實踐的悲劇的根源所在。
[1]毛澤東選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李蓉.人民民主——毛澤東的理想與實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98.
[3]李鐵映.論民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4.
[4]毛澤東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05.
[5]毛澤東選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7.
[6]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2.
[7]毛澤東選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