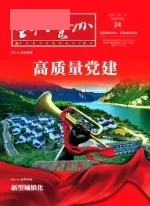認識海洋與認識世界
(本文系《百年風云釣魚島》序,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張天明)
與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陸疆比較起來,6.3平方公里無人居住的釣魚島,真可謂彈丸之地。
這樣一個小小的海島,凝結著如此充滿傷痛、如此讓一個民族耿耿于懷、難以忘卻的歷史,在人類社會中,恐怕并不多見。
這樣一個小小的海島,使一個民族旅居各地的赤子結成共同心愿、發出共同呼喚,訂立共同目標,在人類社會中,恐怕也不多見。
這樣一個小小的海島,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歷史糾結,海洋糾結。
自古以來,我們對海洋的認識主要集中于“興漁鹽之利,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為走向世界通道、作為經濟貿易重要渠道、作為國家發展的全新空間,這些觀念在中國十分缺乏。閉關自守的政治目標,本身就在抑制海權意識的生長和海洋進取信心的獲取,最終使我們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不得不留下這份“望洋興嘆”的糾結與沉重。
恰恰在中華民族嚴重喪失海權的時刻,十九世紀末,一個叫阿爾弗雷德·馬漢的美國海軍上校提出“海權論”,最終使美國這個1776年剛剛獲得獨立、以“門羅主義”自我封閉的地區性國家走向大洋、走向世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漢所提的“Sea Power”(海權)與我們理解的“Sea Right”(海權)存在重大差異:前者使用的“Power”,是指由力量產生的權力,后者使用的“Right”,則是指由公正帶來的權利。
東西方的概念這樣無情地撕裂了,奇怪現象也隨之發生:據說崇尚“專制”的東方,遇事反而總想跟人講清講透道理,通過以理服人獲得“Right”;而據說崇尚“自由、平等、公正”的西方以及全力“脫亞入歐”的日本,動輒使用武力,習慣用“Power”奪取權益。結果是相信“有理走遍天下”的,憑借道理實在無法走出多遠;崇尚力量征服的,反而橫沖直撞暢行天下。如馬漢所說:海權不僅包括通過海上軍事力量對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也包括對和平的商業和海上航運業的控制。
這就是今天的現實世界。
我們相信,我們終將迎來一個公正、平等、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世界。但在理想世界到來之前,我們仍然必須生活在這個不甚理想、由力量決定規則而不是由公正決定規則的現實世界中。一部近現代史一再證明,國家遭遇割地賠款甚至亡國亡種,并非僅僅因為戰爭的失敗,本質上在戰爭尚未發生之時,在確定維護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以及決定主要依賴何種手段的抉擇中,結局就已經大定。
在國際關系中,權利只有在爭取和捍衛時才會得到彰顯。只有公理沒有力量,并不能戰勝強權。
釣魚島成為中國人完成以上認識的一個窗口。通過它,我們再次認識自身,再次認識世界。它已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審視自己利益、權衡自己利益、決定捍衛還是放棄這一利益的基本考驗。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就是隨著現實中遇到的一個個問題一點點擴展開來,從自然海洋走向權益海洋、最終才能是和諧海洋。沒有這些問題發生,不遭遇這些挑戰,我們對世界以及對自身的認識,可能都不會像今天這樣深刻。
寫到這里,腦海中不由得浮現書中出現的三個人:張惠榮,孫書賢,郁志榮。三人都是令我佩服的人,從他們身上,讓人分明看到:在實現海權的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同步增加之時,中華民族中有一批人已經出發,正在大步走向可以托付的成熟。
我相信,在這些新一代引路人的身后,會有更多、更多的后來者。
這里還必須提到第四個人:本書作者李旻。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藝術創作的文弱女士,通過長期的、執著的、鍥而不舍的關注和追尋,把釣魚島問題的來龍去脈梳理得如此清晰,把海洋與中國的關系分析得如此透徹,除去個人才華,何嘗不是一種天地之間的正義、勇氣和責任。
中國所說的國家只是一個詞,包含“國”和“家”兩層意思。“沒有國、哪有家”的概念,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所說的國家,則有三個詞相對照:Country特指“土地”、Nation特指“人民”、State特指“政權”,包含這樣三層含義。
如果按照西方觀念來闡釋,那么此刻說到Country,我腦中會浮現出釣魚島;說到Nation,我腦中會浮現張惠榮,孫書賢,郁志榮,李旻;說到State,我會記起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那句鏗鏘有力的話語: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
這就是我們今天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