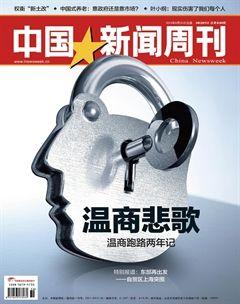溫州的折騰:執政思路換不停
龐清輝
“領導思路頻繁換,醫生可能是個好醫生,但是治不好病。”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近10年來,溫州市委書記更換頻繁,平均任期不足3年。一個領導一個口號,上一任與下一任政府之間的政策缺少延續性,是中國政壇的通病。溫州也不例外。
2013年6月底,經浙江省委研究決定,在浙江金華任市委書記17個月零18天的陳一新,出任溫州市委委員、常委、書記,免去陳德榮溫州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調任浙江生態省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省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溫州地、市合并,建立溫州市委、溫州市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原溫州市及各縣的工作。30多年內,先后有袁芳烈、董朝才、劉錫榮、孔祥有、張友余、蔣巨峰、李強、王建滿、邵占維、陳德榮、陳一新11人相繼成為溫州市委書記。
每個書記都有自己的施政綱領和口號,有的扎實,有的浮躁;有的關注走出去,有的提倡引進來;有的重視輕工業,有的重視旅游業;有的提倡政府無為,有的認為政府要強勢主導。在所有口號的變化中,也體現著“新官不理舊債”的自我政績標榜。
“第一年了解情況,第二年剛提出思路,人就走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結果就是官員浮躁,急功近利,分秒必爭搞形象,追求短期政績。朝令夕改,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在這10年中,溫州經濟增長率也長期處于浙江全省末尾。
施政綱領頻換
現任浙江省省長李強是溫州歷史上第一位溫州本地人當市委書記。2002年4月,李強出任溫州市委書記,在溫州任職2年7個月。
李強任職溫州期間,“走出去”是一個重要特征。他提出很多與經濟相關的經典詞匯,比如“地瓜經濟”“草根經濟”,核心都是“根在溫州”。“有些人把到國外投資叫跨國戰略,把在國內投資叫做‘外逃,我認為這是認識上的誤區。我們要更多更好地‘走出去。”李強經常在媒體上糾正這個“誤區”。他在任內召開了“首屆世界溫州人大會”,成立了海外溫州人聯誼總會。

李的施政藍圖——一港三城發展戰略,“百項千億工程”,政府效能革命,以及他提出的“質量溫州”“品牌溫州”“信用溫州”建設,令溫州人記憶猶新,但藍圖才剛鋪開,2004年11月,他便調任浙江省委秘書長。
李強的繼任者王建滿2004年底主政溫州后,提出招商引資是當年溫州全市工作的“一號工程”,并通過“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引資口號,以遠遠高于民企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
從2005年初的取經杭嘉滬,到成立“開放辦”;從“千人動員大會”落實招商引資“一號工程”,到“12345工程”和“千家民企大招商工程”,再到2005年底的對話世界500強,在“無外不活、無外不富、無外不高、無外不快”的口號下,溫州的招商引資工作到了一種巔峰狀態,走出去開始變成引進來。
溫州市發改委的張林(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此之前,溫州不論從政府還是企業,對于招商引資都沒有興趣,甚至沒有類似“招商局”的部門。主流的觀點一直是:不缺少資金的溫州沒有必要引進外資,而資本本身帶有擴張性,溫州資金的外流是正常現象。
王建滿任溫州市委書記三年兩個月,溫州人稱他為阿滿大叔,他也提出了三個溫州的口號:活力溫州、實力溫州、和諧溫州。2008年1月,王建滿當選浙江省副省長。這些設想囿于他的任期,最終只是成為了口號。
接替王建滿的是邵占維,在溫州任市委書記兩年六個月。“他提出過發展大旅游,沒提出什么綱領,印象不深。”張林說。這也是大多數溫州人對邵占維的總結。人們能想起的是邵占維在紅日亭喝粥并捐款的一幕。紅日亭,是溫州民間的免費施粥點,專為流浪者和外來務工人員送粥解饑寒。
“我和他在他的辦公室里還討論過他要提出的溫州‘五大戰略,推出來還不到3個月他就走了。”周德文說。2010年7月,邵占維調任杭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2013年3月6日,全國兩會期間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病逝。
2010年7月,正值金融危機影響深入、溫州人信心低潮時,陳德榮出任浙江省副省長兼溫州市委書記。這是自1982年浙江省政法委書記袁芳烈兼任溫州市委書記以來,浙江省委為溫州主官又一次高規格調配。陳德榮主政溫州之際,經歷過動車事故、民間借貸危機爆發、創設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等震動境內外的事件。
在大多數人眼里,陳德榮主導了一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強勢政府一面。陳德榮在溫州掀起了大投入、大建設的熱潮,兩年來溫州投資率翻了一番。陳德榮謀劃通過大項目、推動大投入,強化政府主導性投入,以政府投資帶動全社會投資。這也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主流——政府主導型。
在陳德榮的主導下,2010年11月,溫州啟動國企改革,這個民企大市聳立起13家國有獨資集團,以“航母”之勢,成為政府投融資平臺。在民營經濟最為繁盛的地方,“國企的價值”重新被發現。有當地企業主稱,陳德榮在多個公開場合的演說中,對大企業表達的喜愛讓諸多溫州本土的小微企業主微感“酸意”。
溫州市各級政府的考核標準也因應而變。王建滿時期,招商引資納入了對各部門、各地區業績的考核體系。如今,投資率成為縣區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標。“領導不停換思路,很浪費公共資源,有的規劃重新做十幾個的時候都有,光認證就需要很多錢。老折騰,大的難題就很難攻。”朱康對說。
2013年6月,陳德榮就任溫州市委書記3年還差20多天,即奔赴省城杭州新的領導崗位。雖然仍然保留省委常委的職務,但兼任的卻是浙江生態省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省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等閑職。惋惜之聲有之,非議之聲亦有之。采訪中,更多的市民則擔心,陳德榮主政下的一些工程,在離任之后,會否成為“半拉子”遭到擱置。
當時,正在國外考察的浙江金華市委書記陳一新,提前三天才接到上任通知,為此,他提前5天回國到溫州上任。陳一新在金華任職17個月零18天,也成為了自1985年金華撤地建市以來,任期最短的一位市委書記。
陳一新甫上任,考察、調研第一個要點便是民營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發展,召開的第一個大會就是“浙江銀行業服務溫州實體經濟大會”。他指出,當前經濟問題是溫州發展中尤為突出的問題,憑借“溫州人”這個最核心優勢,“溫商回歸”將成為今后溫州趕超發展的最大要素。他也提出了,要把招商引資作為“一號工程”,按照“三招一優”要求,引進一批好項目大項目,力爭完成年度400億元的引資任務。
施政綱領源頭
過去十年,每任溫州領導的主要施政口號都有其自身的經歷和經驗烙印。王建滿在到溫州前,任蕭山區委書記期間,就把招商引資作為發展的最大抓手,實施的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戰略,由政府出面協助當地企業尋找跨國公司洽談合作是王建滿的“拿手好戲”。
王建滿深諳招商引資之道。2004年11月,王建滿甫一到任,就組織溫州各方力量,專題研究招商引資戰略,將招商引資作為2005年的“一號工程”。
邵占維在到溫州任職前是寧波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常年從事管理港口事務,升任溫州市委書記后,第一項有聲有色的動員大會是塘河治理的大會。當地人開玩笑說:搞大港口建設的去整治這些小河,“大材小用”。
陳德榮在到溫州前,任嘉興市委書記,共在嘉興工作12年,國企技術干部出身的他在工業經濟、環境保護及較為棘手的城鄉統籌等公共服務等領域頗有建樹。2008年,嘉興被列入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包括戶籍制度、規劃管理制度、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市鎮建設在內的“十改聯動”。
2010年7月,一到溫州的陳德榮就參觀了溫州城市規劃展示廳,隨后在溫州掀起了一場統籌城鄉發展的改革,大力推進城市改造,其力度前所未有。
戴著眼鏡、氣質儒雅、書卷氣很濃的陳一新在城市規劃上也頗有心得。他在金華上任17個月提出來的轟轟烈烈的“金義都市新區”思路,將新區的未來定位定為“田園智城·都市新區”,號稱浙江第四大都市區。
陳一新上任溫州后,也把城市規劃工作作為市直部門工作調研的首項內容。7月,陳一新赴鹿城區調研,強調“三改一拆”方向不變,著力提升溫州的城市功能,推動都市經濟和城市能級的提升。
每個官員新換一個地方任職都愿意沿襲自己曾經的施政方向,“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最容易出政績。”周德文說。問題是,不審時度勢則寬嚴皆誤。照搬往日經驗,難脫刻舟求劍之嫌。
“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任后一直在強調正確的政績觀,不要輕易另起爐灶,否認前任。”中組部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早在廈門工作之時就提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一張藍圖繪到底”,“一茬接著一茬干”。當前,中央亦要求各級政府樹立正確政績觀。
按照中共組織部門對干部的培養和考評,浙江省內公認杭州、寧波和溫州比較出干部。杭州的省會地位、寧波大港的特殊區位優勢不用說,溫州由于其自身的特殊的經濟形態,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經歷了這里鍛煉的干部,可以加分不少,近10年來李強、王建滿、邵占維、陳德榮的升遷即是明證。
上述中組部人士稱,每一任領導的調任都有深意和考量,比如溫州,以前發展太快了,應該要穩一點,從領導方面來講,就是要加強領導力度和地方管控。“雖然每個人都想體現自己的施政印記,但目標一定要謀地方的發展。”
目標GDP
溫州每任主官的施政方針不同,但殊途同歸,目標都是提升GDP。經歷了長期高速發展的溫州模式,面臨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困擾,近10年來疲態盡顯,其GDP增速位列全省榜尾。
在GDP導向的政績觀指引下,每任主官都要出手。李強的方式是,不放棄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的輕工業,把溫州建成為輕工產品的生產基地、銷售基地和創新基地,建設成國際性輕工城。
王建滿也解釋說,他的招商引資政策,錢、量不是主攻目標,而是通過引進來解決溫州粗放的增長方式。
而陳德榮認為溫州速度慢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投資率不足,政府在公共品領域的投入不足。所以他要政府用高達50%的投資率,親自出手“砸”出GDP。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錢從何來?陳德榮的答案是土地財政。陳德榮說,當前溫州10大國資公司6000畝存量土地,按1000萬元/畝計,就是600億元,通過金融杠桿的作用可以放大到1800億元。
陳一新剛到溫州半個月,代表新一屆溫州市委首次公開“墊底”數據:在16個主要經濟指標中,2012年,溫州市大多數指標處于浙江省“倒數”行列,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財政總收入等9項指標倒數第一,另有4項倒數第二。他提出“趕超發展、再創輝煌”的口號,并把“溫商回歸”作為溫州趕超發展的最大要素。
但是,對溫商來講,有人擔心溫州會否重復中國經濟近年來的怪圈:溫州有著外貿優勢,壟斷土地、資金等要素的政府親自進場,操盤經濟發展,形成GDP越來越仰仗于投資拉動的路徑依賴;有人開始打退堂鼓,如果外進民退、國進民退,“我們老百姓經濟”怎么辦?有很多服裝企業老板至今一直懷念李強“打造國際性輕工城”的溫州設想;有永嘉的商人也認為溫州應該大力發展旅游;有的商人則干脆不去管誰來做領導,“誰給我訂單我關注誰。”
采訪中,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問及對溫州貢獻最大的市委書記是哪一個,無一例外都認為是溫州地市合并后的第一任市委書記袁芳烈。袁芳烈當年對溫州進行了幾年大量調研,以擔當政治風險的勇氣,默許了溫州民間自發的經濟模式創新,成為奠定“溫州模式”的關鍵人物。“有沒有口號,說明不了任何問題,關鍵是看怎么干才是最適合溫州發展實際,這是袁芳烈至今讓溫州人惦記的原因。”朱康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