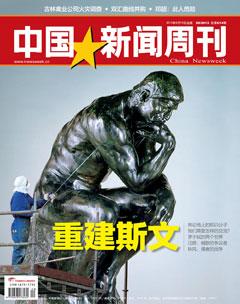深圳:求解立法權之路
徐天
1985年8月,李灝從國務院副秘書長任上調至深圳,成為深圳市第三任市長(1986年5月起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
在與港商、外商的交流過程中,他很快發現了一個問題。“我們搞對外合資、優惠政策,我說我有紅頭文件,但對方說,我們一定要看法律條款。如果打官司,政府文件不可能被法院認可,只有法律條文才行。”李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當時,深圳沒有立法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82年修訂),除省一級行政單位外,只有省會城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當時共13個),擁有立法權。
就這樣,深圳開始了尋求立法權的多年努力,終于在1992年,獲得地方立法權。
2013年5月11日,在深圳市委大樓后樓,前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副書記秦文俊、法制局局長張靈漢和司法局副局長徐建,這4位當年的操盤手重聚在一起,共同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深圳求解立法權的這段歷史。
“后來要到的立法權位階太低,讓深圳掣肘太多。依我說,這樣的立法權不如不要。”徐建開玩笑地說。
“話不能這么說,當年能把立法權拿到,已經很不錯了。”沉默許久的秦文俊說。
“那時給你立法權是什么意思?就是支持你,放權給你去改革。”87歲的李灝騰地站了起來,抬起手,忽然向前一揮:“特區的作用,不是說GDP一定要排在全國前幾名,我們是一塊試驗地,就是用來突破、打頭陣的。商品經濟本來就是法制經濟。沒有立法權,法制不健全,怎么發揮試驗地的作用?”
“要立法權是違憲”
1986年,在廣東省法制工作會議上,為了制定全省的立法計劃,省政府辦公廳法制處負責人詢問深圳,還有哪些立法需求。
1981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使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起“立法試驗田”作用。深圳也在這一年,相應地成立了特區立法工作組,張靈漢任組長。立法工作組后更名為條法處,最后升格為法制局,張靈漢任局長。
為了做好立法規劃,張靈漢帶隊去香港、歐洲和美國考察。香港更是多次往返,收集了幾乎全部的法律。
很快,深圳市委將未來5年的立法需求敲定,計劃在5年內制定135項經濟和行政法規,做到各項工作基本有法可依。
按照這個方案,深圳未來平均每年需通過27項立法。而此前,因立法周期較長(深圳擬定立法草案之后,需報給廣東省政府,然后以省政府的名義向省人大提交),深圳草擬的法案通過省里審批的平均每年只有3項。以這樣的速度,怎么來得及?而且,因對市場改革的認識不同,部分法規草案并沒有獲得省里通過。
深圳市委下決心,要爭取自己的立法權。
為了爭取各方面的支持,1987年夏天,深圳市主辦了“經濟特區立法研討會”。出席研討會的,有來自國務院法制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領導,廣東省的相關負責人,珠海、汕頭、廈門三個特區的負責人,以及廣東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
在會上,張靈漢作了主題發言,總結了深圳的6年立法經驗,提出了今后的5年立法計劃。這位出身廣東梅州的客家人,用帶著濃郁口音的普通話,不疾不徐地說:“只有深圳最了解深圳,最了解如何貫徹特區的特殊政策。因此,為了能完成這個龐大的立法計劃,深圳希望能有自己的立法權。”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
專家學者們大多從法學專業角度出發,對此表示了支持;但省內有的學者卻激烈反對,直言不諱地批評深圳市,“要立法權是違憲”。
反對最激烈的是原司法部一位司長、當時在廣州任職的老同志。“我不能茍同,廣東被授權立法,你也要立法權,這樣廣東不是多頭立法了嗎?一個省弄得四分五裂的,而且違反國家法律的統一原則,我不贊成。”張靈漢一字一句地對著《中國新聞周刊》重復這位老干部的話。
原定三天的會議,因此延長到了五天。
散會之后,李灝告訴張靈漢:“省里不同意,咱們也要給中央寫報告。”
1987年年底,由張靈漢起草的報告,經李灝簽發,上報中央,抄送廣東省。
“那年的報告,我們字斟句酌,連標題都是。沒記錯的話,應該叫《請求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制訂經濟特區法規和政府規章的權力》。”張靈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設計立法委員會
1988年6月,鄧小平發表《要吸收國際的經驗》的談話,指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
根據這一指示,國家體改委派人到深圳和香港考察,完成了借鑒、移植香港法規的專題研究報告,經中央領導人批示后,報告的復印件批轉給了深圳。
既然要“借鑒、移植香港的法律制度”,那擁有自己的立法權,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質量,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李灝立刻召開市委班子開會,討論如何加快爭取立法權的問題。
深圳自從1980年設置特區以來,一直沒有設立人大和政協。這一點讓徐建深感困惑:這不是違憲的嗎?難道是深圳市領導忘記了嗎?作為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和市政府的法律顧問,有一次,他當面向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梁湘提出了這個問題。
梁湘問他:“小徐,你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嗎?”徐建說,大學里學過。梁湘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是經濟特區,也不一定要設人大、政協。”
張靈漢也記得,曾數次參加梁湘主持的市委會議,涉及人大和政協的問題時,大家幾乎一邊倒地認為,不用成立這兩個機構。“那會兒深圳特區剛建立,一切要精簡,辦事才有效率,所以上頭也覺得,不成立人大和政協,對提高效率有好處。”張靈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沒有人大,如何來行使立法權呢?深圳市委探討成立“立法委員會”,代替人大,行使立法職能。
1988年7月,秦文俊將徐建叫到了辦公室,讓他做一個關于立法委員會的方案。秦文俊要求他,不要自我設限,要突破框框,大膽設計。“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形式好,就借鑒過來。”
接受任務后,徐建很興奮。這位當年深圳年紀最小的局級干部,思想活躍,覺得能親身參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非常光榮”。他找來一些資深學者幫忙找資料,其中包括他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78級的同班同學、當時的人民大學法律系憲法教研室副主任、后來的澳門政府法律顧問趙向陽;時任深圳市司法局研究室負責人、現任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郝麗雅等。沒有經費,都是義務幫忙。
在這些學者的幫助下,他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研究了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參考了美國的三權分立、英國的上下議院、臺灣的五權憲法、香港的總督制度等,比較研究之后寫出了5000多字的《深圳市立法委員會條例》草案。
徐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這個立法委員會由51人組成,既有官方委員,又有民間委員。民間委員自基層中來,或在各民主黨派內部競選產生。所有委員都實行職業化、授薪制。每年至少開4次會,采取大會辯論形式。”
徐建還效仿美國總統的立法否決權,設計了一個機制:深圳市市長可以對通過的法案有不予簽發權,但重議如果通過,市長則應該辭職。
《條例》草案規定,深圳市的立法權擁有僅次于憲法的位階,即可以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和國務院的法規相沖突,甚至可以在不違反憲法原則的前提下,與憲法的個別條文相沖突。
草案完成后,徐建向秦文俊做了匯報。秦文俊看后,交代他注意保密,待市委研究后報給中央。
掛牌和摘牌
方案設計的同時,籌備中的立法委員會辦公室已掛牌成立,取代了原來的深圳市法制局,張靈漢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他親自去訂做了“深圳市立法委員會辦公室”的牌子,將“深圳市法制局”的牌子換了下來。
體改委完成借鑒、移植香港法規的專題研究報告后,中央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小組,研究落實。1988年8月,該小組通知深圳市政府,派人去北京參加研討會。此時,李灝恰好要出訪意大利、英國、法國,便由秦文俊代替前往,但會議后來因故未開。
不久,深圳市委收到了中央的指示:支持授予深圳立法權,但不同意設立立法委員會,要深圳成立人大。
1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聯合發出了《關于開展借鑒移植香港和國外法規工作的通知》,成立了領導小組,分成行政管理體制、土地房產等11大類,分別成立了相應的研究起草組,均由市分管領導擔任組長。
幾乎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件意外。
12月7日,香港《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將徐建所寫的《深圳市立法委員會條例》草案的內容做了大起底。
消息傳來,領導大為惱怒。秦文俊要徐建配合有關部門,查出到底是哪個環節泄密。最終,目標鎖定在深圳市一名記者身上,此人曾在徐建辦公室看過這個草案。但因對方不肯承認,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很多年后,徐建在香港碰到了這個早已出國的記者。對方承認,當年的確是他干的。他趁徐建有事離開辦公室的10分鐘,將文件傳真到了香港。
雖然已經時過境遷25年,徐建依然對此事耿耿于懷。不過,他也很清楚,即便沒有這個意外,深圳的立法進程也是不會改變的。
“深圳市立法委員會辦公室”的牌子被摘了下來。“立法權要下來才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對深圳來說有更大的意義。立法委員會的想法只能作為特區體制改革的一種探索。”張靈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院外游說”
1988年12月,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法制局都派人來深圳,商議如何起草議案,以便交給第二年的全國兩會審議。
體改委帶了事先擬好的草案來。張靈漢記得,深圳方面只修改了一處,就是立法權不僅限于經濟立法,還包括行政立法。
最終,深圳市委與國家體改委共同制定了《在原國務院授權廣東、福建兩省有立法權的基礎上,授權深圳立法權的議案》。
1989年3月下旬,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李灝出席了這次會議。
國務院向這次大會提交了提請審議授權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深圳經濟特區法規和深圳經濟特區規章的議案。沒想到,反對的意見蜂擁而至,甚至包括廣東代表團的部分成員。
反對意見稱,深圳還沒有成立人大,怎么能授權?而且深圳已經獲得了那么多的優惠政策,現在再授予特區立法權,將進一步擴大政策差距。
最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建議,鑒于深圳市人大還在醞釀成立之中,議案不提交本次大會討論表決,變通為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深圳市依法產生人大及其常委會之后,再對國務院的議案進行審議,做出相應的決定。
此議以1609票贊成、274票反對、805票棄權,在大會上獲得了通過。
這意味著,如果這一屆人大的多數常委能同意授權,深圳便能得到立法權。
深圳市很受鼓舞,兩會結束后,立刻開始籌備成立人大。法制局開始擬定設立人大的方案,包括立法職能、區人大的設立、人大代表的選舉等。
但受八九風波影響,這項工作一度停滯了。直到1990年12月,深圳市人大才正式成立。
成立大會當晚,張靈漢和當時分管法制的市人大副主任聞貴清即奉命乘火車連夜進京,去向全國人大匯報。
他們到北京后,找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曹志。曹志卻建議他們,放慢速度。因為,很多人是不贊成給深圳立法權的,萬一不能一次性通過的話,后面會很麻煩。曹志還給他們支招,讓他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們分批請到深圳去考察,使常委們理解深圳的這種需求。
張靈漢立刻想到了自己讀中國政法大學時的老師、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江平,以及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蔣一葦。張靈漢和聞貴清拜訪了這兩位委員,代表深圳市聘請他們擔任法律顧問,并請他們幫忙開列應該邀請的人員名單。
隨后一年,深圳市委分四批請了100多人來深圳視察,張靈漢將之比擬為西方的“院外游說活動”。
一市兩法
1991年9月,眼看著游說工作差不多結束了,李灝覺得應該加快步伐了。因為,如果議案不能在第二年的兩會上獲得通過,就面臨著人大換屆,一切工作要重頭做起。
深圳市再次以書面形式,向全國人大提交了請求授予立法權的議案。
1992年初,兩會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王漢斌帶隊來深圳,做最后一次調研。
當時全國人大還請了廣東省人大的負責人一起來深圳。張靈漢匯報到一半的時候,省人大的負責人便打斷了他的話:“深圳要立法權,要法是假,要權是真。”王漢斌立刻揚起手,制止了他:“你不要急,聽人家把話說完。”調研會的氣氛變得很緊張。
不過,事過多年,再和省里的老同志聊起此事,張靈漢才理解了當年省里的顧慮:擔心已是經濟特區的深圳,如果有了立法權,會完全甩開廣東,甚至成為直轄市。
1992年7月1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召開,委員長萬里主持會議。在對授予深圳立法權的議案進行表決時,90%以上的委員都投了通過票,決定授權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制定法規,在深圳經濟特區實施,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授權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規章并在深圳經濟特區組織實施。

議案通過后,萬里發表了講話:
希望深圳珍惜和運用好授予的立法權,在發展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方面走在前面,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成為高度民主、高度法制的市。深圳要研究憲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已經制定的法律,注意在制定法規、規章時不能同憲法相沖突,注意上下左右的關系,注意內外的關系,要吸收香港和其他國家立法方面的成功經驗。總之,我認為授予深圳立法權是正確的,對于推動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會產生重大作用。
歷經5年的曲折,深圳終于拿到了立法權。不過此時,立法權僅限于經濟特區范圍內。
1994年,廈門經濟特區獲得立法授權。1996年,汕頭和珠海經濟特區獲得立法授權。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實施后,深圳市獲得“較大的市”立法權(須經省人大常委會批準,不能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之前通過的特區立法權(只需報省人大常委會備案)予以保留。兩種立法權位階不同,一度造成深圳特區內外立法的不一致,形成一市兩法。
到2007年深圳取得特區立法權15周年時,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了300余件法規和法規性文件,市政府制定規章190余項,成為中國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
2010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深圳經濟特區范圍擴大到全市。相應地,較高位階的立法權也擴大到整個深圳。一市兩法正式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