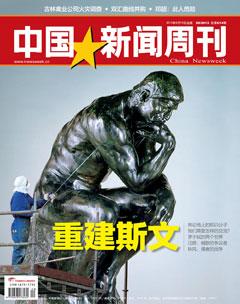不說真話,發誓無用
在需要發誓的地方,真話機制和信任機制其實都已經壞掉,但人們依然假裝發誓有可以代替說真話的功能。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誠實”
生活中常見有人因某事而發誓,言之鑿鑿,那種表情也是極為虔誠,使人不忍心也不好意思去懷疑,倘若有較真者非得上前質疑,那么得到的回答有時會是這樣子的:我的發誓在神圣性上,絲毫不遜于基督徒“向上帝發誓”。
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因為基督徒以上帝之名發誓是一種罪過,不是好基督徒該做的事,好的基督徒是不會以上帝之名來發誓的。基督教的第三誡就是,“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不可以上帝之名輕發誓愿,不要在不必要或者不合適的情況下提念上帝的尊命,這是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的,也應該遵守的。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上帝,他們就該照上帝的話去做。那些偏偏不照這話去做的,裝出很信神的樣子,以神之名發誓來顯示自己信仰的,表現出來的不是比其他基督徒更大的虔誠,而是背棄和偽善。
因此,發誓保證在基督教里是個富有爭議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基督徒是不該發誓的。有的人認為,只有虛假的發誓才是該禁止的。有的人認為,只有以神之名的發誓才是褻瀆,其他的發誓則沒有害處。也有人以“代替物”(surrogate objects)發誓,稀奇古怪,如“以耶路撒冷之名發誓”,“以右手發誓”,“以自己的腦袋發誓”。 反對以任何“代替物”發誓的神學家們認為,不管是天、地,哪怕是人的一根頭發,一切之物皆可歸結到神,神創造了一切,以任何東西發誓都是褻瀆。
不僅如此,基督教還反對一般的發誓保證,因為說真話的人是不需要任何發誓保證的,他的正直,他的話便是“真”的擔保。如果一個人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說的是真話,那又怎么能期待神來替他做擔保呢?神能使假話變成真話嗎?如若奸佞之人說了謊言,又令人信了,難道還要神為他的惡行擔負罪責?《圣經》“雅各布書”說:“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馬太福音”也說,“根本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寶座”,不能指天起誓,那是因為,“耶和華在他的圣殿里,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人指著天起誓,就是指著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指天起誓也就是指神起誓。“馬太福音”對為何不要起誓的解釋與“雅各布書”是一樣的,說真話就可以了,如果別人不相信你,那么,一定是你的信用有問題,或者是別的地方出了問題,把神牽扯進去是一種褻瀆,“你們的話語應該如此: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就是出于那惡者。”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教派,如清教的貴格會(Quaker,又稱公誼會或者教友派),門諾派(Mennonites,16世紀初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派別之一,由德國神父門諾·西蒙斯在荷蘭和德國創立)都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發誓。俄國偉大的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教徒,他認為,基督教反對一切形式的發誓,“馬太福音”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認為,所有法庭的起誓儀式都應該廢除。
有研究者發現,從古到今,發誓最多的地方是市場,市場是人們做生意的地方,人們在那里討價還價,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各自懷著鬼胎,卻又要對方相信自己非常真誠,說的是真話。法庭用起誓來限制偽誓,也是為了盡量讓證人說真話,但起了誓又說謊的人還是數不勝數。所以,對于防止說謊,發誓并沒有什么實際作用,更不能對人有積極的道德教育。
需要發誓是因為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信任,只能用發誓來代替人自己的正直和可信。在不能說真話,說真話會帶來麻煩甚至災禍的地方,發誓又能有什么用呢?在需要發誓的地方,真話機制和信任機制其實都已經壞掉,但人們依然假裝發誓有可以代替說真話的功能。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誠實”。
無論是要證明“真”還是要表白“誠”,都不應借助發誓。發誓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避免發誓,而在于要說真話,說真話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有說真話的自由,說真話有人相信,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能判斷哪些話是真、哪些話是假的環境和機制。
發誓者不僅褻瀆了神的名字,而且往往為了自我利益,偽善地把說“真話”設計成一個表演虔誠的機會,神不需要這種偽善的忠誠表白,一個正常的社會也不需要這種偽善的忠誠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