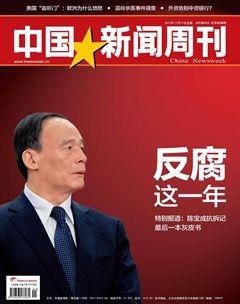“偉人”身后的群眾
馮克利
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折之際,兩種最重要的心理學基礎理論同時誕生。第一種即一般人熟知的弗洛伊德個體心理學,第二種是由兩位法國人勒龐和塔德開創的“群體心理學”。這兩種心理學,其一著眼于個體心理因素與“異常行為”的關聯,其二則專注于“正常”個體聚集成群后發生的可怕的心理變態。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揭示了人類心理中存在著某些不受理性原則支配的強大因素。這兩種心理學一度風行于世,形成了一股解構18世紀以來歐洲理性主義的強大洪流。
自弗洛伊德的學說問世以來,用他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如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著作,一直不絕如縷。而群體心理學又告訴我們,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還得問責于信眾。要想真正弄明白有關的大事件,只搞心理學的個人問責制是不夠的。英雄不但具備獨一無二的稟賦,也是由嘯聚于他身邊的人群所造就。這么說吧,不借助于個體心理學,不能徹底認清有人為何要殺人如麻;沒有群體心理學,則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仍會有那么多人認為他不但做得正確,而且偉大無比。
莫斯科維奇在其著作《群氓的時代》導論中說:自群體心理學誕生一百年來,這門學問所取得的進展十分有限,后來的著述也許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致,但無論問題還是答案,依然沒有超出勒龐等人建立起來的框架。在塔德和勒龐之間,因為兩人的學說過于相似,曾發生過一場誰是群體心理學首創者的筆墨官司。但是塔德自有他的貢獻在,他對領袖和群眾的關系作了更深入的發掘,并對“交流”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充滿洞見,當代一些“大眾文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只是其思想的翻版。他筆下的現代社會的“交流”,同哈貝馬斯推崇的“理性交往”相反,只會把孤獨狀態下的理性人更迅速地改造成智力低下的群體。按他的理解,自從報紙這類媒體普及以來,一個坐在家里讀社論時評或廣告的人,與中世紀農舍里的村夫已經大不相同,他同千千萬萬的個人形成了一個“隱形群體”,同屬于某個中心,隨時能夠走上街頭。
與以上兩人相比,弗洛伊德只是這個領域的一個尾隨者,算不得開山之人。《群眾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一書是弗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勒龐著作的雙重刺激下寫成,他用“愛欲”和“戀父情結”之類自己特有的概念去解釋勒龐,試圖把后者的思想納入自己的精神分析體系。他在起點上有著與勒龐和塔德截然不同的理論預設,在后兩人看來,孤獨的個體還算正常而理性,只是到了群體中才會變得扭曲,他則認為個體的心理如果健全,那么到了群體中也沒有出毛病的道理。
說起來,在勒龐或弗洛伊德之前,有關群眾心理學的思想并非不見于文獻史。蘇格拉底就是死于被他“說話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眾;馬基雅維里在給他的“新君主”獻計時也說,人皆善于“忘恩負義、反復無常、裝模作樣、虛情假義”,所以統治者與其博取眾人愛戴,不如令其恐懼更安全。顯然,這些話與群體心理學中那些洋洋灑灑的敘述相距不遠。17世紀的英國普通法法官會說,他在斷案時既不能聽命于國王,更不能屈從于下院和民眾的意見;美國的聯邦黨人既知道存天理不能也不必滅人欲的道理,也曉得建立自由政體不能全靠統治者的個人品質和公民美德。他們雖沒有明確表述群眾心理學的原理,卻都暗示著對英雄和民眾的深刻懷疑。
但是,近代以前的世界在精神和制度權威的穩定性方面遠非今日能比,而動員民眾的手段較之現代社會則大為遜色,故歷史依然可以主要由帝王將相或宗教先知來書寫。從這個角度說,群眾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是與宣傳技術手段的進展分不開的。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價值世界的認同對象——各種“教義”——飄忽不定,表現出強烈的時尚化趨勢,這就為心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人提供了巨大機會。尤其是在失敗導致集體恐懼癥時,在人們都覺得需要變革而又不知如何變革時,在為生活空虛或認同失敗尋找替代品時,我們都會感到迫切需要“魅力領袖”的出現。今天,無論是政客還是廣告策劃,經銷商還是演藝明星,都在揣度群眾心理,因為只有群眾能為他們提供權力的正當性,提供金錢和名聲。
不過,有一點是這兩種人都值得牢記在心的。正如艾略特所說,人這種動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虛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機制之一,所以他喜歡那些折射出某種集體幻覺的東西。但是在現代社會里,這種喜愛總是短暫的。韋伯把它視為魅力領袖的事業逃不掉“平庸化”命運的根源;用莫斯科維奇的比喻來說則是,私奔時的激情澎湃,遠不如婚姻的恬淡來得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