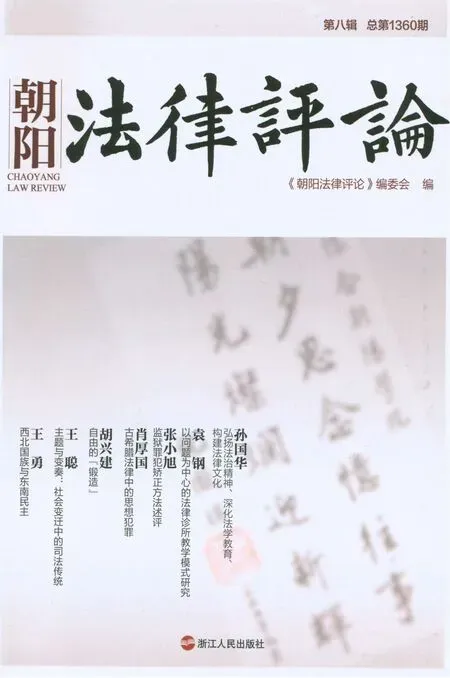法律教育的實像
——以朝陽大學夏勤、郁嶷和王覲的《法學通論》為中心
程 波
法律教育的實像
——以朝陽大學夏勤、郁嶷和王覲的《法學通論》為中心
程 波*
宣統二年(1910)冬,由汪有齡、江庸等人牽頭,聯絡北京的立法、司法界人士,以研究法學,鼓吹法治為目標,籌議辦以一所大學、一個刊物、一份報紙為中心的法學會,就商沈家本。沈家本極為贊成,并捐款相助。同年11月,北京法學會成立,沈家本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汪有齡①汪有齡(1879—1947)字子健,浙江杭縣人。清附生,1897年以浙江蠶學館官派生身份赴日學習新技術,后奉浙撫廖中丞改派東京學習法律,畢業于日本法政大學。回國任京師法律學堂教席,清政府商部商業雜志編輯。民國成立后,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局參事,8月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長,法律編查會副會長,1913年被選為參議員,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1918年8月任安福國會參議員,大理院推事。1920年任《公言報》社長。1913年朝陽大學首任校長。1921年至1931年任朝陽大學校長。1931年后到上海以律師為業。總理會務。根據法學會籌創以研究法學和開展法學教育為主的高等學府的宗旨,汪有齡與襄助辦學的黃群、蹇念益等人,殫精竭慮,各方奔走,他們呈請清政府審批建校,結果被駁回,只同意建法律研究機構。直到1912年才批準法學會建校,定名“民國大學”。接下來是校址選擇,汪有齡先呈請大總統袁世凱,獲得允準用前清翰林院房屋來建校舍。可是,工商部總長劉揆一,以國務院早先已將房屋批給工商部辦公為由,拒不交房。出于無奈,民國大學于1912年10月一紙訴狀把工商部告到京師“地審廳”,這就是所謂的民國“國民控告官署”(民告官)第一案。劉揆一以民事訴訟管轄不明為借口,稱京師“地審廳”是司法機構,無權審理民事案件,拒不出庭答辯,僅以工商部公函知照地審廳。作為民國大學原告的汪有齡當庭表示:“當此行政裁判所未立之先,人民據約法當然有訴訟法院受其判審之權,不然即人民無所控訴,豈非約法所載之權利橫被剝削?”盡管汪有齡的觀點十分在理,但在當時情況下,民國大學依然敗訴。①這樁“民告官”第一案雖以“官”勝訴告終,但另一方面卻引出了民國初年中國的行政訴訟采取“一元制”還是“二元制”立法與司法的爭論,其意義十分深遠。國務院只好另批北京朝陽門外的“海運倉”舊址給民國大學,取名朝陽大學,含有“早晨的太陽光芒萬丈,向民主法治邁進”的寓意。新成立的朝陽大學首推汪有齡為校長,1913年8月學校招生,9月10日正式開學,至1916年即有蔣鐵珍等129人畢業。②汪有齡:《初版序》(中華民國6年12月),載夏勤、郁嶷合述:《法學通論》(朝陽大學法律學講義),中華民國16年10月版。在朝陽大學執教者中,有夏勤、郁嶷和王覲等人先后任過朝陽大學《法學通論》課程的教員。在本文中,筆者將以朝陽大學《法學通論》的任課教員為中心,輯錄包括夏勤、郁嶷等人在內朝陽法律學人為《法學通論》寫的序文,力圖展現朝陽大學的夏勤、郁嶷和王覲等從事法律教育的實像。
一、夏勤、郁嶷與他們的《法學通論》及其《法學通論》序文輯錄
夏勤(1892—1950),原名夏惟勤,字敬民,一字競民,江蘇泰州人。夏勤16歲時,考入由沈家本和伍廷芳奏請成立的京師法律學堂。20歲那年,入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深造。畢業后,又在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研究部專攻刑法。1917年歸國,擔任大理院推事,并“以其學詔后進,所成就甚眾,凡京師各法政學校無不有夏子講席焉”③萬宗乾:《序》,載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

1919年至1928年夏,夏勤出任朝陽大學教務長。在夏勤長朝陽教務期間,“校務遂日益發展,來校者趾踵相接”。每屆高等文官及司法官考試,朝陽同學錄取比例很高,多次名列前茅。迄至1926年,全國各地法院普遍有朝陽畢業生的席位,“無朝不成院”成為當時司法界廣為傳播之語。朝陽大學多次因辦學認真、成績卓著而屢獲教育、司法兩部的明令褒獎。①1914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員視察該校,許為“管教認真,成績大有可觀”;1916年11月,教育部以該校辦理成績卓著而頒發特別獎狀;1918年3月30日奉司法部第2928號指令,許為“法學模范”;1921年12月10日奉司法部第155號批示,許為“課士程功,歷久不渝”;1922年6月17日奉教育部第302號批示,許為“辦學認真,教育有方”;1924年,司法部批獎“課程邃密,造就益宏”;1927年2月11日奉司法部第99號批示,許為“成績優異”;1927年2月14日奉教育部第42號批示,許為“辦學認真,成績卓著”;1929年11月15日奉司法行政部第1484號批示,獎以“該校自創辦以來,成績卓著,殊堪嘉尚”;1931年復奉教育部指令,謂該校“辦理有年,近更努力擴充,益求精進,自足嘉尚”;1933年1月11日奉司法行政部第52號批示,謂“第三屆法官初試,本學院畢業生錄取幾及三分之一,復多名列前茅,具征成績優良,深堪嘉慰”;1934年8月,復經教育部認為該校法科辦理成績優良,特補助法科圖書費八千元,1935年繼續補助;1935年1月17日奉司法行政部第62號批示,獎以“辦理有方,成績卓絕”。“校史志略”(四),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增訂版),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另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頁。1929年在世界法學會海牙會議上,朝陽大學被肯定為“中國最優秀之法律學校”。朝陽大學對中國法律人才的培養影響深遠,其畢業生在全國法律、政治等專業畢業生中所占比例最大,而且每次國家司法官考試被錄取的朝陽大學畢業生幾乎占三分之一。由于該校畢業生從事司法工作遍及全國各地,因此,有“無朝(陽)不成法(院),無朝(陽)不開(法)庭”之說。上述成績的取得,亦與夏勤“勵精圖治,擘劃周詳,慘淡經營,日不暇給”的教務工作是分不開的。
作為朝陽教務之長,夏勤不僅自己親身執教、親編教材,以樹立榜樣,而且鼓勵和協同教師,在認真教學之余,“窮探廣搜”,撰述“朝大講義”。當時,朝陽大學辦有印刷部,教授自己編撰講義,按課印發。這些法律學講義自成系統,闡述中外法理,回應立法爭議,成為北京各大學研究法學或參加司法官考試、文官考試的學生必備參考資料,許多人以擁有“朝大講義”為榮耀并加以保存。夏勤后來總結說,朝陽大學自創辦以來,“教科首重法學,凡主講斯學者,皆當代名流,所授講義類,網羅歐美鴻喆著述,而擷其菁英。參酌吾國現行法令,以評其得失,學者由此研求,既事半而功倍,政治家資為考鏡亦駕輕就熟。所以嘉惠士林,開拓學圃者,為效尤巨”①夏勤:《再版序》(中華民國9年12月),載夏勤、郁嶷合述:《法學通論》(朝陽大學法律學講義),中華民國16年(1927)版。。在夏勤和朝陽大學教師共同努力下,朝大“法科講義”,“世論推許,頗負今譽”。②夏勤:《五版序》(中華民國15年1月),載夏勤、郁嶷合述:《法學通論》(朝陽大學法律學講義),中華民國16年(192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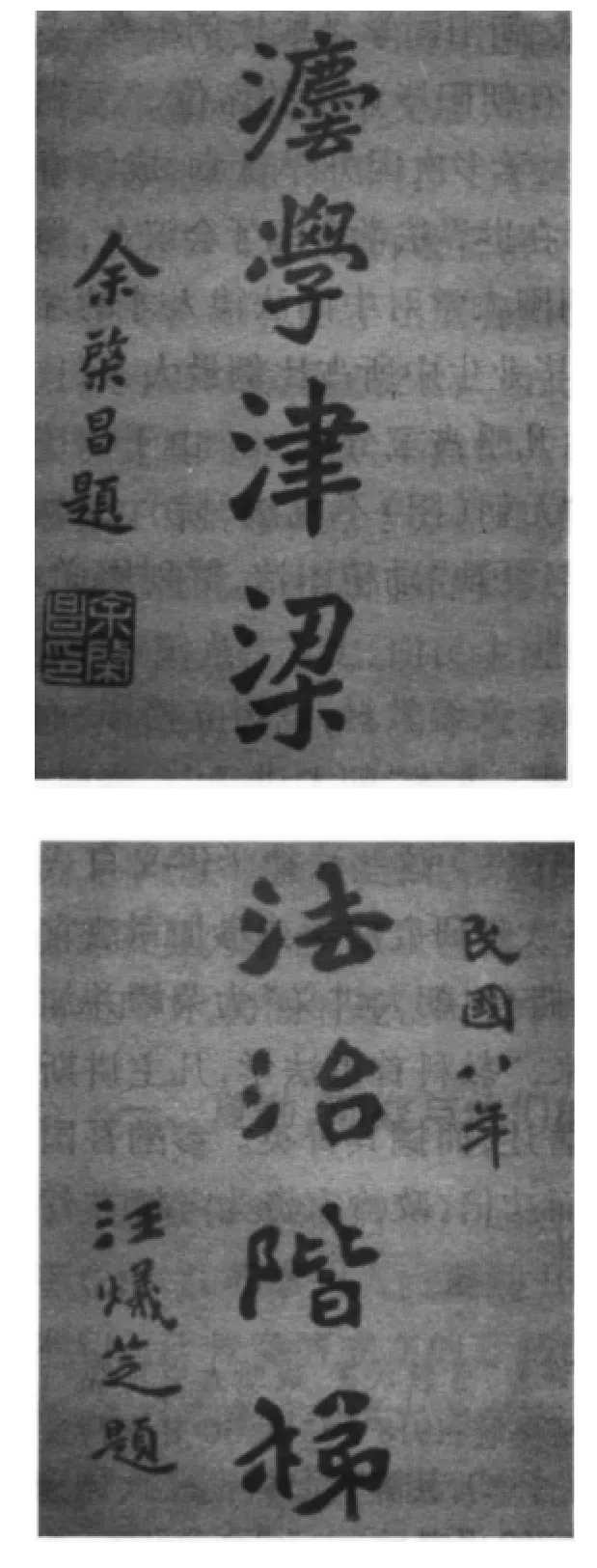
中華民國8年(1919),“年少才俊,志守端直”的夏勤與郁嶷,“同居北京城,罕接人事,扺掌盱衡,相約著書”③郁嶷:《序》,載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2頁。,通過“朝夕潛研”,合編出版《法學通論》四卷。在這本《法學通論》的版權頁上,明確記載系由朝陽大學出版部發行,北京東西制版所印刷,時間是中華民國8年(1919)9月10日印,10月10日發行,全書128頁。從民國6年(1917)開始,朝陽大學將教師講義正文及學生聽講筆記及參考而得的資料,編為疏注,先后出版《法學通論》、《法院編制法》、《憲法》等29種“朝大講義”。夏勤與郁嶷共同講述的這本民國8年的《法學通論》亦是其中之一種。作為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的《法學通論》于民國9年(1920)再版,到民國16年(1927)10月,該書出至第六版。在民國8年(1919)這本《法學通論》的初版扉頁上,汪燨芝④汪燨芝(1882—1928),字鹿園,安徽休寧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歷任清農工商部主事、京師法律學堂教習、修訂法律館協修、民國法制局參事、大理院推事兼庭長、法典編纂會調查員、北京總檢察廳檢察長。民國北京政府時任大理院一庭庭長,司法部司法講習所學科主任兼教員。題有“法治階梯”,民法專家余棨昌①余棨昌(1881—1949),字戟門,浙江紹興人。1902年以京師大學堂高才生選派留學日本,1911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回國后曾任清政府戶部主事。民國北京政府任大理院民二庭庭長,司法部司法講習所講師、所長。歷任法制局參事、司法懲戒委員會委員、司法訓練處處長兼法典編纂委員會顧問、大理院院長兼司法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修訂法律館總裁。民國后,除抗戰八年,一直任朝陽大學教授。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題有“法學津梁”,銅仁萬宗乾及是書編纂者之一郁嶷分別作序。為保全資料,特全文輯錄萬宗乾、郁嶷寫的《法學通論》初版序言。
萬宗乾序《法學通論》全文:
我國自建共和以來,八載于茲,政變紛呈﹝乘﹞,訖無寧日。法治國之正軌,既不可得而見。即憲政之幸福,亦渺不可期。推原其故,實由一般人民缺乏自治能力。政識瞢闇,常為武人政客所挾持。此國民教育所以不可無法政常識以陶鑄之也。同學郁子憲章夏子敬民,賦性孤介,不好徵逐,自顧同居北城,杜絕塵俗。朝夕潛研,陶然互樂。近以合編法學通論見示,屬為弁言。余不禁有深感焉。郁子本博古通今之才,抱艱苦卓絕之志,曾任江寧地方審判廳庭長,選主金陵、沈陽、燕京各校法科講席,其言論風采之表現,于各種新聞雜志也。望之者莫不嘆為今之古人。宜其屢為南北當道諸公所羅致。然又每有用不能盡其才之憾焉。夏子為江南志士,游學東瀛。學行優美,常冠其曹,畢業首選,譽聞海外。歸國后,以其學詔后進,所成就者甚眾。凡京師各法政學校無不有夏子講席焉。近復供職法曹,本其經驗,著《指紋法》一書,海內風行。嘆為創作。其學理經驗,兩俱淵富。實為時賢中所不易觀也。二君造詣之深,其法學名著已達于專門名家之境。顧惟汲汲以法學通論問世,先其淺者近者,而后其精者深者。蓋有見夫法政常識為國民教育所不可少之學科。思有以啟其鑰而通其窮,以徐至夫廣大高明之域,法治前途,庶其有豸。其用心亦良苦矣。第法學通論之作,近人譯著不下數十種。而擇其最適用,可稱完全者卒鮮,是編詳明要約、辭旨雅訓,教科善本,得未曾有,行見洛陽紙貴,意中事也。余讬同學舊誼,知之有素,故樂為之序。
銅仁萬宗乾拜撰②萬宗乾:《序》,載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
上文中,提及的“郁子憲章夏子敬民”,即指郁嶷和夏勤。郁嶷(1890—?),又名祖述,字憲章,號憤園,湖南津市人。光緒三十三年(1907)7月,郁嶷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1912年秋,郁嶷參加了北洋法政學會,他和同學李大釗被推選為學會編輯部長,負責籌辦法政學會刊物《言治》,主編法政學會刊物《言治》共6期。先后在《言治》、《言治季刊》、《晨鐘報》、《甲寅日報》、《斯覺》、《甲寅日報》、《青鶴》等刊物上,或為編輯,或是撰稿。有《人治與法治》、《言治季刊宣言》、《歐洲與移民》、《歐洲人口出生率衰減之原因》、《人口過庶論》、《人口過庶后論》、《代議非易案》等文章傳世。1918年,郁嶷在朝陽大學執教,同時兼任北大教授。郁嶷曾任湖南財政廳廳長,擔任過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主持制訂了《親屬法》。他的《中國法制史》是比較方法運用的杰出成果,尤其在親屬法等方面,表現出扎實的基本功和獨到的見解。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遇難后,郁嶷辭去公職,致力于法學教育與研究,筆耕不輟。郁嶷先后執教任于奉天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北京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河北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學府,亦先后出版了《中國法制史》(1920年)、《法學通論》(1919年)、《繼承法要論》(1932年)、《比較憲法》、《政治學史》、《貨幣綱要》、《法學通論》等10種著述。還出版了《郁嶷文集》、《郁嶷論文集》。原《言治》編輯、云南省高等審判廳廳長黃旭先生在《郁嶷文集》序中說:“余聞自古文人,鮮達而多窮,窮之者,所以工其文也。以郁子之懷負如彼,而十年以來,長刑訟于南京,總財政于長沙,艱屯錯午,皆不得行其志以去。比者主京師中國朝陽兩大學講席,一志學術避遠政潮。豈天將困厄之使顓力于文之一途而工之耶?吁是可嘆也。”

郁嶷序《法學通論》全文:
國人習性,喜徵逐,躡浮響,或枉道辱身以求榮,或縱情歌舞以墮志。自僻州陬境至通都巨埠,皆然。而京師為最。余旅京三載,所接士大夫,工語酬應,研精絲竹者,十嘗八九,而冥縋孤往,有志學術者不一二觀也。同學夏子敬民,年少才俊,志守端直,處京師紛華之會,值政局擾攘之秋,而抗志千古,獨行踽踽,勵品竺學,殫心撰述,所著指紋法一書,本其經驗,宏闡理蘊。既為海內所稱頌而于刑法及刑事政策,肆力專攻。洞燭纖微,節解枝蒐,征引精博,亦將以次餉。世之澆學喪,國亡無日,得夏子榰柱其間。庸能振聵發微。闢榛蕪乎。余(梼味款?)啟又迫窮患,幽憂侘傺,學殖荒落。夏子顧引為同調,辱與討論,邇者同居北京城,罕接人事,扺掌盱衡,相約著書。彌月之間,遂成法學通論四卷。夏子蘊淵富,區區短簡,豈足盡平生。余以疏陋,附名其間,實增漸愯,爰書卷首,以志歉焉,抑以見夏子虛懷為謙,不自封殖之盛德也。
民國八年秋九月澧陽郁嶷序
在《法學通論》緒言中,夏勤認為,法學通論“總闡法學之要義,示初學者以準的也”。“不獨法學有專門,而諸法之中,類別業分。亦各馳思于所欲焉,以自為方,然其始也,非粗識大體,則無由進研邃密,此鉤元箕要,為法學要旨之詮釋,有不能不資乎法學通論也”①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這一看法,在當年中國法學理論教育起步之時,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進而夏勤明確地指出,法學通論在法學教育中的功能作用,“一方為學者進攻專門之階梯,一方又為普通人類所應具之常識”②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
從來編纂法學通論者,其詳略次第,雖各不同,然夏勤之《法學通論》體例,首論國家,次述法律,再次論權利,最后殿以法學,自有其特色。對這一編纂體例,時人稱善,謂之為“先其淺者近者而后其精者深者”,“思有以啟其鑰而通其方,以徐至夫廣大高明之域。法治前途,庶其有豸。其用心良苦矣”。③萬宗乾:《序》,載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夏勤在緒言中,對此作了簡要的說明。現抄錄如下:
積人類而成社會,由社會而演國家,國家既立,法制斯起,政治以生。蕓蕓者眾,既不能離國家而獨立,以生斯國也。茍于國家之義何居尚爾茫然,其去榛狉未化之民幾希。故本書編纂次第首論國家。
繼國家而起者,是曰法律。法律者,所以范制吾人外部之行動,齊其不齊,一其不一。抑強橫,扶羸弱,以維持國家社會之秩序也。國有常刑,犯者必懲。朝莫跬步,舉有法律繩其后,國俗境禁,遨游所抵,且需聞問,烏有長蟄斯土,而于法律之謂何瞢然茫然。能以遂其生存者乎。故次述法律。
法律所保護者,是曰權利。人自呱呱墜地,即具人格,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泊夫漸長,權利之欲望盛,而藉法律為保障之塗﹝途﹞益廣,然而權利之觀念不明,斯行使之方術多窳。故法律意義既明之后,次論權利。
近世國家,號稱法治,法所由興。類緣于學,學術榛蕪,則法律終古無進步之望矣。故總覽古今,殿以法學。①夏勤、郁嶷:《法學通論》,朝陽大學出版部1919年版,第1頁。
這一編撰體例,論題已涵蓋法學通論的核心內容。夏勤如此編纂,一方面是因為近代中國大學的法學理論教育以法學通論為建構的起點,并沒有編撰先例可循;另一方面則是夏勤在京師法律學堂和日本留學,系統接受和學習西方法學理論使然。至于夏勤《法學通論》的內容特色,筆者在《朝陽法學評論》第二輯的一篇文章②參見程波:《“法學津梁”——法學家夏勤與朝陽大學》,載《朝陽法律評論》第二輯,中國華僑出版社2009年版。已經作了說明,此處從略。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隨著時光流逝,夏勤和郁嶷在1919年寫的《法學通論》教科書,現已經難得一見,甚至一些著名的圖書館也未有收藏。與朝陽大學淵源極深的中國人民大學,其圖書館藏亦僅存孤本。筆者在知見這本朝陽大學出版的《法學通論》教科書時,發現本書紙張發黃、動輒易碎。至1946年,這本《法學通論》又由夏勤單獨署名出版(高承恩發行,正中書局印刷實驗所印刷)。這一在戰爭時期出版的版本,使用的是時稱“土紙”的紙張,色澤不一,品質極差,紙薄透明,間或有洞,以至今天欲影印都已不能。為搶救、整理這些朝陽大學的法學作品,筆者在點校夏勤、郁嶷的《法學通論》過程中,特別參考了夏勤、郁嶷1919年的《法學通論》版本及1927年《法學通論》(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第六版。而這本作為“朝大講義”的《法學通論》版本,收入夏勤、郁嶷合述、王選疏的《法學通論》和何超杰述、李祖蔭疏的《法院編制法》等法律講義有兩種。通過這本“朝大講義”第六版,筆者再將汪有齡寫的初版序及夏勤為《法學通論》寫的再版序、五版序和六版序,加以整理并輯錄出來。這樣,加上萬宗乾、郁嶷寫的《法學通論》初版序言,以及居正于1946年為夏勤《法學通論》所寫的序文,①民國35年(1946)10月,夏勤在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的基礎上,將其與郁嶷合述的《法學通論》稍作修訂,單獨署名出版,發行人為高承恩,由正中書局印刷實驗所印刷。該書在原版本的基礎上,對所引西哲人名,均后附英文,并增加注解以釋觀點,有利于查證《法學通論》之思想來源。時任司法院院長的國民黨元老居正先生還親自為夏勤這本《法學通論》作序。從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分析,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學人編撰的法理學教科書。所有這些序文,既為朝陽大學法學院的《法學通論》教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又為我們描繪朝陽法律教育的實像提供了珍貴的線索。以下是汪有齡寫的初版序及夏勤為《法學通論》寫的再版序、五版序和六版序的全文輯錄:
汪有齡初版序全文:
朝陽同學蔣鐵珍等一百二十九人,既畢業乃收集三年來之講義及聞諸諸先生之口授者,以為講義錄。既成,問序于余。余維綜核學說,研求法理,此學法者之事也。依據法條,平亭獄訟,此用法之事也。用法學法,雖分為二事,而其本則一。諸君今既畢業,是學法之事已終而用法之事將始。雖然用法之難也,非公則私,非平則偏。吾國自改革以來,雖朝野昌言法治,然民商無適切之規程,判斷以意思為法律。或罪本相同而處刑則異,或身蒙大戾而問責無從。有法而不能用,與用之不得其固由盲從之輿論,與武斷之政治左右于其間,抑與學法之初心固大相刺謬矣。諸君學法既成,他日用法,吾愿斤斤于公平兩字也。此則余今日不能已于言者。是為序。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汪有齡撰
夏勤《再版序》全文:
庚申季夏,朝陽大學法律科畢業諸君擬收集歷年講義。分任校讎,由校對付諸剞劂。余主講是校,五稔于茲。近復承乏教務,與諸君相處既久,與是校關系尤切。誼不能無一言以弁簡首。夫學術盛衰,國運系焉。而名喆碩儒,潛討幽縋,鴻儒巨制,層出不窮,則學術隆盛之表征也。
余曩者負笈東瀛,見彼邦人士修業之勤,進德之猛,著述浩瀚,日新月異,心竊慕之。以為其國運蒸騰,度越等夷者,有自來也。
吾華文明鳳居彼上。迺近古以還,風氣固陋,學術榛蕪,蕓蕓者眾,相率于頹廢靡俗之中。既酣嬉而不迫。而二三操觚之士,有志撰述者,又往往摭拾膡義,自欣拱璧,災禍黎棗。貽譏大雅。他勿具論。即以法學一科言之,海通以后,承學之士,習以綦眾。然誠走偏﹝遍﹞書肆,欲求一法理精善之著述,不可得也。有識君子寧不引為深憂乎?本校自創辦以來,教科首重法學。凡主講斯學者,皆當代名流。所授講義,類網羅所授講義,類綱羅歐美鴻喆著述,而擷采其菁蕪。參酌吾國現行法令,以評其得失,學者由此研求,既事半而功倍,政家資為考鏡,亦駕輕而就熟。所以嘉惠士林,開拓學圃者,為效尤巨。爰刊以餉世,藉廣流布而國運之盛。其或造端于此乎。余所厚望也。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夏勤序
夏勤《法學通論》五版序全文:
法貴適時,而因應蛻變。張皇補苴于不敝者。學術為之也。故瞻人國者,考其學術之盛衰,而法制良窳可驗矣。海通以來,國人競言興學,顧通都大邑,□舍林立,而髦士論著,斐然成章,足資研討者,闃焉無聞,私竊深擾。以為士習儇薄,學殖荒落,至于此極,預期法制之革新,是卻行而求前也。寧有幸乎。朝大立校,垂十余稔(年),法科講義,刊行四次。世論推許,頗負今譽,雖不敢詡為名篇巨制,足以潤色鴻業。而精義諦解要,可潛發幽光。鹖冠云,中流失舟,一壺千金。撰述諸公,窮探廣搜,嘉惠士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庶幾一壺之獻乎。茲值五版,特弁數言。異日學術之興,淵源有自,則法制改革,于焉攸賴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夏勤序
夏勤《法學通論》六版序全文:
韓非曰,國有常法,雖危不亡。明乎法者,國之紀綱,緝暴鋤惡,風行草堰。所以安堵民生,寧謐閭閻者。此物此志也,顧美列強,揭橥法治,政績斐然,彪炳人寰,古賢今喆,后先輝映,東西同揆,良足尚矣。改革以還,國人競言法學,遠搜舊聞,旁擷歐化,浸淫鼓蕩,垂十余稔(年),而徒勝口說,著述闕然。將何以驗進修之臧否,資來學以考鏡乎。本校法科講義,歷年鋟行,今凡六版矣。諸家論列,與時革新,學士疏注,不囿師說,際此法學凋敝,彌望荒涼,故不敢詡為饋貧乏之糧,而要于寥落沉寂之出版界中,少紓耿光。庶使好學敏求之彥,感奮興起,其于提倡法治,或不無小補歟。
中華民國十六年孟秋夏勤序
居正《法學通論》序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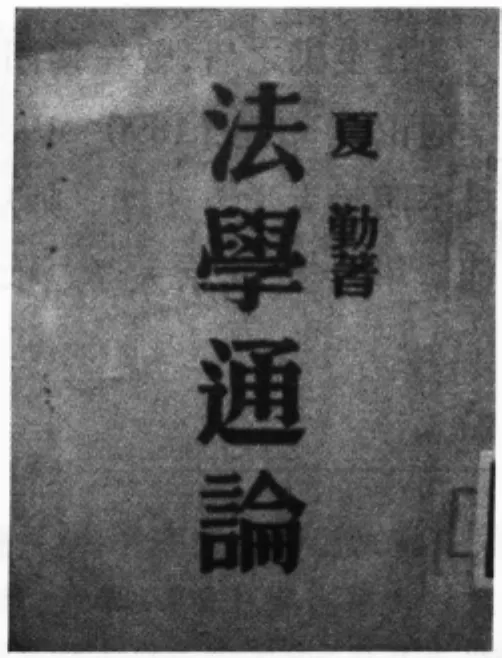
治國準繩,示民軌范,窮于理者唯心,本乎事者唯物,其惟法學歟。條緒紛披,文理密察,綜萬殊而會歸其適,約一貫而要言不煩。其惟法學通論歟。夫法者典也,天下之公道也。非任人之所得私也。私則作法自斃己。法者律也,天下之正詣也。非任人之能得骫也。骫則民無所措手足,亂之所由興也。吾儕法界,青年讀法,皓首明刑,果體證到自性能生萬法,萬法本乎一心,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悖,上也。聽訟猶人,片言折獄,哀矜勿喜,察必以情,次也。思不出位,案牘勞形,又其次也。若夫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路溫舒之所痛絕,斯為下矣。
吾人須知法學者,形而上之學也。包括宇宙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上通于無上大乘各種之宗教哲學者也。釋家言一真法界,何謂一?純粹精也。何謂真?其實不虛也。儒家亦言,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不幾與釋家言,若合符節也乎。雖然,心法吾知之,而不知法界因何建立,是則孔子所訾,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適足見其義,墮耳。故宗教家言一真法界,有理法界、事法界,所以者何?法必因事而生,法即據理而立。若離乎事,遠乎理,而求別有所謂法者,從古至今,由中推外,無有是處。此可斷言也。故事理者,法之實相也。然若偏計所執,而謂事是事,理是理,法是法,拘泥而不通,支離而不貫,是又著相而不由其道也。故必進而推究闡揚,至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何以故?礙者,障也,塞也。礙于理則理障,礙于事則事障,礙于事事則事事障。如果只排除一事障,而或有理障,則仍滯塞而不通,排除理障,而或有事障,推而極于事事障,其不通也更甚。故必至于無礙,則事障、理障、事事障,均排除凈盡,融合無間。由有陋悟人,無陋有學,辯證無學,亦行布,亦圓融。斯乃朱子所謂:“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即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則通之至也。夏子敬民,蜚聲法界,垂三十年,探賾妙門,精窮奧義。近出其平日所授《法學通論》,付諸梨棗,問序于余,余為雜說如上,或不免有隔靴炙踝、畫蛇添足之譏。然學者,茍因此玩索而有得焉,庶幾與夏子《法學通論》互相發明,言語道斷,我法雙意,倘亦為法界善知識所許也乎?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谷雨前三日,居正覺生氏序于重慶山洞準提陋室。①范忠信、尤陳俊、龔先砦編:《為什么要重建中國法系——居正法政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406頁,收入這篇為夏勤《法學通論》寫的序。據編者交代,該序文選自李翊民等編:《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臺北1954年印行,第593—594頁,但上書編者考證該序文寫作時間有誤。本書點校者認為,這篇序文不是居正于1927年為夏勤《法學通論》出版所撰序言,而是1946年為夏勤《法學通論》出版所作的序言,落款日期為民國三十五年亦即1946年。居正在序文中說:“夏子敬民,蜚聲法界,垂三十年,探頤妙門,精窮奧義”,亦可證明該序不是寫于1927年,而是1946年。——點校者注
以上《法學通論》教材的編寫和時人關于《法學通論》的序文寫作,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朝陽大學法律學人“學法”、“用法”的心路歷程,而這種作為朝陽大學學生的“法治階梯”和“法學津梁”的教科書,亦是朝陽大學法律教育實像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能普及法學知識于國民”:王覲與他的《法學通論》
在夏勤之后,曾在朝陽大學任教的湖南瀏陽人王覲亦曾編撰過一本《法學通論》。王覲(1890—1981),字漱平,1914年于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后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習法律。師從日本刑法學大師牧野英一博士。1919年歸回,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大學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及朝陽學院代院長。王覲曾著有《中華刑律論》,時人“喜其可為明刑弼教之助”,①王文豹:《“中華刑律論”序》(中華民國14年5月),載王覲:《中華刑法論》,姚建龍勘校,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并稱許王覲“于古今中外刑法學說論述,以及沿革,博習淹通,精微洞見”。②呂復:《“中華刑律論”敘言》(中華民國14年4月),載王覲:《中華刑法論》,姚建龍勘校,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王覲這本《法學通論》,由公慎書局于民國10年(1921)6月18日初版發行,1923年1月出至訂正增補的第4版。該書封面的“法學通論”四個字由曾在日本學習法政的范源廉先生題簽,并有鄭晟禮先生為之作序,鄭晟禮在序中說:
法學通論為泛論法律之學。持義貴新,取材尚富。世界學者,精研法理思想變遷,率月異而歲不同。非若一成不變之物,著以為法令者比也。若夫治斯學者,陳陳相因,舊說是封,則往編具在,豈待更有所論述哉。是非取精用,宏得鉤玄,則失之則遠矣。予友王子漱頻,劬學有年,研究深邃,出其所學,轉輸學子,別成《法學通論》一書……學子得由此,以為階梯,進而窺公私各法之堂奧。原來問學,俾法律常識普及于人人,則王子斯書,不惟有裨學益,更于法治之途為助非淺焉。……③鄭晟禮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
王覲在自序中,對編纂這本《法學通論》亦有所交代。他說,“欲臻國家于法治域……貴乎完善之法律,尤貴乎能普及法學知識于國民”④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在作者看來:
法律之于國家和個人關系,即重且大。……惟是法律之學,乃精神的科學,欲究其奧蘊,窮其深理,既非一朝一夕。研究所得而能。復不能強人人以悉,喻是則對此浩瀚之法,又悉其梗概,明其綱領,必有響導(向導)引之以入,必有階梯攜之以升。階梯響導舍法學通論其誰屬哉。……⑤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
據此,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王覲在編撰這本《法學通論》時,作為一名講授這門課程“有年”的資深教員(瞿同祖先生在燕大讀書時,就聽過王覲講授過《法學概論》課程),對當時社會上“陳陳相因,舊說是封”的《法學通論》教科書是不甚滿意的。因此,王覲在自序中指出,“諸學子咸以坊間陳物不足以資考鏡”①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這樣,在當時法理學資源相對匱乏的京城法政教育的現實中,王覲從“能普及法學知識于國民”的目標出發,特別強調法學通論的“階梯”、“響導”作用,并期待該書“以期為法治之助”,從而表達了他的寫作目的。
王覲的這本《法學通論》,全書篇幅不大,共156頁,分緒論和本論兩篇結構。當時,對我國法學理論教育影響頗大的日本《法學通論》教科書均流行有“各論”。對此,王覲一方面認為,“我國法律不備,僅能就通論述其原理原則,而于各論一編,多無成規可循,不得同時付梓,深為遺憾”,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擬俟異日,法律公布再行庚續”。②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正是這種“深為遺憾”,王覲這本《法學通論》與稍早的夏勤那本朝陽大學的《法學通論》講義,均開創了中國人自己編撰《法學通論》教科書的傳統。即以“就通論述其原理原則”的“本論”為主體的《法學通論》編纂模式,為中國法理學形成發展作了初步的準備。
在緒論中,王覲對上述編纂體例作了說明。他認為法律學通論是“說明法律學之大體,為初學法律者之階梯”,“進而為各種法律之研究,養成實地應用之法律思想為目的”。③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這是因為,“法律有公法私法,國內法國際法之區別,其間相互關系之處,皆須融會貫通,是故考究法律者,非曉然法律學之綱領,通觀法律相互之關系,則有如墮入五里霧中,茫茫不知所之”。因此,在王氏看來,法學通論“乃是以網羅法律學之全體,而無所遺,庶異日研究各種法律特殊之原則,得尋其途徑焉”④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頁。。于是,王氏對這本《法學通論》的編纂之順序為緒論與本論二篇,作了以下說明:
以緒論為三章,第一章說明科學之類,藉悉法律學之位置。第二章說明法律學之范圍,以示法學通論之本領。再于第三章中說明法律與其他科學之關系。然后及于本論關于法律之意義、淵源、效力、分類既權利義務等法律全體之概念,加以說明焉。⑤同上,第2頁。
接下來,結合王覲這本《法學通論》教科書的相關“知識論述”,作些說明。
關于法律學的范圍。當時,一般均認為,法律通論是“說明法律學之大體”。故王覲在緒論的第二章中,特別就“法律學”之范圍加以說明,“以示法學通論之本領”。在王氏看來,“法律學者為研究法律之學”:
(法律學)研究基于人類知性之社會的生活之秩序,說明其過去、現在、將來之科學也。法律的現象變遷靡常,因地因時,亦自有異,故所謂,不得為科學之目的,僅能以之為技術,供吾人之應用者。是殆不然。何則科學之為何物,系相對于諸種法律現象,理解其因果關系,智識之總體而言。至技術則為達實際上之目的。諳練通達而已。若是則對于法律的現象,悉其原則,理解其因果之關系者,曰法學,僅因實際應用得精熟法律之技術者,曰法術。……故研究法律者,須考其根本之科學,然后于末葉之技術焉。①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9—10頁。
在第二章的前三節中,王覲還分別討論了“沿革法律學”、“比較法律學”和“系統的法律學”等法學研究的方法。在他看來,沿革法律學是以“歷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法律,敘述古代之變遷及于現在之關系者也”②同上,第11頁。。而比較法律學者,“比較古今東西之法律,研究其性質之差異,取其共同點,以理解法律進化之原則為目的者也”③同上,第13頁。。至于系統的法律學者,“分析一國現行之法律,發見其原理原則,以系統的排列而研究其法理之謂也”④同上,第14頁。。在上述三種法學研究方法中,王覲特別服膺“系統的法律學”,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常說的“分析法學”,王氏認為,“法律研究以理解現行法之法理為急務,故系統的法律學誠為法律學中的樞鍵”⑤同上,第15頁。。
在“法律學”這一章的第四、五節,王覲又說明了“法律哲學”和“法律學通論”這兩個概念。所謂“法律哲學”者,“以研究法律之現象最高原理或根本的原則為目的者也”①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6頁。。正是基于研究法律現象之“最高原理”和“根本的原則”,王覲區別了沿革法律學、比較法律學和系統的法律學與法律哲學的不同,他認為,法律哲學的終極目的在于,“能洞悉法律之進路,評判現行法律之善惡,為將來之法者所采方針之指導,以冀增進國家人民之福利”②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6頁。。而所謂“法學通論”,王覲講了四層意思:一是“為法律學之階梯也”,二是“明法律學之本領也”,三是“明法律學之概要也”,四是“為法律哲學之階梯也”。以上四者,王氏總結說:
要之,法學通論之目的,不獨使學法律者得法律全體之智識,并令一國之人通曉國法之大體。蓋國民公私之生活,皆統御于法律,生命、生身、自由、財產,莫不惟法律保護之,是賴此普通教育學校,近無不增此一科者。
法律與其他學科之關系。在法律與其他學科之關系中,王覲從對法律與政治關系的認識出發,分別討論了法律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醫學的關系。他認為,“法律者為政之要道也”,“法律隨政治變遷而發達,故研究法律須注意政治之沿革。觀一國之政治,須知一國國家組織之憲法,研究一國之憲法,尤以洞悉其政治史為必要。憲法為政治史之結晶物,是憲法之研究與政治史之研究,有密切之關系,不可須離也”。③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16頁。在王覲看來,“為人類社會生活秩序之法律,發生于人類社會組織國家以后,是國家為法律之源泉”。故“無國則法律亦不成立,無法律國家亦不存在。……國家制定法,規律社會生活秩序,依此統治國民,以達其行政目的,是法律為國家行使政策之一種手段”④同上,第22頁。。而法律與經濟的關系,在王覲看來,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法律為保護經濟關系而存,經濟關系賴法律保護始發達。”⑤同上,第24頁。至于法律與醫學的關系,王氏從法律家研究法學以資實際應用,醫學者以醫學研究之結果,行審判鑒定時,則是法律家須有醫學上之知識,而醫學者亦必有法律上之知識也。
關于法律的概念。王覲認為,法律者維持人類社會的生活,定生活關系之規則為一般的且強而行之者也。對這一定義,王覲強調了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法律者秩序之規則也;二是法律者生活關系之規則也;三是法律者維持人類的生活,定生活關系之規則也;四是法律者依共同團體之公力得以維持生活關系之規則也。①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27—29頁。在該書第四、五章,王氏分別討論“法律之發生及目的”和“法律之維持”,這兩方面的內容,都與王覲對法律的概念的認識有關。例如,王氏從“法律者為維持團體生存,整理秩序而發生也”②同上,第40頁。。進而認為,邊沁關于“法律之目的,在使最多數之人民享最大之幸福”的享樂主義,以及耶林關于“法律為確保人類生存之要件,茍能保一般國民之安全秩序”的秩序主義均是最為重要的“法律之目的”。③同上,第41—42頁。至于“法律之維持”,王覲說:
法律固賴有國家權力之強制以維持其效力,然維持法律僅持形式上之強制,其力量異常薄弱,是故非有他物為之輔助,不為功。他物者何?曰內部之強制是也。內部之強制力分為三:恐怖心、道德心、實利心。④同上,第43頁。
關于法律與國家的關系。王覲認為,國家者是以一定土地為基礎,有統治“組織之共同團體”,在這種共同團體中,“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區別。治者以團體全體之公力,強制其各部使各團體成員服從共同團體公益上必要生活關系之秩序”⑤同上,第32頁。。王覲認為,國家這種“公力”乃是統治國民最高權力,即主權。關于國家主權,王覲通過兩個方面加以說明:對外,主權在國際法上,“稱為國家獨立權,又曰對外主權”⑥同上,第11頁。。對內,主權在用法上稱為統治權,“統治權者,國家之最高惟一之權力,與獨立權為對等之權利也”⑦同上,第11頁。。在作了上述說明之后,王覲指出,國家主權雖屬一國最高之權力,而其作用活動也得分立法、行政、司法之三面而言之。⑧同上,第33頁。因此,王覲分別就“國家制定法律”、“利用法律且執行法律”以及“解釋法律而適用之”等三個方面定義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關于法律與宗教及道德之關系。對這一問題,王覲論述得較為詳細。他認為,時至今日,政治思想發達,法律亦隨之進步。宗教與政治分別益顯。于是“信教自由,莫不認為憲法上之大原則”。①王覲為《法學通論》作的序,載王覲:《法學通論》,公慎書局1923年訂正增補4版,第34頁。王覲認為,法律與宗教教義雖同屬人類行為之法則,但在“客體”、“威力”、“制裁”、“目的”等方面,亦存在差異。在對法律與道德關系上,王覲列舉了八種重要學說,在他看來,“法律與道德混淆時代,道德為主,法律僅資輔助”,“二者獨立分離,性質亦有所異”。②同上,第37頁。因此,王覲取其適當者為區別之標準,指出道德與法律,雖也有“客體”、“威力”、“目的”等方面的差異,但“二者素不抵觸,不過其支配之行為有廣狹而已。故違反法律者必定背乎道德者,非即違犯法律之規定也”。這種認識在當時已屬先進。王覲還說:
近世文明各國道德與法律相輔而行。如親屬法關于夫婦間權利義務之規定。親子間權利義務之規定,以及親屬相互撫養之義務之規定等,莫非由道德上之思想而來。誠以法律有明文,則道德上之法則,可藉國家強制行之,如其不然,吾恐無良心之人,肆其不道德之行為,法律將無可如之何矣。是法律所規定,俟國民道德心之發達始先達其目的。道德養成亦惟法律是賴焉。③同上,第39—40頁。
在這里,王覲還表達了他的法律之效用觀。他認為,法律既無萬能,于是道德、宗教、良心、習慣等,均是“補助法律之效用”的“輔助資料”。④同上,第45頁。其他諸如法律制定之手續、淵源、效力、解釋、分類、制裁、內容以及法律上之權利,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之,通過對上述作為基礎科目《法學通論》教科書的研究,筆者認為,20世紀20年代以后,這些由朝陽大學夏勤、郁嶷和王覲等人編撰的《法學通論》教科書,可以視為是一種過渡的、可塑的形態,成為“傳統”法學向“近代”法理學“嬗變”之間的媒介,為近代中國法理學的形成發展做了初期準備。
(初審編輯 林藝芳)
Real Image of Legal Education:Focusing on General Theory of Law by Xia Qin,Yu Yi and Wang Jin at Chaoyang College
Cheng Bo
*程波,湖南商學院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