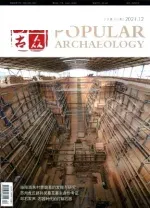金戈鐵馬 北方重裝騎兵再現
文 圖/禺 斤

東晉十六國時期,戰爭頻仍,騎兵往往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作戰時人與馬都會穿一套防御性的鎧甲。但是,北方民族的重裝騎兵形象一直掩映在歷史的霧靄中,遼寧喇嘛洞墓地讓我們有幸拂去時間的塵埃,重見這段真實的歷史影像。
《宋史·儀衛志六》記載:“甲騎具裝,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為里,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褖,青絁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鈌,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騰蛇。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

5號墓木棺內的鐵甲堆積5號墓位于喇嘛洞墓地東區,長5、寬4米。鐵甲堆積位于該墓棺內墓主的足下,人甲和馬甲的甲片多散亂銹蝕。
鐵甲堆積原來為“甲騎具裝”
遼寧喇嘛洞墓地是我國北方地區迄今所見最大的一處以三燕文化(即十六國時期的前燕、后燕和北燕)墓葬為主的大型墓地,其相對年代為3 世紀末至4 世紀中葉。因其地屬遼寧北票市南八家子鄉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組而得名。曾被評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遼寧喇嘛洞墓地是一處大型墓地,該墓地計有墓葬420 座,占地面積近1 萬平方米,出土陶、銅、鐵、金、銀、骨等各類隨葬品5000 多件(副、套)。其中5號墓內的甲騎具裝復原后重現了當時我國北方重裝騎兵的雄偉形象。
1995年10月11日,在發掘領隊張克舉(已故)的主持下,開始對5號墓進行考古發掘。此墓位于墓地東區,長5、寬4米,屬于墓地中的一座大型墓葬。經過1 天的緊張清理之后,考古隊員的目光被一處罕見的鐵甲堆積所吸引,它位于該墓棺內墓主的足下,平均厚度20 厘米左右。位于其西南部之上的人胄和馬胄尚可見其原形,人甲和馬甲的某些局部雖保存尚好,未經大的擾動,但表層甲片多數已散亂,殘碎亦較嚴重,大多銹結成塊狀。部分甲片雖保持著原來排列的形態,但在總體上基本呈現為無序堆放之狀,很可能是在其入葬時被有意拆散所致。鐵甲堆積的北部被馬具的銅飾件所覆蓋。從人胄、馬胄與大量型式互異的甲片共存的情形判斷,這處鐵甲堆積當屬于《宋史》中所記載的“甲騎具裝”。
什么樣的人能擁有這樣一套裝備呢?顯然,尋常百姓是沒有這樣的雄厚財力的,有些貧窮者只能隨葬幾個陶罐了事。而5號墓出土的隨葬品頗多,除了這處鐵甲堆積和銅、鐵馬具之外,還有鐵劍、環首刀、矛、鏃等兵器和銅釜、甑、洗、鹿形飾、銅鎏金人面飾、金耳墜和銀釵等。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套只有當時的高級軍事首領才能擁有的比較完備并極具裝飾性的戰時防護裝備。
次日,在整理出墓內大部分隨葬品后,就只剩下這處鐵甲堆積了。興奮之余,我們意識到一個難題:體積如此“龐大”的鐵甲堆積,如何在整體起取時做到萬無一失呢?如果起取不當就會造成隱藏于發掘現場的信息丟失,給日后修復和復原工作帶來許多麻煩。因此,起取的方法必須慎之又慎,才有可能獲得更多遺留下來的歷史信息。專業書籍中介紹的“套箱法”可供參考,但我們還缺少經驗,操作起來并無成功把握。怎么辦?為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特意請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師李存信先生。10月27日,在他的幫助下,開始實施套箱法,將鐵甲堆積整體運回室內保存。套箱法的順利實施,為日后在室內作進一步的細致清理打下了良好基礎。

鐵甲修復情形圖中右一坐者為白榮金老先生,他是國內考古界少有的一位以古代鎧甲的復原研究見長的著名老專家。在其數十年的專業實踐中,曾歷經河北滿城漢墓、廣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獅子山漢墓等重要墓葬出土的鐵甲的整理研究,有著十分豐富的甲胄復原經驗。

以套箱法起取鐵甲堆積套箱法——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整體起取的一種方法。喇嘛洞鐵甲堆積的起取過程是:先在鐵甲堆積的四周開挖溝槽,切斷其與四周土層的聯系并嵌入事先準備好的“箱框”;在此基礎上進行“釜底抽薪”,即在掏空鐵甲堆積下面土層的同時漸次插入諸塊托板;然后,再對鐵甲堆積的表面進行石膏加固、蓋板封護;最后,就地取材,用木樁支成三腳架對加固后的套箱進行整體起吊,移出墓外并運回室內保存。
迎難而上,模型展示重裝騎兵風采
如此眾多的甲片是怎樣聯綴在一起的?如何探明它的內部構造?它是怎樣在騎兵和戰馬身上組合披掛的?
面對著這箱曾深埋地下1500年左右的鐵甲堆積,其銹蝕嚴重且又支離破碎的外表給人一種漫無頭緒、無從下手的茫然之感。與以往出土的類似鐵甲相比,喇嘛洞鐵甲不僅銹殘程度更甚,而且甲片的數量更大、類別更多、結構也更為復雜,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復原的難度。如何再現中國北方古代騎兵的原始形態?歷史沒有給我們提供現成的參考和經驗,我們只有正視困難,迎難而上。2003年7月下旬,我們對這處存于套箱內的鐵甲堆積開始進行室內清理。著名文物修復專家白榮金老先生主持和指導此番整理和復原工作。在他的具體指導下,從起取堆積表面的散亂甲片開始,我們對這箱鐵甲進行了科學、系統的清理。

整理復原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思考和探索的過程,科學根據定位分區、確定范圍、分組編號、逐層提取的基本原則,工作流程和操作步驟如下:的復原工作容不得半點馬虎,清理、拍照、記錄、實驗……隨處都需要工作人員的智慧、經驗和技能上的支持。在現有的認識水平和技術條件下,如何盡可能地保證實證復原的科學性和推測復原的合理性,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時刻注意的重要問題。在以上流程中,除了一些程序化的操作之外,實證復原與推測復原的相互結合能夠保證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相。從最初的觀察與分析開始,到對疑難部位的初步辨識、推測和判斷,再到相關資料的查閱、類似研究個案的比較和借鑒以及復原方案的擬定等無不如此。


例如,如何確定同屬于一個層面上的諸多甲片為甲騎具裝中某一部位上的甲片呢?在被壓于馬身甲片之下的鐵甲堆積中,有一處由15 個橫排、198 片甲片組成的鐵甲衣的局部,從其縱列形態、通長和其一端的寬度及另一端向兩側延展的形態來看,可以確認其為人身甲中背甲的殘存。在此基礎上,參照北朝時期有關甲衣定形象的資料,即可勾畫出此領身甲的復原展開輪廓,再將有關散亂甲片復位于上。由此可知,背甲的腰部以上由6 排甲片組成,每排由最上一排的21 片逐漸增至最末一排的25 片;背甲的腰部以下甲片共9 排,每排皆為65 片,總計為846 片。背甲的復原方案一定,與之相連的胸甲即可參此作相近復原。根據甲片上的綴連痕跡判斷,此副人身甲的甲片均用皮條以先橫后縱的方法綴合而成。復原后的人身甲屬于一種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組成的“兩當甲”。披掛時,可通過兩肩處的革帶和帶扣將胸甲和背甲聯接起來,右腋下的開口則用織帶系結。
再如,馬身甲是用于馬身左右兩側防護的主體部分,構成這一部分的甲片基本完整地保持著原來的組合排列狀態。根據由同類片型所組成的長寬相同并且對稱的兩個局部,可將其從其他甲片堆積中區分出來。從甲片橫向疊壓的狀態來看,也與右身甲片疊壓的一般規律相符,此是判斷馬身甲中的右身甲的根據。據此,以出土時保存最完整的第2 排甲片中的1~56號甲片為基準,其余1、3、4、5 排僅作少量補配并與第2 排甲片數量取齊,如此共由280 片甲片組成。右身甲的形狀和結構一經確定,左身甲亦可參此復原了。
在整理這堆鐵甲的過程中,有一些形狀比較特殊的甲片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它們共編有60 個號,分屬于6 個組。其中少數甲片之間雖然保持著原來的相對位置,但多數甲片已斷殘且分布散亂。因此,在其用途一時難以判明、復原又尚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著實令人困惑了一番。在苦苦揣度及求索中,一處墓葬壁畫讓這一難題迎刃而解。這座墓發現于河北磁縣灣漳境內,其年代為北朝晚期(6 世紀中葉)。在該墓內的壁畫上,一個身著魚鱗甲武士的衣領處的甲片竟與喇嘛洞的這些特殊甲片很相似!這一偶然發現似撥云見日,為判明這些可疑甲片應是人頸甲的甲片提供了重要借鑒。復原后的人頸甲狀似現今衣服的“立領”,它由60片甲片組成,按左右對稱、自前而后的疊壓順序圍圈成一個環形,上下緣以皮革包裹。

這樣,在反復觀察、比較和分析的基礎上,以實證復原為主、推測復原為輔,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我們終于制作復原出國內第一套甲騎具裝紙板模型。根據統計,除了先行復原的人胄和馬胄之外,此套甲騎具裝現存甲片共計3156 片(另有一些殘碎片未予統計)。如果按每片平均重約16克計算,則這套鐵制甲騎具裝原來重量可達50 公斤之多,如此沉重的“鐵甲”為脆弱的肉體構筑了一道堅實的“城墻”。
甲騎具裝復原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這套紙型標本不僅再現了東晉十六國時期重裝騎兵裝備的原始形態,而且還為研究東亞地區馬具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
過去,對這種流行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重裝騎兵裝備,只能從史書記載和古代壁畫、陶俑資料中得知一些片段。這類鐵甲雖早在1965年秋發掘的北票馮素弗墓(北燕,5 世紀前期)、1988年夏發掘的朝陽十二臺鄉磚場1號墓(前燕,4 世紀中葉)也曾有發現,但一直未能對其進行整體復原。喇嘛洞鐵甲的發現和復原則彌補了這一缺憾。喇嘛洞甲騎具裝的復原對中國古代軍事史、甲胄工藝史以及三燕時期馬具文化的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證意義。
這套人甲和馬甲的紙型標本是以喇嘛洞5號墓內甲片排列的初始狀態、聯綴殘跡和不同層面上的甲片分布的最初形狀為依據,再參考其他相關考古資料初步復原出的,系國內第一套完整的甲騎具裝實體原大模型。從這套模型上可以看到,人甲共由頭盔、頸甲、披膊、身甲和腿裙五部分組成;馬甲則由馬胄、頸甲、胸甲、身甲、鞧甲和搭后甲六部分組成。在喇嘛洞5號墓中,它與鐵環首刀、長劍、長矛和箭鏃隨葬一起,向我們展示出一套近乎完備的攻防武備系統,這在以往的類似發現中是不曾見到的。
在古代甲胄制作工藝史的研究價值方面,喇嘛洞甲騎具裝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如人胄和馬胄的鉚合結構以及馬胄上的面罩和護頰板之間的活銷聯接等,尚屬于一種少見的工藝方法。再如,用于披膊上的那種以固定式編綴技法形成的板塊結構、用于人身“兩當甲”和腿裙上以活動式編綴技法形成的伸縮結構等,均屬于以小型甲片——魚鱗甲為主體的中國古代甲胄系統所特有的傳統工藝,而其中的皮條編綴和皮革包邊的技法則又帶有鮮明的騎馬民族文化色彩。又如,從用于鐵甲披掛聯接的主要部件——帶扣來看,其形制已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以適應較為復雜的防護裝備的披掛需求。所有這些都表明,甲騎具裝的制作工藝和造型結構早在3 世紀中葉即已趨于完備。由此我們不難想見,在十六國時期諸強紛爭的歷史舞臺上,曾經上演過的又該是怎樣的一幕幕重裝騎兵揮刀執槊、列陣相搏的壯觀戰爭場面呢!
從中國歷史來看,作為一種流行于十六國時期北方地區的重要軍事防護裝備,甲騎具裝顯然是騎馬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遺物。這次復原為考察這一時期北方地區重裝騎兵的防護裝備提供了一套完整、直觀的實體資料。從整個古代東亞地區來看,甲騎具裝在遼西地區的盛行,推動和促進了與之密切相關的鞍、鐙、銜和帶扣等銅鐵馬具文化的東傳。通過這種傳播,遼西地區的馬具文化首先對高句麗王朝,繼而對三國時期的朝鮮和古墳時代的日本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古代的遺存在偶然被發現后向我們講述著那段歷史的故事,但“考古學家面對的只是古代遺存的冰山一角,而古代的物質性遺存又只是古代社會與文化的構成部分”。不僅僅是考古學者,我們每個公眾都應該積極善待和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這是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