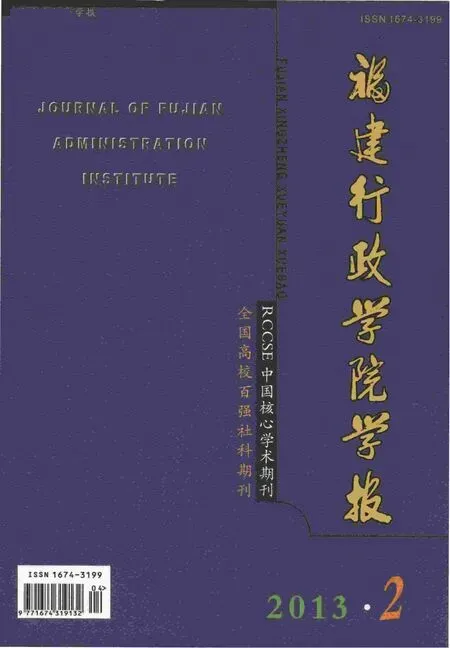性別分工、自我定位與農民工的城市適應
黃翠萍
(福建江夏學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350108)
一、選題緣由與相關研究
從流動模式上看,農民流動已逐漸從早期的個體流動轉向夫妻共同流動,舉家進城的農民工家庭數量越來越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5億人,其中舉家外出農民工3279萬人。[1]
農民工舉家進城,首先面臨的是對陌生城市的社會適應問題。學界已有不少關于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從代際角度對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進行比較。研究發現,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適應水平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水平不如第一代[2];李培林等從經濟、社會、心理和身份等四個維度對新老農民工的城市適應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社會融入狀況上不存在根本差異。[3]二是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最早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的王春光從社會認同的角度展開研究,他認為,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這種制度性身份的認同在減弱;但新生代農民工尚未建立起對城市社區歸屬意識。[4]在最近的研究中,王春光開始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一是政策的調整跟不上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需求;二是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城市化的能力與他們城市化向往之間的差距;三是地方政府城市化措施落后于中央城市化的政策。[5]也有研究從實踐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討,這方面的探討關注農民工適應城市的實踐及其邏輯。[6]此外,研究農民工城市適應的視角還有現代性視角[7-9]、社會資本視角[10]、社會化視角[11]等。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已有研究少有從性別分工和農民工自我定位的角度考察他們的城市適應問題。事實上,農民工的自我定位以及農民工夫妻之間的性別分工會影響他們對城市的適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文化本位為立場,從農民工自身的角度考察他們對城市的適應。為了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筆者于2008~2011年期間在福建、江西等地對40多個農民工進行調查。采用滾雪球法即通過外出務工或經商的親屬和老鄉介紹找到調查對象。為避免調查對象的同質性,筆者調查了不同職業的農民工,如建筑工、制造業工人、散工、個體戶、業務員等等。調查對象包括男性農民工和女性農民工。采取開放式的訪談方法收集資料,圍繞研究問題進行深度訪談。個案訪談時間均超過一個小時,并對訪談進行錄音和文字整理。同時,本研究采用性別分工和自我定位視角考察農民工在城市的經濟適應、心理適應以及社會適應。
三、研究結果
(一)農民工夫妻通過合理的性別分工能動地適應城市生活
作為整體的農民工家庭與個體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有相似之處,也有差異。相似性表現在,無論是家庭和個體在適應城市過程中,都必須首先從經濟層面適應城市,其次是社會層面的適應,最后是心理層面;其不同之處在于,個體農民工只需解決單個人的適應問題,而家庭涉及多個成員,因而需要解決多人的適應問題。調查發現,農民工家庭在適應城市的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形成了不同的性別分工模式。第一種分工模式為“男主女從”模式;第二種為“男女不分主次”模式。
1.“男主女從”模式。在所調查個案中,從農民工從事的職業來看,“男主女從”模式即男主外女主內,從所調查的農民工職業和工種來看,進一步分為男的做生意女的做家務、男的做技術工女的打散工兩種類型。丈夫做生意,而妻子做家務,之所以形成這種性別分工模式主要是因為丈夫的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妻子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為了照顧做生意的丈夫,妻子的主要職責是做好家務。調查中,筆者發現,妻子們在做好家務之余會充分利用剩余時間從事一些工作以補貼家庭。例如個案1中的劉女士在外出前長期在鎮上開縫紉店,掌握了縫紉技術,在跟隨丈夫外出后除了把家庭打理好之外還在附近一家工廠打零工。2008年筆者在東莞對劉女士與其丈夫馬先生進行了調查。調查得知2004年具有高中文化的馬先生出來跑業務,2005年下半年馬先生叫妻子出來,夫妻租住一套三室一廳的套房。據筆者觀察,套房收拾得很干凈,很有家的感覺。談起夫妻之間的分工,馬先生回答說:“家里的事情基本是她打理,業務上的事情我自己理。”顯然,馬先生與妻子之間的分工是傳統的社會性別分工,表現為“男主外、女主內”。問及夫妻之間分工的依據,他說:“根據個人的(能力),怎么說呢,反正長期以來就是這樣。”
在訪談中,劉女士告訴筆者,2005年下半年她過來后并沒有一直待在租來的家里,而是出去找事情做。她說:“我要做家務,別的事情也有做,從老家出來到這里就開始去找事情做了,去服裝廠打零工。有時候一個月能掙一千多。多少也能幫家里減輕點負擔吧,能做多少算多少。”
馬先生夫婦自從外出后家庭經濟狀況明顯改善,這表現在馬先生買了一輛二十幾萬的轎車,此外,還在廈門買了房子。
2.“不分主次”模式。“不分主次”模式主要指分工模式中丈夫與妻子做的事情沒有明顯差異。從所調查的職業來看,主要包括農民工夫妻共同開店和共同進廠打工兩種類型。
個案2:2006年之前羅先生一個人出門打工,之后他不再為別人做工而是自己開店。2006年他與妻子嚴女士在縣城開快餐店一年,2007年夏天開始在廈門開飲食店。
問及來廈門開店的原因,他說:“在朋友那里玩的時候講起來,最主要的是前年在城里沒法做下去了。”嚴女士則是不想再種田了,也不想給別人打工,對此她說:“過完年不想在家里種田了,想出來打工,我會做的他不會做,他會做的我不會做,問題就變成打工也不是一個好辦法。總之有這樣一個想法:打工永遠是打工,不想一直打工。如果自己有本錢,做點小小的生意也覺得比打工更有味道。打工畢竟要受人管。”
問及開店的決定是如何做出的,嚴女士表示是夫妻共同做的決定:“兩個人做好了決定,事先打聽好了。我去跟別人學炒菜,他則去找店面。他找到店面我學到技術就開始開店。”
談到夫妻的分工,嚴女士說:“講在店里做事情,兩個人平做。但是要搞什么關系,打比方要辦理什么證明,如衛生許可證或工商證明,就要由他決定。因為我一字不識,不曉得如何辦理。”
當問到外出后家庭經濟是否有改善時?他笑著說:“肯定要有的,比以前要好,現在能拿出一萬八千塊。以前跟人家借一千快都難,甚至貸款都要托人,那種日子過去了。現在已經幾年沒貸款了,已經幾年沒跟政府打交道了。”據筆者了解,羅先生夫婦通過幾年的開店在家里蓋了一棟三層的小洋樓。
除此之外,還有部分調查對象夫妻共同進廠打工,他們除了上班,彼此都會根據具體情境來決定分工,共同為家庭做貢獻以便更好地從經濟層面融入城市。
上述個案分析表明,農民工夫妻通過分工及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在經濟層面能動地適應城市。應該指出的是,農民工的適應能力是非常強的,無論到哪里,他們都能找到工作,問題在于,他們的工作是不穩定的,收入也是不穩定的。雖然他們能夠在經濟上自立,但這種自立也是暫時的。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搞裝修的農民工有工作的時候,每天收入能夠達到兩三百元,但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收入來源。因此,從經濟層面來看,農民工的這種適應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
(二)農民工的自我定位與心理適應
已有研究表明,農民工對城市的適應更多體現在經濟方面。通過對農民工的深入調查,筆者發現,受制度、市場和家庭的影響,農民工雖然能夠在城市找到工作,能夠從經濟方面適應城市,但心理上他們依舊保持對家庭的高度認同,以及對城市社會的低度認同。本研究表明,農民工對城市的心理適應明顯地受到他們對自己定位的影響,農民工對自己的不同定位會影響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認同。
1.農民工在身份上依舊認為自己是農村人而不是城里人。盡管農民工在城市已經工作生活多年,但當問及你覺得自己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時,絕大多數農民工依舊認為自己是農村人,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外地人,在地位上低于城里人。
一位做油漆工的李先生與老婆孩子一家四口租住在套房里,在龍巖市已經工作生活多年,但他依舊認為自己是農村人,對此他說:“本來就是農村人,這沒辦法改變,農村人就是農村人。”
另一位在龍巖開油漆店的林先生夫婦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說:“還是農村人,還是山區人”。
在農民工看來,在農村與城市之間有一堵無形的墻。雖然他們能夠通過就業和流動突破空間上的障礙,但對于大多數的農民工而言,他們的突破很可能停留在城市打工,無法更進一步,即他們無法突破制度的障礙。這種制度的障礙使他們感覺身份難以改變。正因為身份難以改變,使他們處處感覺自己低城里人一等。
一位同樣來自江西贛州的擁有多年外出經歷的油漆工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說,一家人租住套房,雖然也有家的感覺,但他覺得跟人家(指城里人)相比,在這邊再怎么住下去,永遠低人家一等。這種感覺是他在長期的務工過程中體悟到的,對此他說,“自己出門在外看多了,就會想為什么人家的能力跟自己的能力相比,人家會比我們好很多,在外面做工會有錢買房子。就算買了房跟本地人對比也會矮人家一等。在外面說話十句話不如本地人一句。還有小孩讀書,房子買下來,戶口遷到這邊來,讀書都低人一等,永遠比人家矮。”
2.農民工在心理上依舊歸屬于農村,難以建立對城市的歸屬感。正因為農民工難以從心理上融入城市,他們感覺自己是城市的過客,是城市的邊緣人。城市政府以及市民對他們的排斥加強了他們對家鄉的認同。訪談過程中,諸如“家里是根據地”、“家是避風的港灣”、“老家畢竟是老家”、“老家才是真正的家”、“我們的根在老家”等話語不斷重現。
許多訪談對象表示,如果打工掙了錢,要蓋房子,首選家鄉。當問及是否考慮過在城市買房時,一位與丈夫同在工廠打工的彭女士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她說,“現在的想法是在這里上班,如果有這個能力,在老家蓋棟比較像樣的房子。幻想過在外頭有房子,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空想每個人都會有。因為我們夫婦都打工,城市房價很高,自己沒有能力買房子。想把房子建在老家,這樣比較實在,畢竟自己沒工作。”
另一位做泥水裝修的江先生也表示,有錢了,買房會回到家鄉買。問及緣由,他說:“打工這種體力活到了一定年齡干不動了,到時候開支收入方面要考慮一下。那個時候,就要考慮退回老家,結束打工生涯了。”
農民工之所以會首選在家鄉蓋房,原因之一是他們的收入不高,但城市的房價卻很高,這使得即使能夠掙到購房首付的錢,他們也難以負擔每個月的按揭貸款。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城市生活,農民工缺乏社會保障,首先是住房缺乏保障,城市住房供應體系從來沒有將農民工納入進去。其次是日常生活缺乏保障。因為農民工的身份是農民,戶籍身份使得他們難以像城市居民那樣享有社會保障。相反,農民工在家鄉還有一份耕地,這份耕地雖然不能讓他們致富,但足以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
(三)農民工的自我定位與社會適應
農民工外出打工有兩種不同的邏輯:一是外出務工賺取收入以維持農村家庭的體面生活,城市只是打工的地方,最終是要回到家鄉的;另一種是外出務工掙錢是為了脫離農村定居城市。農民工對自我的定位不僅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而且還影響他們對城市的社會適應。農民工的社會適應主要體現在社會關系層面和居住空間方面。
首先,從居住空間看,受收入因素影響,外出農民工主要通過租房和住單位宿舍等方式來解決居住問題。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工有的租住城中村的民房,有的租住城市邊緣的民房。他們居住的房子比較簡陋、空間狹小、人員擁擠、衛生條件差、安全性低。他們與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間上相對隔離,居住空間上的隔離影響了農民工與市民的交往。
因為收入不穩定,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很少能夠買得起商品房。一位農民工付了首付,但最終因為家庭經濟壓力太大還是把房子退了。談起此事,他無奈地說:“想買房子沒那么容易,壓力太大了,吃不消,按揭的,比如這套房子二十多萬,自己資金才七八萬,買下去后考慮到有小孩,萬一家庭有點什么事情,所以要留有預備金。我們主要是收入不穩定,不是每天都有,有接到活才有收入。房子按揭每個月都要還貸,如果這個月沒有活做就要向別人借錢,越欠越多,心理壓力太大。”
其次,從社會關系層面看,因為農民工多與老鄉居住在同一社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多與老鄉進行交往,交往對象局限于本群體內部,社會交往具有封閉性特征。有調查顯示,51.5%的農民工主要交往對象是老鄉,基于友緣、業緣的社會交往較少。[12]農民工與市民的交往更多是業務性的,他們與市民的關系更多是事務性關系,一旦業務結束這種關系便結束。
當談到社會交往時,一位做油漆裝修的農民工告訴筆者:“在這里朋友也不多,主要都是打工的,我們打工的交往的朋友都是打工的,像房東之類的交往比較少,房東好的我會多聯系幾次。”
有研究顯示,農民進入城市帶來職業及生活方式的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網絡的邊界,城市農民工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基礎仍然是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核心的初級關系。[13]雖然,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以親戚和老鄉為主,但我們注意到自我定位不同的打工者在建構城市適應所需的社會網絡方面還是有所差異。這表現在:如果外出務工者打工的目的是為了在城市定居,那么他們會主動與城市居民打交道,并積累和維系與城市居民的關系,從而拓展自己的社會網絡;而外出務工的目的僅僅是掙錢的農民工在拓展與市民的關系方面沒有那么積極,他們僅僅依靠原有的網絡關系。
四、結 論
以上是筆者從性別分工和自我定位角度分析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分析表明,農民工家庭在經濟層面上通過性別分工能動地適應城市;而心理層面上受限于制度的障礙以及城市社會的排斥,大多數農民工難以對城市形成歸屬感,與之相反,農民工對家鄉卻擁有深厚的情結,這種情結使他們將未來投向家鄉;從社會層面看,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不高,這表現在: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主,這種封閉性的社會網絡妨礙了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融合;此外,絕大多數農民工居住在城市的邊緣,在空間上與城市居民隔離開來,這也妨礙了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有學者指出,因為制度的不接納,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14]總之,本研究表明,除了受宏觀制度排斥、市民排斥、資本剝奪之外,農民工的自我定位也會影響其對城市的認同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建構。
[1]國家統 計 局.2011 年 我 國 農 民 工 調 查 監 測 報 告[EB/OL].(2012-04-27).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2]景曉芬,馬鳳鳴.代際差異視角下的農民工的城市適應[J].南方人口,2012(3):65-72.
[3]李培林,田豐.中國農民工社會融入的代際比較[J].社會,2012(5):1-24.
[4]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63-76.
[5]王春光.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及問題的社會學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6]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的發現[J].社會,2006(2):136-158.
[7]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1996(4):42-52.
[8]周曉虹.流動與城市體驗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J].社會學研究,1998(5):58-71.
[9]江立華.城市性與農民工的城市適應[J].社會科學研究,2003(4):92-96.
[10]曹子瑋.農民工的再建構社會網與網內資源流[J].社會學研究,2003(3):99-110.
[11]戴榮珍.論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再社會化[J].福建論壇,2003(8):30-33.
[12]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農民工市民化[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1:276.
[13]曹子瑋.農民工的再建構社會網與網內資源流[J].社會學研究,2003(3):99-110.
[14]李強.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半融入”與“不融入”[J].河北學刊,2011(5):1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