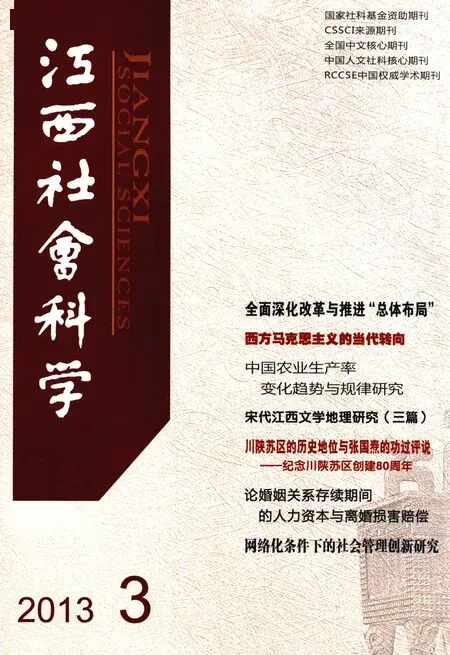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鄒東濤 付麗琴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近10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既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衍生品,同時也成為我國當前及今后發展的障礙,甚至有可能進一步誘發“中等收入陷阱”①。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一、中國是否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自2006年世界銀行首次提出東亞新興市場國家需要特別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后,作為剛步入中上等收入國家的中國②備受國內外關注,關于今后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論日益激烈。中國能否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考察。
第一,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從2008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凈出口額逐年下降 (見圖1),凈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從2008年的8.8%下降到2010年的3.98%。而在服務貿易市場上,2011年中國出口1821億美元,進口2370億美元,處于貿易逆差的位置。③中國出口萎縮既有源自國際方面的因素,如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的影響,也受到人口紅利減弱、土地成本上升等自身發展的制約,因而,未來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減弱。

圖1 2002-2011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
第二,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投資在 中所占比重過高 與2003—2011年美國、日本投資支出在GDP所占百分比相比,中國投資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過高,相當于日本的2倍,美國的3倍。
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1998—2003年中國政府發行了7000多億元國債,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西部開發、西氣東輸、青藏鐵略等重大項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抵御國際經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和實現“保8”的增長目標,國務院批準在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方面投資4萬億。叢明對1998—2003年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的研究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對于GDP增幅的直接貢獻率,在1.5~2個百分點之間④,此外政府投資還通過帶動私人投資、增加最終消費間接促進經濟增長。但對GDP的拉動作用在下降,1998年為1.5%,1999 年為 2%,2000 年為 1.7%,2001 年為 1.8%。另外,從政府支出對固定資產投資乘數來看,1998—2003年為1.83,而2009年1月到 2010年7月下降到1.52⑤。這些數據表明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第三,國內消費需求。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較低。自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巴西等國家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均高于70%,英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大多數年份高于80%,美國最終消費略低也仍高于60%,而中國自2006年以來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低于50%,相形之下消費需求明顯不足。
中國國內消費需求增速也在下降。自2009年以來,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從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1年的17.1%。從2012年1—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情況來看⑥,增速進一步下降。
對中國城鄉、城鎮、區域之間居民消費情況的比較發現,高收入家庭以發展型消費為主,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費為主。
“沒錢可花”、“有錢不敢花”、“錢少沒法花”、“有錢無處花”是中國面臨的四個消費問題。這四大消費問題是收入分配對消費需求影響的現實體現。影響中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很多,如物價、商業流通的發達程度等,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其消費水平的高低。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收入分配差距對消費需求有很大的影響。
二、從“中等收入陷阱”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影響
國內很多學者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時,通常用兩類國家來進行比較:一類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日本、新加坡、韓國。1973年日本人均GNI為3580美元,僅用8年時間人均GNI突破10000美元躋入高收入國家之列,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新加坡、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分別為12年(1977—1989年)、8年(1987—1995年)。另一類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別在1986年、1994年、1991年人均GNI達到3000美元后,至今人均GNI沒有突破10000美元,成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⑦。
值得關注的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和跨越國家在社會公平方面存在很大差異。1981—2010年間巴西的基尼系數均高于0.5,遠高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個別年份甚至高于0.6,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不公平問題嚴重。阿根廷自1986年以來,基尼系數始終大于0.4,⑧2003年最高,達到0.5471,近年來系數有所下降,但仍高于0.4,超過國際警戒線。1986年該國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窮人收入的16.63倍,2001年達到58倍,近年來這一數字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較為不公平。墨西哥的基尼系數大都高于0.45,2000 年達到 0.51,而后略有下降低于 0.5。1989 年該國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窮人收入的10.5倍,2000年達到27.7倍,近年來這一數字有所下降,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較為不公平。
相形之下,亞洲四小龍重視并較好地解決了社會公平問題,通過國內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發展戰略,基尼系數一直處于較低水平。日本的基尼系數在1981—1990年間均低于0.3。韓國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1971年為0.36,1993年時僅為0.316⑨。中國臺灣基尼系數一直低于0.3⑩,人均收入分配差距世界最小。
較低的基尼系數意味著社會各界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布比較均勻,而不是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擴大國內消費,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同時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基尼系數比較高,在0.4~0.64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大,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阿根廷在2001年的經濟危機期間先后更換了5位臨時總統,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與教訓表明:“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公平與效率“平衡”點不同,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階段,仍然用“低收入國家”階段以犧牲社會“公平”的發展尤其犧牲大多數居民的福祉為代價換取片面的經濟增長,提高“效率”,最終讓增長扭曲成為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反之,“公平”的社會環境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中等收入階層消費市場,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發展,推動經濟增長。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要繼續維持“效率”,唯有突出社會“公平”,建立社會收入公平分配的機制,構建“橄欖形”社會收入結構,從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包容性”增長,產生足夠的推力,強勁助推經濟跨越“陷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一國經濟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準“效率”和“公平”平衡點的“砝碼”。巴西等拉美國家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仍過度關注GDP增長,忽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廣大中低收入者不能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國內消費結構難以升級。雖然拉美國家消費占GDP的比重與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相差不大,但拉美國家因為貧富差距惡化,廣大低收入者、貧困人口以生存型消費為主,低消費結構進一步制約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步伐,經濟發展緩慢。只有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共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議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標,“努力實現兩個同步、著重提高兩個比重”的新思路: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為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創造條件,從而構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內生動力機制,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各國發展經驗來看,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在控制收入差距上都采取了全面系統的措施。實現國民收入合理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著重“提高兩個比重”。十八大報告針對收入分配領域中出現的新問題,結合新形勢,創造性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更公平”意味著合理分配,意味著繼續實施“提低、擴中、調高、打非、保困”政策,打破既得利益集團,打破壟斷,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等制度變革。
(一)繼續實施“提低、擴中、調高、打非、保困”政策
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調高、擴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從2003年開始,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大致遵循“提低、擴中、調高”的方案分層次推進。九年以來,政府在“提低”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如提高低保待遇、調高養老金水平、減免農民稅負,加大對教育、醫療的投入等;“擴中”與“調高”則涉及多方面利益,與政治體制改革亦密切相關,始終難有實質性突破。
十八大之后,新領導層延續“提低、擴中、調高、打非、保困”的改革思路。
“提低”。包括在中小企業中建立工資增長機制,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大力促進農民增收,消除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各種歧視性政策和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消除與主觀生產條件相聯系的身份制、等級制,通過“提低”讓一部分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中。
“擴中”。關鍵在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政府將通過加快推進城鎮化、鼓勵自主創業、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等措施,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擴大中產階層的比重。
“調高”。包括調控某些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研究制定國有企業工資總額改革辦法,完善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建立健全財產稅制度,考慮適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調控社會上某些群體的過高收入。
“打非”。就是取消或規范“灰色收入”。堅決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嚴厲查處走私販私、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非法活動;清理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等,繼續深入開展“小金庫”治理工作。嚴打侵吞資產、貪污賄賂等行為,避免收入再分配向一些特權部門、特殊利益集團和特定社會成員的傾斜。
“保困”。就是幫助困難群體,扶貧濟困促公平。加大政府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加大扶貧力度、提高扶貧標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健全就業幫扶、生活救助、醫療互助等幫扶制度,更好地解決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
(二)解決收入差距須打破三大既得利益集團
2004年國家發改委、人保部、財政部等部門共同啟動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并在數年間多次上報、修改。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經8年仍未出臺“難產”的原因,主要是在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牽涉到了各種利益的博弈,包括權貴利益群體、壟斷利益群體和資源利益群體。
一方面,這些特殊利益群體充分利用現有制度或政策空間通過攫取社會公共利益來放大自身利益,從而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現在:一些部門、行業通過行政壟斷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其中的成員將利潤轉化為個人收入和在職消費;一些政府部門或公職人員利用規則制定權或資源分配權進行權錢交易,獲得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一些群體通過尋租行賄、偷稅漏稅或走私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會財富。
另一方面,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為謀求自身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利益訴求渠道進一步謀求政策的傾斜,阻撓可能有損自身利益的改革措施,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在這種權力利益獲取和博弈過程中,強勢利益部門和一些富人群體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話語越來越多,而普通民眾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響力越來越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自然就變得雷聲大、雨點小。
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進度將成為各方關注中國改革整體進度的一個窗口。而要想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所作為,首先必須著力破解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政府部門必須在利益集團和其他社會階層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三)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中等收入者倍增
早在十六大報告就明確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
2011年以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再度出現。從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二五”規劃到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頻頻出現。在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專門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十八大報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強調“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多方面,關鍵還是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讓更多的低收入人群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一是縮小收入差距。縮小行業之間、各個階層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是擴大居民消費的重點和關鍵。要打破能源、通信、金融等行業壟斷,進一步使收入透明化;應大力發展現代化農業,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除了加快城鎮化步伐,更重要的是加快以農民土地權利保護為重點的財產權制度建設,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
二是改革財稅金融制度。減少中小企業稅負,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創造更加寬松的創業環境,鼓勵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使更多的人成為創業者。更期待的則是放開金融行業的壟斷,讓中小企業真正在陽光下快速發展。這既是提高低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徑,也是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手段。此外,還可以考慮對中等收入群體適當減稅。個稅政策改革除了提高起征點以外,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考慮適度降低各檔的稅率,考慮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
三是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車輛、土地、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讓財產使用權所獲得的利息、租金、專利收入等;財產營運所獲得的紅利收入、財產增值收益等。國外中等收入人群的財產多以住房、股票、基金、理財產品以及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
收入分配改革不應該只是頂層設計,而應該是國家與公眾、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協商互動的過程。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最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要有社會和廣大群眾的參與,不能高高在上,閉門造車。目前,許多部門、地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積極主動地進行了一些嘗試。比如,加大民生投入,改革公務用車、促進經濟轉型、完善福利保障等。今后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與首創精神相結合,一味等待頂層設計則可能錯過改革的良好時機。
注釋:
①2011年12月12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產業競爭力藍皮書》稱,按照2011年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經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正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人均收入難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驗。2012年,法國媒體稱中國很可能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正在走上馬來西亞發展道路。
②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8月公布的數據,人均國民總收入在3946~12195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偏上的國家。2009年中國人均GNI為3620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NI為4240美元,2011年中國人均GNI為4940美元,根據這一標準,中國自2010年起步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之列。
③數據源自《從十六大到十八大經濟社會發展系列報告之四》,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
④轉引自張信柱《積極財政政策研究——基于我國1998—2008年財政政策分析》(東北財經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
⑤數據源自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⑥《2012年消費品市場情況》,源自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2012年10月18日。
⑦數據源自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⑧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1986年以前阿根廷基尼系數相關數據缺失。
⑨曾國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現狀評價與調節政策選擇》(《經濟評論》2002年第5期)。
⑩權衡《從公平增長收入差距擴大的轉變——臺灣經驗與政策考察》(《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11期)。
[1]高杰,何平,張銳.“中等收入陷阱”理論述評[J].經濟學動態,2012,(3).
[2]趙培紅.國內“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進展及展望[J].當代經濟管理,2012,(6).
[3]周叔蓮.關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思索[J].中國領導科學,2012,(10).
[4]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未來10年的中國: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
[5]張飛,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比較[J].亞太經濟,2012,(1).
[6]孔涇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背景、成因舉證與中國對策[J].改革,2011,(10).
[7]劉鴻明.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視角的分析[J].現代經濟探討,2012,(4).
[8]毛強.“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發展道路——基于國際經驗教訓的視角[J].中國人口科學,2011,(1).
[9]金振宇.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及其對消費的影響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1.
[10]王敏.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2011.
[11]Indermit Gill, 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u Economics Growth.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7.
[12]Acemoglu Daron.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The Princetou University Press,2008.
[13]Davis,Deborah.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4]Kang Du-yong.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s Growth Driver Industries.KIET·e - Kiet Industrial& Economic Information, 2005.
[15]賈后明.論收入分配調整手段的適用性[J].經濟縱橫,2012,(5).
[16]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政策體系構建研究[J].企業經濟,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