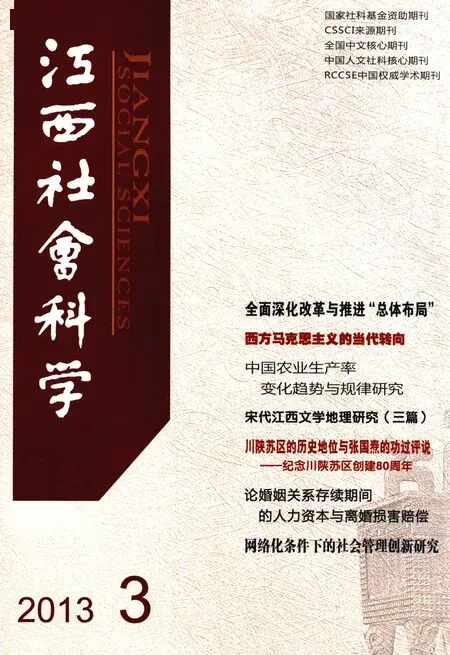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結(jié)構(gòu)分析
■夏漢寧 劉雙琴
“區(qū)區(qū)彼江西,其產(chǎn)多才賢”,在宋代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江西絕對是一顆璀璨的明珠。經(jīng)統(tǒng)計(jì),宋代江西有作品傳世的文學(xué)家就有1359人①。本文試以歷史人口學(xué)及定量分析的方法,對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性別結(jié)構(gòu)、身份結(jié)構(gòu)及年壽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統(tǒng)計(jì)與分析,以期借此進(jìn)一步了解宋代江西文學(xué)發(fā)展中所呈現(xiàn)出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學(xué)問題,重新詮釋和理解江西文學(xué)。
一、性別結(jié)構(gòu)
在兩宋有作品傳世的1359名江西文學(xué)家中,從性別來看,共有1349名男性作者,僅10名女性作者,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情況如下表所示:

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性別結(jié)構(gòu)及其創(chuàng)作簡表
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輝煌成就,主要是由男性文學(xué)家所創(chuàng)造的,女性文學(xué)家尤其是杰出的女性文學(xué)家寥寥無幾,盡管出現(xiàn)過蔡琰、李清照那樣在有著獨(dú)立人格、有才情有品格的優(yōu)秀女性文學(xué)家,但從整體上來說,女性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還僅僅是作為男性文學(xué)的陪襯和附庸而存在。就宋代的女性文學(xué)來看,我們對蘇者聰《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宋代部分)、葛曉音《中國歷代女子詩選》以及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宋代部分)進(jìn)行考察,除去重復(fù)者,約有女性文學(xué)家138人。此外,《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共收錄女性文學(xué)家近300多人。在這近300名女性文學(xué)家中,籍貫可考者有約110人,其中江西僅10人,分別為:王文淑(王安石妹)、王氏(王安石長女)、王氏(王安國女)、王氏(王女)、李氏(李常之姊)、何師韞(抱甕先生天裴女)、陳梅莊(陳仲微女)、楊氏、來氏、楚娘。
從數(shù)量上來看,江西女性文學(xué)家不及歌舞娛樂文化盛行的浙江(約26人)以及具有深厚傳統(tǒng)文化的中原地區(qū)河南(約15人),人數(shù)與四川、江蘇基本持平;從質(zhì)量來看,宋代江西缺少像李清照、魏夫人、朱淑真這樣蜚聲文壇的著名文學(xué)家。可見,江西的女性文學(xué)在宋代仍處于比較薄弱的地位。然而,在宋代江西女性文學(xué)的發(fā)展中,有一個(gè)很顯著的特點(diǎn),即“家族現(xiàn)象”。宋代江西的女性文學(xué)家絕大多數(shù)與文學(xué)家族、文學(xué)名家密切相關(guān)。在這10名女性文學(xué)家中,就有4位屬于王安石家族;此外,李氏與李常、陳梅莊與陳仲微、何詩韞與抱甕先生天裴之間也都有深厚的家族血緣關(guān)系。宋代女性文學(xué)家的家族現(xiàn)象,宋人亦有覺察,如魏泰《隱居詩話》就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能詩者最眾。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fēng)不入小窗紗,秋意應(yīng)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游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fēng)”。皆脫灑可喜之句也。[1](前集卷六十)
由于經(jīng)濟(jì)的繁榮、文化的發(fā)展和社會(huì)的相對穩(wěn)定,宋代逐漸出現(xiàn)許多文學(xué)家族。其中,以一男性文學(xué)家為首,提倡指導(dǎo),而后形成該家庭中一代或數(shù)代女性文學(xué)群體的現(xiàn)象,在這一時(shí)期也有所體現(xiàn)。家族中居于首要地位的男性文學(xué)家女性觀的開明,促進(jìn)了女性文學(xué)家的成長與創(chuàng)作,如王安石就非常重視女性的文學(xué)修養(yǎng),甚至視女性的文學(xué)才能為魅力。在王安石文集中就能看到王氏兄妹、父女的諸多酬唱之作。如與二妹的詩文《寄朱氏妹》、《寄虔州江陰二妹》和《游賞心亭寄虔州女弟》,與三妹的詩文唱和《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與長女的詩文《寄吳氏女子》、《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寄吳氏女子》、《次韻吳氏女子韻二首》,與小女的詩文《寄蔡氏女子二首》等。正是這種對女子才情的認(rèn)同,王家多位女性在文學(xué)史上留下了她們的才名。
王安石對女性才能的認(rèn)同,與王、吳兩個(gè)家庭間的聯(lián)姻有深厚的淵源。王育濟(jì)就曾指出:“在臨川王氏走向興盛的過程中,與烏石崗吳家的聯(lián)姻是其中至關(guān)重要的一環(huán)。出身于詩書世家的吳夫人的到來,使當(dāng)時(shí)文化積淀尚薄的臨川王氏受益匪淺”,吳夫人“帶著明顯的文化優(yōu)勢嫁到王家”,“此前王家所有女眷都沒有知書好學(xué)的記載,自從吳夫人入嫁后,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吳、王兩家婦女,多知書能詩。’‘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2]在宋代文集中就可以看到大量關(guān)于吳家先人的記載:王安石的外祖母黃氏“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dǎo)處士,信厚聞?dòng)卩l(xiāng)”(王安石《外祖母黃夫人墓表》);母親吳氏“好學(xué)強(qiáng)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兼喜陰陽數(shù)術(shù)學(xué)”(曾鞏《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志銘》);妻祖母(即吳敏妻)“于財(cái)無所蓄,于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屑,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shí),當(dāng)世游談學(xué)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王安石《河?xùn)|縣太君曾氏墓志銘》)。王安石妻吳氏,出身書香之家,亦工文學(xué),嘗有小詞約諸親游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fēng)”之句,被宋人魏泰稱道“脫灑可喜”(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正是由于與吳氏家族的聯(lián)姻,臨川王氏的整體文化水平被大大提高,王氏家族女性的文學(xué)才能也得到最大的發(fā)掘與尊重。
此外,從王氏家族女性文學(xué)家的婚姻歸宿來看,與之聯(lián)姻的家族非富即貴,有著良好的文學(xué)素養(yǎng)。王安石大妹王文淑嫁給張奎,他是“尚書比部郎中、贈(zèng)衛(wèi)尉少卿”;王安石二妹嫁朱明之,他“仕至大理少卿”;王安石三妹嫁給沈季長,他是治平二年進(jìn)士,曾官至少府監(jiān);王安石長女嫁吳安持,乃吳充之子,吳充官至宰相;王安石二女兒嫁給蔡京之弟蔡卞,蔡卞熙寧三年進(jìn)士,曾兩度為相,是北宋末年政壇的風(fēng)云人物。正是由于家族的良好教育與文學(xué)氛圍以及文化家族彼此之間的聯(lián)姻,為宋代江西女性文學(xué)家的出現(xiàn)和女性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
二、身份結(jié)構(gòu)
首先,從文學(xué)家的登科情況來看,兩宋江西文學(xué)家共有進(jìn)士約679人,其及第年齡及各體文學(xué)作品量的創(chuàng)作情況如下表所示:

宋代江西進(jìn)士文學(xué)家及第年齡結(jié)構(gòu)及創(chuàng)作情況統(tǒng)計(jì)表
在679名進(jìn)士中,及第年齡可考者有206人,從以上宋代江西進(jìn)士文學(xué)家相關(guān)信息表可知,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中進(jìn)士的平均及第年齡約為30.58歲,與宋代狀元的年齡結(jié)構(gòu)(31.42歲)[3](P184)、宋詞作者中進(jìn)士的及第年齡結(jié)構(gòu) (30.2歲)[4]以及宋詩作者中進(jìn)士的及第年齡結(jié)構(gòu)(29.37歲)[5]基本一致。20-29歲這個(gè)年齡段及第的進(jìn)士人數(shù)最多,共96人,同時(shí)他們也是創(chuàng)作力最旺盛的一支隊(duì)伍,人均作品量最高,為417篇(首)/人。15-19歲之間及第的進(jìn)士,也極具創(chuàng)作活力,人均創(chuàng)作量達(dá)到394篇(首)/人。
從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整體力量來看,進(jìn)士絕對是一支重要的創(chuàng)作隊(duì)伍。從不同文體的創(chuàng)作來看,宋代江西進(jìn)士以占總?cè)藬?shù)49.96%的人數(shù),創(chuàng)作了占總量67.89%的作品量。在各體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中,進(jìn)士的詩、文創(chuàng)作量均超過宋代江西詩、文作品總量的一半。進(jìn)士文學(xué)家的人均創(chuàng)作量高達(dá)94篇(首)/人,遠(yuǎn)高于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整體人均創(chuàng)作量69篇(首)/人。從文集情況來看,進(jìn)士也是江西文學(xué)的重要生力軍,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中擁有文集的進(jìn)士占了擁有文集人數(shù)總量的58.99%。在宋代學(xué)優(yōu)登仕、從科舉正途躋身官僚體系的人才選拔、任用制度下,進(jìn)士無疑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的地位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一方面,他們的創(chuàng)作方式、文學(xué)品味符合了統(tǒng)治者的需求,備受統(tǒng)治者青睞,因此進(jìn)一步激發(fā)了其創(chuàng)作熱情;另一方面,由于進(jìn)士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其作品保存下來的可能性大大高于非進(jìn)士出身的普通作者。
經(jīng)過考察還發(fā)現(xiàn),在各體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中,進(jìn)士在“文”這一領(lǐng)域的創(chuàng)作極為活躍,在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所有文中,進(jìn)士的創(chuàng)作量就達(dá)到了82.96%,其中包括論、書、子、奏狀、奏疏、序、記、雜著、碑銘、墓名銘、墓表、祭文等多個(gè)文種。這一方面與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之后科舉重視經(jīng)義、論、策的制度緊密相關(guān),與進(jìn)士躋身仕途之后頻繁的社交應(yīng)酬、上疏論事有密切關(guān)系,同時(shí)也與古文運(yùn)動(dòng)的興起與發(fā)展不無關(guān)系。宋初太宗即位以后,廣開科場,以詩賦取人,這種政策的后果是大量南方士人以擅長詩賦入仕,以至于馮拯有“江浙士人專業(yè)詩賦以取科第”[6] (卷六十八,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癸未條,P591)之不平。李覯(1009-1059)在《葉學(xué)士書》中也曾引少時(shí)所聽“鄉(xiāng)先生”之言說:“當(dāng)今取人,一出于辭賦,曰策曰論,姑以備數(shù)。”可見,真宗之前,詩賦在進(jìn)士科考試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那時(shí)雖然也規(guī)定考策論,但形同虛設(shè)。真宗即位初,以策論為考試內(nèi)容的制科逐漸受到重視。天禧元年,右正言魯宗道言:“進(jìn)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真宗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jìn)士兼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jīng)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之。”[6](卷九十,天禧元年九月癸亥條,P803)仁宗時(shí),進(jìn)一步提高策論在進(jìn)士錄取中的分量,如葉清臣“天圣二年舉進(jìn)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jìn)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7](卷二百九十五《葉清臣傳》,P9849)。天圣五年(1027),仁宗詔貢院:“將來考試進(jìn)士,不得只于詩賦進(jìn)退等第,今后參考策論,以定優(yōu)劣。”②[8](P192)統(tǒng)治者在科舉制度上的政策與措施,直接影響著進(jìn)士的價(jià)值取向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這個(gè)過程中,詩賦所代表的南方文化逐漸受到策論所代表的北方文化的強(qiáng)烈沖擊。我們從宋代江西進(jìn)士各體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量可以推測,走在文學(xué)、文化前沿的進(jìn)士在古文復(fù)興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在文的創(chuàng)作量方面占了絕對優(yōu)勢,而且涌現(xiàn)出一批古文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文學(xué)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江西即有三家,分別是歐陽修、曾鞏、王安石。
其次,在宋代文學(xué)中,還有一群身份比較特殊的文學(xué)家,即出家人,包括僧人、道士,尤其是僧人,在宋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我們對宋代僧人文學(xué)家作了初步的統(tǒng)計(jì),這一時(shí)期共有僧人文學(xué)家約1068人。籍貫可考的約501名僧人文學(xué)家地理分布大致如下:

宋代江西進(jìn)士文學(xué)家作品量統(tǒng)計(jì)表
籍貫不可考而寓居地可考的約173名僧人文學(xué)家的地理分布大致如下:
若將籍貫可考及寓居地可考的僧人文學(xué)家加起來一起算,則浙江排名第一,為219人;福建第二,為91人;四川第三,為74人;江西第四,為70人;江蘇與湖南并列第五,為46人。從整體排名情況來看,宋代江西僧人文學(xué)家的人數(shù)比較靠前。我們將宋代江西僧人、道士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大致如下:

宋代僧人文學(xué)家地理分布表

宋代江西僧道文學(xué)家作品量統(tǒng)計(jì)表
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中的出家人,雖然其創(chuàng)作總量并不多,但從人均創(chuàng)作量91篇(首)/人來看,遠(yuǎn)高于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整體人均創(chuàng)作量。其中,僧人人均創(chuàng)作量達(dá)到122篇 (首)/人,可見宋代僧人文學(xué)家群體創(chuàng)作力的強(qiáng)盛。從各體文學(xué)所占的比例來看,僧人文學(xué)家詩的創(chuàng)作量最高,為4328首;文的創(chuàng)作量次之,為1000篇;詞的創(chuàng)作量最少,僅22首。我們知道,自唐代開始,“詩僧”一詞逐漸成為一個(gè)特定稱謂③。降至宋代,雖然這些出家之人的創(chuàng)作及聲名整體上不及唐代詩僧,但從參與創(chuàng)作的詩僧人數(shù)及其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上,仍然可以窺見宋代僧人文學(xué)尤其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繁盛。影響宋代江西僧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gè)方面:第一,從宋代江西文化來看,這一時(shí)期得到了迅猛的發(fā)展,江西的文學(xué)之盛,人才輩出,為僧人的學(xué)習(xí)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這也勢必影響到僧人學(xué)習(xí)文學(xué)的熱情;第二,從宋代寺院的分布來看,“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9](卷二),江西寺觀雖不如兩浙、閩中,但就全國范圍來說,數(shù)量并不少,有的寺廟更是聞名遐邇,如廬山東林寺,這也為僧人的居住與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第三,從詩詞文三種不同的文體來看,僧人對“詩”這種文體的特殊偏好與禪僧作詩偈的傳統(tǒng)密切相關(guān),詩僧中禪宗人數(shù)為最,作詩幾乎可以說是禪僧專利。從不同文體的功能來看,詩主言志,詞主抒情,文主論事,只有詩這種文體最能切合僧人的出家身份。
第三,兩宋時(shí)期尤其是宋室南遷后,一些有著特殊身份的文學(xué)家也登上了江西文壇,這就是宗室文學(xué)家。據(jù)考察,宋代宗室文學(xué)家共有約412人,在籍貫可知的88人中,江西占20人,僅次于浙江,其中北宋1人,南宋19人,有文集者共8人。從作品量來看,宋代江西宗室文學(xué)家約有1435篇(首)作品傳世,人均創(chuàng)作量為72篇(首)/人,略高于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人均創(chuàng)作量。宗室文學(xué)家中不乏趙長卿、趙彥端、趙師俠這樣的著名詞人以及趙汝這樣的優(yōu)秀詩人,他們與其他社會(huì)集團(tuán)的聯(lián)系使得精英和平民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和多元化,并對宋代江西文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重要推動(dòng)作用。如趙汝,為江湖詩派重要詩人,其古體詩“氣雄筆健,遠(yuǎn)追太白,近接坡公”(《宋百家詩存》卷一三),近體詩暢快流利,“造境奇而命意新,與四靈分壇樹幟,直欲更出一頭地”(《宋百家詩存》卷二十五),一方面對江湖派短于古體的不足有所完善,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江湖派詩歌的藝術(shù)內(nèi)涵。
三、年壽結(jié)構(gòu)
作為人口自然變動(dòng)的基本要素之一和人口更替的方式,人口的死亡年齡、年壽結(jié)構(gòu)與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醫(yī)療條件等密切相關(guān)。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都活了多少歲?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量與年壽高低有無關(guān)系?為探尋這些問題,我們對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的年壽結(jié)構(gòu)及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情況進(jìn)行了對比分析,如下表所示:

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年壽結(jié)構(gòu)及作品量統(tǒng)計(jì)表
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中年壽可考者共有351人,其平均壽命約為64.3歲,高于宋代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齡56.7。[10](P305)其中,年齡最小的為臨川晏潁,年僅17歲;年歲最大的為大庾孫璉,壽過百歲。在年壽可考的351名文學(xué)家中,年壽在60-69歲這一段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最多,其次是年壽在70-79歲者,再次是年壽在50-59歲者。從作品總量來看,60-69、70-79、50-59歲這三個(gè)年壽段分別排第一、第二、第三名,同時(shí),這三個(gè)年壽段有文集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也分別排第一、第二、第三,與這三個(gè)年壽段從事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成正比;處于40-49、80-89歲這兩個(gè)年壽階段的文學(xué)家其作品量分別排第五、第四名,與這兩個(gè)年壽段從事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不成正比,但從文集情況來看,這兩個(gè)年壽段有文集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分別排第四、第五名,總體來說從事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與其創(chuàng)作總量比較平衡;年壽在10-39歲之間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相對很少,其創(chuàng)作總量相對也比較少;年壽在90-99歲之間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也不多,然其創(chuàng)作總量相對比較高,其人均創(chuàng)作量最高;年壽在100歲以上的文學(xué)家僅1人,其創(chuàng)作總量僅2首。在年壽可考的351名江西文學(xué)家中,進(jìn)士就有212人,我們對這200余名進(jìn)士的年壽及創(chuàng)作量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同樣發(fā)現(xiàn):70-79、60-69歲這兩個(gè)年壽段的進(jìn)士無論是作品總量,還是有文集的人數(shù)都排前兩名,同時(shí)其人均作品量均超過300篇(首)/人,分別排第二、第三;50-59、40-49歲這兩個(gè)年壽段的進(jìn)士其作品總量分別排第四、第三,擁有文集的人數(shù)分別排第三、第四;80-89歲年壽段的進(jìn)士其作品總量及有文集的人數(shù)均排第五;90-99歲年壽段的進(jìn)士其作品總量雖不多,然人均作品量達(dá)到519篇(首)/人,遠(yuǎn)遠(yuǎn)高出其他年壽段的進(jìn)士。
從這些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幾個(gè)規(guī)律:第一,一般來說,不同的年壽段,人數(shù)越多,由于人口基數(shù)大,創(chuàng)作的作品量越多,從上表可知,不同年壽段的作品總量基本能與該年壽段從事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家人數(shù)成正比;第二,年壽越長,由于創(chuàng)作時(shí)間相對比較長,其創(chuàng)作力越強(qiáng),作品總量也越多,由上表可見,年壽在50歲以上的文學(xué)家其人均創(chuàng)作量明顯高于年壽不及50者;第三,文學(xué)家的作品總量雖與從事創(chuàng)作的人數(shù)以及文學(xué)家的年壽高低有密切的關(guān)系,但并不絕對,例如,處于80-89歲年壽段的文學(xué)家,其人均量反不如處于60-79歲年壽段的文學(xué)家;處于40-49歲年壽段的文學(xué)家尤其是進(jìn)士文學(xué)家,表現(xiàn)出相當(dāng)活躍的創(chuàng)作力。整體說來,在宋代江西的文學(xué)家中,最具有創(chuàng)作活力的還是年壽在60-79歲之間者。
以上對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一些現(xiàn)象上的描述與分析。通過這些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族對文學(xué)的推動(dòng)作用,可以探尋到科舉、宗教的發(fā)展對江西不同文體其格局形成的影響,還可發(fā)現(xiàn)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創(chuàng)作量與年壽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這些數(shù)據(jù)與現(xiàn)象背后,還有更豐富的內(nèi)涵有待發(fā)掘,更深刻的意義尚需追索,我們將繼續(xù)嘗試和努力,以期從中尋找到文學(xué)發(fā)展的某種規(guī)律。
注釋:
① 本文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jì)主要依據(jù)《全宋詩》(傅璇琮等主編)及《全宋詩訂補(bǔ)》(陳新等補(bǔ)正)、《全宋詞》(唐圭璋編纂)及《全宋詞補(bǔ)輯》(孔凡禮補(bǔ)輯)、《全宋文》(曾棗莊等主編)以及《宋代江西文學(xué)家考錄》(夏漢寧主編)。部分由宋入元的江西文學(xué)家,其作品存佚情況亦參照《全元文》(李修生主編)。
② 見《宋會(huì)要輯稿·選舉》三之一五,轉(zhuǎn)引自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xué)考論》。
③“詩僧”一詞大約出現(xiàn)在中唐時(shí)期,晚唐以后“詩僧”的稱呼就非常普遍了。“詩僧”的名號(hào)雖然出現(xiàn)在中唐,但其源可上溯至東晉。學(xué)術(shù)界對“詩僧”這一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本文采用的說法是: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的出家佛教徒。
[1](宋)胡仔.漁隱叢話[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王育濟(jì).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親[J].東岳論叢,2001,(3).
[3]周臘生.宋代狀元奇談·宋代狀元譜 [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4]王兆鵬,劉學(xué).宋詞作者的統(tǒng)計(jì)分析[J].文藝研究, 2003,(6).
[5]劉俊麗.宋詩作者隊(duì)伍的定量分析 [D].武漢:武漢大學(xué),2004.
[6](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xué)考論[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9](宋)吳潛.許國公奏議[M].叢書集成初編本.
[10]程民生.宋人婚齡及平均死亡年齡、死亡率、家庭子女?dāng)?shù)、男女比例考 [A].朱瑞熙.宋史研究論文集(第 11 輯)[C].成都:巴蜀書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