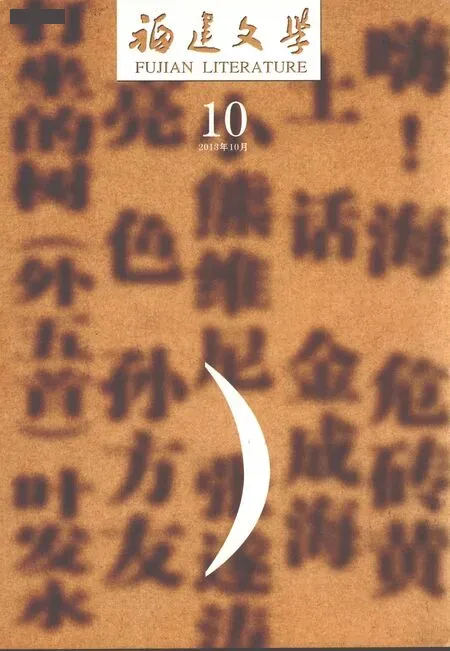我的母親趙與琰
□修 武
壬辰年農歷十一月,我在掛歷“十二月十一”所處的位置上做了一個記號。這是一個扎眼的日子,每年的這一天,我都會想起已經走遠的母親,她是空的,但光線中總能沒來由地摸到她的身影。去年,因為忙碌,我竟然錯過了祭母之日,那一天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為此,我特別提醒自己及家人,要做好祭母的準備。
母親出身于書香門第。母親的祖父姓趙,家住福州三坊七巷衣錦坊三官堂,辦過私塾學堂,是很有名氣的私塾先生;母親的父親也是私塾先生,但他不甘寂寞,后到上海經商去了。母親是家中的獨生女,比父親小十三歲。我的奶奶是林則徐的外玄孫女,奶奶的舅舅是林則徐的長曾孫,名叫林源渼,字清畬。清末民初年間,先后駐德國、法國參贊,之后升任其他要職。奶奶娘家住福州宮巷25號,她父親是清朝舉人,而祖父家住福州光祿坊,兩家人都很熟悉,你來我往,正所謂門當戶對,遂結成親家。我在家排行老二,原名修武。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母親悄然離世。我不知冥冥之中上蒼是否早有安排,這一天是我正式獲得通知將被選調省政府辦公廳掛職之日,一邊是天大的噩耗,一邊是突如其來的佳音,我夾在其間,哭泣無聲。我的家人和鄰居都很清楚,沒有母親趙與琰,就沒有我們一家。母親走后,我的內心世界黯然失色。母親至今已去世十八年了,去世時年僅六十二歲。十八年來,每逢“清明時節雨紛紛”,便是我斷魂時。如今,我的女兒出落得亭亭玉立,也當上了母親,而我已進入天涼好個秋的生命時節,每當有人提起“母親”這個字眼,我總思緒萬千,那些和母親有關的人與事歷歷在目,揮不去,也抹不掉;每當我的家人聚會歡樂時,背地里,我總想起母親的身影,她孤孤單單,無法享受天倫之樂,同時深感對母親的養育之恩無以報答,糾結得很。
九十五歲的老舅奶曾告訴我,母親生我之前差一點就和我一起離開這個世界了。母親快臨產時,為了養家糊口,她起早貪黑,每天乘公交車,停站后再走上一段砂土路,然后搭乘輪船到倉山麻袋廠上班。有一天,大雨滂沱,江上水勢兇猛,母親挺著大大的肚子(離臨產只有一星期),那搭乘的渡船左右搖擺,上下起伏,母親孤身一人,無依無靠,幾乎葬身在江河之中。我出生后,家里口糧不多,可為了全家人的生計母親還堅持上班,母親沒什么奶水,四十五天后,我就斷奶了。母親是家里的頂梁柱,她不僅要養活剛生下來的我,她還要養活家中的另外幾口人——曾外祖母、外婆、我的哥哥,還有生病住在家中的表舅,還要救濟在獄中的我的父親,為生計她日夜奔波勞碌著,從未喊疼,從未喊苦,我的母親,在那樣的一個年代里,她像一根火燭,照著那個偌大的家庭避開了黑暗的吞噬。
其時,母親娘家已家道中落,嫁給父親后,我們這邊的家境也很差,她連尋求幫助的勇氣也沒有。直到我懂事后,我才時斷時續地聽到,那時的母親除了賣力工作,她什么也不去想,她覺得在那樣的一個年代,每個家庭都有著自己的苦難,而在我們家,她正好就是那個可以直面苦難的人。我的母親,整整幾年,舍不得為自己買幾尺布,剪裁一套衣裳,為了節省路費,她每天要花一個多小時,徒步從城里走到倉山,做完工后,她要花費近三個小時才能回到家里。我的母親,她每個月只有二十九元九角的薪水,套用她自己的話說,“這錢抓在手里,怎如冬日里的雪米粒,又輕又薄”。我的母親總會告訴我,要聽長輩的話,要好好讀書,有了知識,就能改變不幸的命運;要學會做人,多做好事多積德,福分都是養出來的,而不是吐出來的。我的母親,她說這話時,我還夠不著她的腰身,但我知道,她在那樣的時刻是幸福的,她的幸福就埋藏在我的身體里,圓鼓鼓的,比那瘦削的日子要來得更有分量。
一直以來,母親就沒有多少說話的時間,她用的更多的是手,是腳,這是那樣的年代可以看到的真正意義上的勞動的樣子。勞動大于一切,因為只有勞動,只有讓身體忙碌起來,母親才覺得自己還活著。每當我看到母親慈祥的雙眸,我就想說話,可我太小,我還不能明白一個母親在她的眼神里所能包容的愛意。好多年后,我長高了,長大了,我才看見母親的眼神開始變得呆滯,一些事物到了她眼里已經不再閃爍。最讓我揪心的就是母親去天堂之前,那是一九九三年底(當時我在三明工作)我回家與她聊家常時,她神態有些恍惚,她指著我說:“三個子女中數你們家最困難了,前些日子在臺灣的二姨丈(臺師大教授)剛剛寄來一點錢給我看病,我準備拿它把這‘房改房’買下來,以后你們如果回家,或者能調到福州工作,也有個寬敞的地方住,即便是二姨丈、姨媽春節回來時,也有個像模像樣的落腳的地方,不至于那么寒酸!”母親說這些話時,聲音很正常,但表情有些異樣,原來在我返回三明臨別之前,她已悄悄地在我口袋里塞了三佰元錢,我回家換衣服時才發現。妻子指責我怎么能拿走母親的“救命錢”啊!我不知回答什么,那錢攥在手中,猶如掰不開的錘子。我的妻子開始有些許不祥的預感,雖然她沒說,而事實是福州的這一次見面已成了我與母親永遠的訣別!當我領著一家人趕回家中,直奔靈堂前,呼天搶地號啕大哭,俯身用臉緊貼著母親,而母親的臉還是微熱的,她身體中最后一絲的力量都凝結在了那兒,我知道,這是母親給我的最后的溫暖了。
我六歲前,從沒見過我的父親,母親也很少說起父親。有時,我會纏著她,要找父親,母親只是輕聲說:“健健,你的父親在外地工作,過段時間他就會回來了。”一九六0年春天,父親在我6歲那年才回家,他是被“左”傾路線冤枉,而后被送進了監獄。父親回來后,母親還是一樣的忙,忙里忙外,父親勸她要休息,母親卻說:“你在監獄受苦了,要休息的是你。”父親的老部下到我家時說父親,“他在獄中可以讀報紙,拉京胡,過著‘逍遙’的獄中生活”,母親就笑。那笑,無聲無息,只能看見母親那兩排白得雪亮雪亮的牙齒。
有一回,家中好像來了客人,客人走完后,我看到桌子上擺著兩瓶魚肝油、兩罐牛奶膏、一瓶鈣片。我嚷嚷著想吃,母親很嚴肅地說:“孩子,這不是你吃的,是寄給我們家‘親戚’的。”我感到很奇怪,是什么親戚呀,母親對他比對我還好?后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曾外祖母才悄悄告訴我,那些我愛吃的東西,是親戚寄給我父親的營養補品,我的父親,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
那個夜晚,我躲在被窩里一個人想著,這個所謂的“親戚”我并沒見過,可我的母親,她在生活面前,在親人面前,她那操勞持家的樣子,我如何也揮不去、抹不掉,難道母親就不怕自己的身體垮了嗎?這件事直到我上小學二年級才知道,原來,我只看到了母親粗糙的手、彎曲的背、睡夢里偶爾發出的沉重的呻吟,對于父親,她所給予的愛是多么真摯!本來,這些補品母親應該第一個享用,一家人生活的重擔全壓在她身上,她還有冠心病,可她從未發出只言片語,唯獨把勞累、辛苦攬在自己身上,她心里裝的總是身邊的親人。
一九八三年,我沒有辜負母親對我的悉心栽培和殷殷期盼,驕傲地坐在了大學教室里聆聽老師的授課。那是我工作若干年后,很努力才跨進了大學之門,而且還考上了冷門的作曲專業。我常想:如果沒有母親的含辛茹苦,沒有她的血汗哺育,我豈能茁壯成長?豈有我今天美好的日子?
屈指算來,母親已離開整整十八年了,有很多親戚前輩們聚在一起還會提到我的母親,說她善良的、說她本分的、說她堅強的、說她白皙漂亮的、說她端莊賢淑的、說她任勞任怨的、說她勤儉持家的,說母親的手掌如何有力,說母親的眼神多么剛毅,說從未見過母親掉淚,說母親是世上少有的女人。我都聽到了,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表情,在他們眼里,我的母親趙與琰好像仍還活在這個世上,可我摸不到,可我喊不出聲,對著空氣也好,對著人群也好,但我能感覺得到,我的母親就在身邊,在朝陽中,在落日里,在那數也數不清的光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