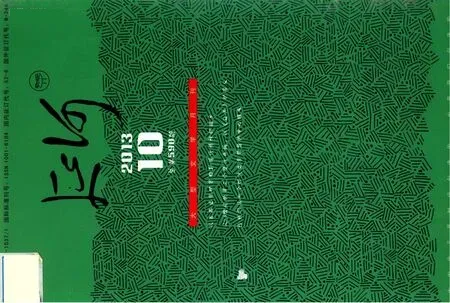鎮 物
張秀峰
自打入伏以來,太平家就沒有真正地太平過一天,總出事,接二連三地,先是死雞,一只一只地死,十天不到,一十幾只雞就全都死了。然后呢,就開始死羊,連當年的羊羔子都沒能幸免,全死絕了。沒過幾天,喂了半年的克朗豬也死了,時隔不長,他家的那頭老灰叫驢也悄沒聲兒地死在了圈里。又是請獸醫,又是按土方子灌藥,一點作用也沒有。看著這些原本上竄下跳、歡實可愛的牲靈們一個個地變成了僵硬冰冷的尸體,太平這心里是百爪撓心。可是呢,還沒等太平緩過勁兒來,家里的人又開始害病,先是老婆,下來是大兒子、小兒子、女兒,這個剛爬蜒起來,那個又睡倒了,輪班換崗地,沒消停過一天,獨獨他沒害。八九月天,莊稼都熟了,正催人呢。太平一天忙完家里的,又忙山里的,跑斷骨頭累斷筋,腳后跟打著后腦勺地兩頭奔。半個月下來,七千多塊就全賠了進去,精精壯壯的一個后生,愣是操磨得變了樣子走了形。
“日他先人的,今年一滿里不順頭。”太平說,狠命地抽著煙。
“狗日的。”太平說。
“要我說,這怕就是命,是命!”太平說,睜著通紅的眼睛。
“你說是命嗎?凈胡球說。”胡子爺挪開了嘴上的旱煙鍋,看著太平,說。
“那可不,不是命還是個甚,你倒說說看,那么多的麻煩事咋就都讓我給攤上了呢?這叫個甚事。”
“吃了驢肉嚷鬼話,大路上的狗屎咋就凈讓你一個踩了呢?放屁拉了一褲襠,哪有這么背運的?我估摸著,得是你那地方有問題,要我說,還是請個陰陽先生來看看吧,不礙事的。”
村里的人都這么勸他。
“球,我才不信那號東西,鬼谷亂談的,兩句鬼話就把你們哄得五迷三道的,哼,我才不相信呢。”太平倔倔地說,脖子一梗一梗地。
“你看你看,狗吃粉子糨(犟)×嘴,糊腦孫了不是?”
“這鬼孫,真是犟板筋,不識人心好壞。”人們說,悻悻然中透著惋惜。
“球樣。”胡子爺說。
“我才不信呢。”太平說,“我上過小學五年級的,學過文化,你們說的那是迷信,是假的。”
老镢頭一上一下地翻飛,很實在,也很沉實。太平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生活。
亮紅晌午的,羅陰陽就來了。
羅陰陽是在背莊埋完人后被太平他大背鍋老漢叫過來的。背鍋老漢知道和太平說這事肯定不行,就先斬后奏。先請來再說。沒想到太平正在家,老漢就有些尷尬。
“我讓他來看看。”背鍋老漢說。
太平就站在太陽地里看著羅陰陽,眼睛亮亮的。
“就是看看嘛,礙不著甚事的,咱家今年不順頭。”背鍋老漢看著太平,說。
“是這,我就是來看看,我不來,是你大硬拉我來的。”羅陰陽說。
太平看著羅陰陽,不說話。
“知道吧,背莊的木狗老漢今早上才發喪出去,一上午都沒消閑,把他家的,這不,剛從山上下來嘛,你大就叫我過來了。”羅陰陽說。
“你要是不讓我看,那我就不看,我還要坐席去。”羅陰陽說,看著太平。
“噢,那就看看”。太平說。
羅陰陽斜歪著腦袋端詳了老半天,眉頭就皺了起來,臉上一忽兒晴一忽兒陰的,然后拿出羅盤,放在地上,站遠了,走近,然后又蹲下,站起,很認真地端祥著,突然像火燒了屁股似地跳了起來。
“啊噢,啊噢,了不得了不得。”說完后,還牙疼似地抽了抽嘴。
太平看著他,覺得這家伙做什么總是神神道道的,很招人厭。
太平一向對這個家伙沒有好感,總覺得他不順眼,削瘦寡白的臉上總帶著些敗敗的灰色,小眼珠子閃爍不定,東瞅西脧的,一點都不正相。特別是說話,總是偷聲緩氣的,好像隨時都在密謀著什么,最不順眼的是那幾根稀稀疏疏的黃胡子,就那么胡亂地支乍著,還總愛穿些個灰不嘰嘰的衣服,松松垮垮的,長袍不像長袍,短褂不像短褂。不知怎么地,太平一下子就聯想到了老鼠,所以一看到他就不由得想笑,現在,他又想笑了。
“什么?”太平問。拼命地忍住笑。
“你這窯址是誰定的?咋連個規矩都不懂。”羅陰陽說,語氣很嚴肅。
“我這地方向陽背風,吃水又方便,還不好嗎?”太平問。
“啊呀呀,你這人真是的。”羅陰陽瞅著太平,有些不耐煩。
太平不說話,只是眨巴著眼睛看他。
斜眼瞅著太平,看他像真是不懂,就有些恨鐵不成鋼的意思:“是這,你這地方坐字兒不對,曉得不?你看看你看看,啊喲喲,這叫什么話?啊,怕連姜太公、徐荗公也不敢坐這樣的字兒呢,咱算什么?平頂子老百姓一個,這么價胡來,能服得住?”
“要改,一定要改,要不就麻煩可就大了。”羅陰陽說。
“嘿嘿,我不信,”太平終于憋不住,笑出聲來,“打小我就不相信那號事。”
“什么,你再說一遍。”
“三個陰陽定不下了拴驢的橛子。”
“你呀,真是頭驢,一頭倔驢。”羅陰陽說。
“這號人,說不成個球事。”羅陰陽說,跺跺腳,走了,肚子一鼓一鼓地,活像只蛤蟆。
“哎,我說你個鬼子孫羅陰陽,咋不吃飯就走啦?”
太平來找羅陰陽的時候是一個有霜的早晨,羅陰陽正在拉屎,臉憋得紅紅的,像個正在下蛋的小母雞。太平就站在茅房外短短的土坯墻邊跟他說話。
“消停了,總算是消停了。”太平說。
“噢。”
“雞死了,豬死了,老叫驢也死了,”太平說。
“噢。”
“你不曉得,我那是半大的克郎豬呢,骨架可真不小,就是還沒長膘,說好了今年十月出欄,賣個好價錢,咋說死就死了呢,好可惜。”
“噢。”
“那是我開春時在集上買的,出了二百塊錢,我能看出那是個好胚子。”
“噢。”
“還有,我家的那頭驢,你見過,是頭叫驢,頂好使喚的。一點也不欺生。那年滿順用騾子和我換我都沒答應,我那驢真真兒個好,口輕,又肯下死力,猛格拉乍地,就死了,”太平說,“日他先人的,這叫什么話。”
“我大也歿了,今兒個是頭七,”太平說,聲音顫顫地,頓了頓,又開始說,“安塞、延安,幾個大醫院都去過了,查來查去,愣是查不出個什么,眼見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那么剛強的個人,竟然疼得嚎哇哭叫,實在沒法子了,請后陽溝的王巫神來跳過一回大神,好了幾天,就歿了,唉。”
“噢。”
“誰不曉得王巫神頂著黑虎靈官呢,聽有萬老漢說,很靈的,拉板她媽的心口疼就是他給看好的,咋就偏偏治不好我大的病呢?你說,這是不是命啊?”
“噢。”
“唉,我看就是命,老輩人常說……”
“胡球說甚哩,這咋是命哩嘛?我說啦,是你那地方有問題,”羅陰陽一邊說,一邊系著褲帶,語氣十二分地肯定。“早就給你提了醒,你個狗日的就是不聽,看看,看看,這不有事了嗎?哼。”
“咋會有問題呢,我不信,”太平說,語氣軟軟的,明顯的底氣不足。
“你那地方坐字不對,”羅陰陽加重了語氣,說,他左右看了看,忽然壓低聲音,將嘴湊近太平的耳畔,“而且還被人下了鎮物。”
他一驚:“什么?鎮、鎮──物?”
“對嘍,就是鎮物。”
“怎么可能呢,絕對不可能。”
羅陰陽看著他,笑了笑,背抄著手,雄赳赳地回家去了。
他馬上意識到:事態嚴重了!脊背上一陣發涼。這下可不得了了,他知道,若真如羅陰陽所說,那他家發生的一切不幸就全都會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以前他只是聽說過,并沒有親見,石匠給人家箍窯洞時,若有主家怠慢于他,他便會給這家人下鎮物── 一把泥刀、一個鋼釬甚至是一雙破手套、一塊石頭,只要一沾人血,然后封進窯里,就會變成一個十分靈異和可怕的東西,然后這家人就別想有安生的日子過,輕則多病多災,重則死人斷后。
太平臉色通紅,憤怒使得五官都挪了位。
“狗日的。”他咬著牙,狠狠地罵。
“是金鎖,肯定是他,這個狗日的,我箍窯時這小子才是個學手,合龍口那天我發煙時忘記給那狗日的發了,他當時就惱了,口口聲聲說我沒把他當人看,”
“肯定是那小子。”太平說。
“你得禳解。”米陰陽說,“要不還得出事。”
果然,經過一番搜騰,在第三個窯腿下找到了一些物件:一把泥刀,幾根鐵釘,都已經銹得不成樣子。
米陰陽說,按行規要收二百元錢的,但這是行善事,就不能要錢了,可又不能壞了規矩,就拉走了太平家的一只黑頭山羊。
“這是行善事。”羅陰陽說。
年底剛過,太平就被槍斃了,犯的是故意殺人罪。
村里人說,太平也真是的,金鎖給你家下了鎮物,那是你怠慢人家在先,別忘了,那可是匠人呀,就他那驢脾氣,換了金鎖,別的匠人也會這么做的,及古以來,沒聽說過誰還敢得罪匠人的。再說了,你把金鎖殺了,那是他的報應,一對一扯平,告到法院也有理,你殺人家的老婆娃娃做甚?不死才怪呢!
太平的婆姨自太平抓走后就瘋了,整日價坐在門口哭一氣,又笑一氣,晚上就在對面的山畔畔上孤魂野鬼似地游蕩,發出一陣又一陣的長長的嗥叫,像狼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