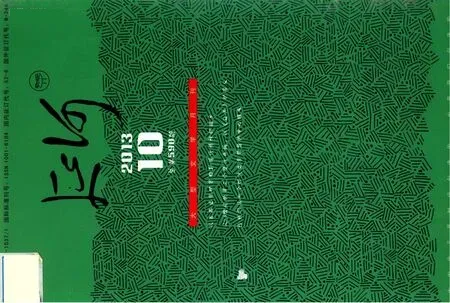直擊人性的殘缺——讀阿南的中篇小說《殘瓷》
阿 探
阿南的中篇小說《殘瓷》(《延河》2013年7期),是直擊文化藝術心態的作品,突破了現實、歷史的時空觀,在二者對照、交錯中陳鋪,以歷史的滄桑和現實的癲狂,直擊了殘缺的人性、社會文化心理,是民族藝術本真意識缺失的普遍意義寫照。
小說具有較大的容量,涉及了繪畫藝術,瓷品鑒賞,鑒古藝術,藝術家、商人生態,文化生態等等,既是鑒賞藝術知識的傳播,亦是歷史與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寫真,是作家長期文化生活體驗、沉淀的結晶。
元代青花爐,稀世珍品。
元瓷,以傳世稀有,融合漢民族以外的文化因子及海外貿易之影響,集瓷品工藝、審美發展之大成,而成為中國瓷文化一個重要而短暫的歷史聚核階段,明清瓷器形制、品類等均不出元瓷范疇。一件古董,其價值在于一段歷史的文化提煉,凝結和永恒性意義的承載,這,是不能用市價所能衡量的。
作品構思高妙。歷史現實兩條線索看似永不相交,實乃氣韻神韻相通,血脈相連,為同一主題潛滋暗長。設疑巧解,以現實、歷史不完整之結局,給讀者留下巨大的閱讀空間,完成了作品的整體圓潤。
小說以這件元青花的充滿人間大義至情,凝結仇恨殘酷的歷史原焰中錘煉歷程,在現實中純真回饋的贈送,充滿貪婪的高智慧商人伎倆的順手牽羊式的掠奪,以及終成殘品的過程,刻畫了物欲社會現代人“經營”歷史感,失卻人之本性的高智商高情商;至真至純藝術追求者的寂寞,悲涼;穿越漫漫歷史與現實,將元瓷匠人苗根大與當代民間畫家六子對藝術的理解和堅守,卑微困境,元代胡商馬可與當代藝術商人陳兆遠對藝術的取巧與投機,一時的得意永久的悲催,遺憾有機融合,達成了作品的人物命運的古今通義。
元青花依舊是元青花,穿越了歷史走進了現實,由稀世珍品卻變成殘品殘瓷;六子沉淀至久至純的畫依然在現實中寂寞無人識,無法擺脫商人的掌中擺布。
是元青花爐殘缺了嗎?
是功利社會下人性失衡的殘缺!
古今如此,尤以今甚。
作品的意義似乎遠遠超越了所涉及的層面,當下之文學領域,推及更廣的經濟社會各行業意義的“藝術”追求,就會發現,正是利字當頭的通則導致了社會大面積的“人性殘缺”,心靈失衡。過度的功利追求,不僅僅造成對主流文化的破壞,對社會個體生活安全的威脅(如毒奶粉毒大米等),更重要的是對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因此,極度功利是藝術的死敵,亦是人性殘缺的本源。在這個意義上,陳兆遠是一個只有歷史文化知識而沒有歷史意識的鑒賞者、投機者,而不是一個藝術家;單純的苗根大和六子才是真正意義的藝術家;元代胡商馬可(匯通中西的馬可波羅)僅僅是中國燦爛文化藝術的過客。
小說人物刻畫是成功的,選取京味題材,并未著力凸顯京味,卻以高雅者的“俗化”反襯出人物現實生活的“本真”。陳兆遠的“俗”是得志得意者的橫行于世的霸氣大氣,物欲生態下虛偽機變的體現;六子的“俗”是真正藝術家的卑微生存生態的體現。歷史線索中苗根大審美意識的古板堅守是民族文化核心精神的體現;胡商馬可的藝術改造則為外來文化對民族核心文化沖擊。現實敘事的現代元素的紛雜融入呈現著當下普遍浮躁的社會心理;歷史敘事的冷靜沉穩是歷史滄桑的寫照。沒有寫成京味小說,恰恰是阿南一種成功的突破,文本整體彌漫著東北人的豪爽直爽之氣,大大增強了文本的可讀性。
“自古以來,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他們把本屬于世界的美好,完全當成一個人的玩物,以至于在死后都不肯撒手而去。他們的墓穴里的那些華麗殉葬,到頭來哪一樣不是成全了如饑似渴的盜墓賊?”(第5章)
雖是婦人之見,卻既是陳兆遠極度占有欲的時態寫真,亦是對歷史文化的確切概括。第7章文尾師傅提出把玩元青花爐兩天被陳兆遠婉言謝絕,是對這一心態的進一步精度刻畫。
“胡鬧!手藝人,怕就怕投機取巧。”聽完馬可的設想,苗根大看都沒看,就武斷地否決了他草擬的革新方案。
苗根大的態度頑固而蠻橫,說服他放棄對老法的推崇,無異于是在以沙筑城。(第8章)
真正恒久的藝術就是某種艱難的持守。類似以上的極具穿透性的語言還有多處,一定程度上是阿南對純度文學的堅定選擇與執著追求。
小說唯一不足,文本稍顯冗長,形制不夠凝練,大約在于作家對作品承載期許過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