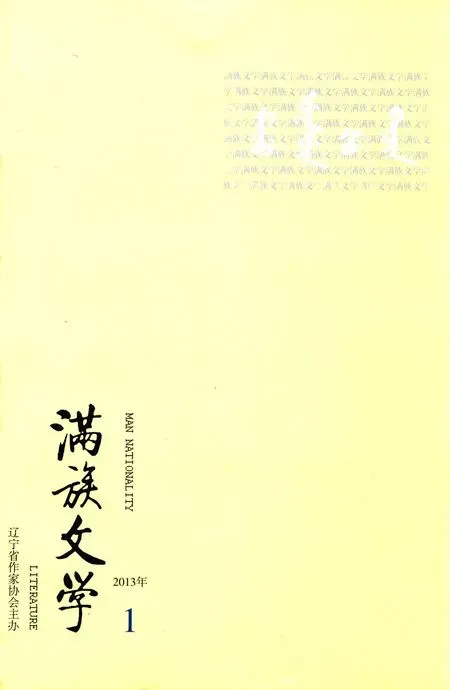寫在書的另一邊
賈 穎
亂彈讀書
買了一堆書。
于是,八小時之外的主題,就是,看書。
一邊看書,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藏書的人。
藏而不看的人,是不是有些像意淫美色的男人?把漂亮女人搜羅回去,放在那里,用來顯擺,卻并不用實際行動去愛。甚至連偶爾情趣所致的一個調情都沒有。
唉!替美人寂寞。替架子上的書寂寞。
女人是用來愛用來寵的,不是當家具一樣用來擺著顯闊氣的。
書是用來讀用來學習的,不是當不動產一樣用來擺著充學問的。
有的書,像妻。必讀。必備。讀著踏實。
有的書,像妾。須讀。須備。讀著輕松。
按說,形容書,應該恭敬些。但,妻妾成群坐擁天下的那種成就感,用來形容讀了好多內容風格各不相同的書,真的是很貼切。
書上說
書上說,西周時,組玉佩是用來約束人行走儀態的。組玉佩掛在身上,行走時不能發出玉相撞的聲音。
若是我有一組玉佩掛著,在走路時,大概是不會腳步輕挪,走出雍容與華貴之感。倒是很有可能會故意蹦跳著,聽玉和玉之間親昵清越的“丁丁當當”。
書上說,臣和妾,在古代都是奴隸。臣是男奴隸。妾是女奴隸。
怎么是這樣子?還以為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貴呢。不過,也對。臣,是天子的奴隸。妾,是男人或者是愛情的奴隸。想象中,還是侍立一旁,為愛守護的妾,形象更親切,也更具楚楚動人的味道。臣,跪拜在一個男人面前,跪拜在權力面前,實在很“奴”。
書上說,所謂卉服,是指用長滿樹葉的樹枝做的衣服。
這很像是《圣經》里夏娃和亞當的衣服。不過,他們西方人似乎更節儉,用的是葉子,沒有樹枝。
書上說,在很久很久以前,農歷二月十二是百花的生日,謂之“花朝”。為什么,我們過了那么多與我們的歷史和信仰不相關的節日,卻不記得“花朝”呢?為什么不可以懷一顆誠摯之心,在每年的春天來臨之前,感謝百花在四季中帶給我們的繽紛色彩和芬芳花香呢?
百花——這是大地和自然饋贈給我們的禮物呀。
愛上王維
看書看到愛上王維。
能詩,會畫,精通音律。
這樣的男子,誰不愛呢?
如果可以,就讓我生在唐朝,做一個小小的書僮,陪伴在他的左右。
只是,這樣的陪伴,該不該停止在玄宗天寶十四年呢?那一年,安史之亂,被賊軍捕獲的他,當了偽官。
愛上王維。只愛天寶十四年之前的王維。
他的詩,是在用文字描畫山水——“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寥寥數句,如潑墨山水。
他的畫,云水飛動,清新灑脫,一如俊逸的田園詩篇。
還有他的音樂天賦,僅憑一幅奏樂圖,便知是《霓裳羽衣曲》的某疊某拍,分毫不差。
想起十六年前,我讀大學四年級,寫畢業論文,選了海明威。
這是與王維不同的另一種男人。
海明威,言語簡潔的像電報似的男人,喜歡飲酒,狩獵,捕魚,拳擊和滑雪。一個純粹的硬漢,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
也是像今天這樣,我查資料查到愛上海明威。恨不能將圖書館里,所有與他有關的書籍,統統偷走。
入選標準:(1)符合《中國帕金森病治療指南(第二版)》[6];(2)接受抗帕金森病藥物治療達劑量穩定期至少30 d;(3)年齡介于30~80歲;(4)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我學喝酒,看拳擊,瘋狂閱讀海明威的原著,學習他濃縮緊湊的語言風格。崇拜海明威崇拜到,渴望嫁給他。
讀書讀久了,有時,真的分不清,究竟,是愛上了那些文字,還是,愛上了寫出那些文字的那個人。
給文字以靈魂
文字也有靈魂呢!
這是近來讀書的感悟。
讀到一句話: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
這句話說的很對。文章的好壞,是看寫的人是不是在用心寫出自己的真誠。
做假的文章,詞句再華麗,結構再復雜,只是貌似深奧。
沒有靈魂的文章,充其量是一堆文字的排列組合而已。
就像女人——(其實我是愛女人的)
有靈魂的女人,才漂亮,才讓人回味無窮。即使是擦肩而過的一瞥,許多年后回想起來,也是動人心弦的浪漫。
沒有靈魂的女人,長得再好,也只是趁著年輕時賺幾年風光。等歲月變成皺紋顯現在臉上時,沒有了靈魂的姿色,只剩下蒼白的一聲嘆息了。
遙望七十年前的戰場
本來是為了尋找華萊士線。就是那個區分亞澳物種的分界線。結果沒有找到這條隱形線,卻天天把世界地圖捧在手里,尋找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交戰國的進攻和防御線。
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很好看。精彩。只是,書中有一句翻譯,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horse-minded,鈕先鐘先生翻譯成“戰馬情懷”,而我以為,譯成“戰馬情結”會更貼切一些。情懷是一種浪漫,而情結中的這一個“結”字,別有味道。正是因為這一個結,才牽絆住了波蘭在戰爭中的速度和力量。他們在一場現代的機械化戰爭中,居然仍然信仰騎兵沖鋒的價值。
勝敗,拼的真的是與時俱進的思想和思維。
雖然與時俱進這個詞,已經被人們用的濫俗,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在與時俱進呢?不過是說說而已。
清早讀了一小時的戰史,并沒有讀幾頁。
從前拿到一本書,會著急趕快看完。仿佛看完了,也就了了一份心事。現在讀書,慢得很。一本稍厚重些的書,沒有一個月兩個月的,似乎是讀不完的
現在讀書,真的是在享受一種樂趣了。比如,讀戰史,里面不僅僅是在講一場戰爭,有許多戰爭以外的東西。
“戰爭是件太嚴重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軍人。”這是法國曾經的總理克里蒙梭說的。
套用一下格式:讀書是一件太復雜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眼睛。雖然有些不通,大概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