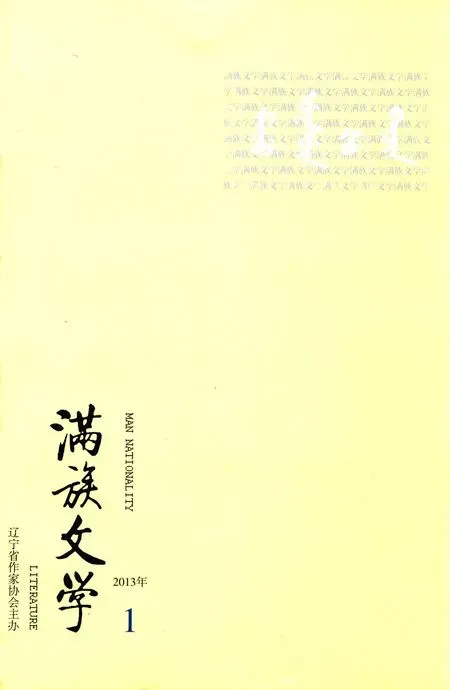故園之戀
孫成文
老屋后面,深刻在記憶中的兩棵樹
老屋后面有兩棵樹,一棵是棠梨樹,一棵是杏樹,是我兒時(shí)見過最大的兩棵果樹,長(zhǎng)大后所見到很多同類的果樹,大多也沒有這兩棵樹那么高大、粗壯。
至于這兩棵樹是自然而生的還是人工栽植的,我就不很清楚了;反正,自打我記事兒起,它們就已經(jīng)那么高大、那么粗壯了;至于我對(duì)這兩棵樹的所謂的關(guān)注,其實(shí)更多的是對(duì)脆甜棠梨和酸甜杏子的關(guān)注罷了。
從直覺上判斷,那棵棠梨樹是該早于那棵杏樹落戶我們家的;當(dāng)時(shí)那棵棠梨樹,我用手臂合抱不住;那棵杏樹呢,倒是可以合抱過來(lái);當(dāng)然,這僅僅是我一廂情愿的猜度而已;至于梨樹與杏樹同期生長(zhǎng)的速度是不是一樣快,這是生物學(xué)研究的范疇,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還是先說(shuō)說(shuō)那棵棠梨樹吧。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棵樹的樹干又粗又直又長(zhǎng);樹冠上最低的部分,與地面的距離至少也有一米八左右。這樹長(zhǎng)得相當(dāng)茂盛,春季里,那綴滿樹冠潔白的花朵,遠(yuǎn)遠(yuǎn)望去,宛如銀白色碩大的傘面,醒目在你的視野之中,那景象非常壯觀,令心靈感受到一種純粹的凈化和洗禮。盡管小時(shí)候并沒有更多的詞匯來(lái)形容當(dāng)時(shí)的感受,但現(xiàn)在能重溫清晰的記憶,且這樣來(lái)表述,心里還是算比較欣慰的。
繁花落盡的時(shí)候,地面上飄落了一場(chǎng)厚實(shí)的雪,那是場(chǎng)不死的雪;而雪的精魂,已化作了青澀的果實(shí),精神抖擻地高掛在枝杈上,沐雨臨風(fēng)地生長(zhǎng)著。
相信在孩子簡(jiǎn)單又樸素的內(nèi)心世界里,最大的渴望就是緊盯著那些青澀的果子一點(diǎn)點(diǎn)長(zhǎng)大,然后成為脆甜可口的幸福。時(shí)間一天天過去,夢(mèng)便一直這樣延續(xù)著;直到那一天,高遠(yuǎn)的天空下黃綠交錯(cuò)的葉子間,近似橢圓型、褐黃色的山楂般大小的果實(shí)掛滿了枝頭;無(wú)論遠(yuǎn)聞,還是近嗅,到處都彌漫著甜絲絲、香噴噴的氣味,那氣味誘惑又沁人心脾……
每當(dāng)這個(gè)時(shí)候,奶奶的一句“這棠梨好了”,總讓“小尾巴”的我欣喜不已。奶奶呢,則是操起一根細(xì)長(zhǎng)的木棍子,踮起一雙小腳,朝著樹上一棍子一棍子抽去,我呢,則是在地面上鋪開一塊塑料布,那打下的棠梨便噼里啪啦地雨點(diǎn)般落下來(lái);在我看來(lái),奶奶是很講究抽打技術(shù)的,輕重緩急拿捏得相當(dāng)好,抽打的位置把握得也準(zhǔn)確;因?yàn)楣髯映榇蛄Χ刃×耍睦婢蜁?huì)頑固的還掛在枝頭上;力度大了呢,會(huì)打折樹枝或者把棠梨打的遍體鱗傷。可是奶奶抽打下來(lái)的棠梨,一個(gè)個(gè)囫圇著呢,沒有一點(diǎn)傷痕。
待收拾好落下來(lái)的棠梨后,奶奶總是喜歡坐在一邊,微笑著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并一再叮囑:慢點(diǎn)吃,別急!有的是呢!
那棠梨啊,真是好吃!皮薄肉脆,咬一口滿是甜甜的水兒,還有一股別致的香味兒;那是一直流到心底的甜香,至今都還忘不掉。
對(duì)于那些掛在高處,奶奶的長(zhǎng)棍子也抽打不到的棠梨,便交給猴子般的老叔來(lái)解決了。個(gè)頭不高的老叔爬樹技術(shù)堪稱一流,脫下鞋子,抱住樹干,兩只腳就那么隨著兩只相攏的手臂移動(dòng),向上一縱一縱地,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那干凈利落的身手,讓站在樹下仰望的我好生羨慕。只見他胸前掛著一個(gè)大兜子,一會(huì)兒將這個(gè)枝頭的棠梨擼下來(lái),裝進(jìn)大兜子,一會(huì)兒又爬到另一個(gè)枝杈上再擼一通,看得我目瞪口呆;待大兜子裝滿了,他又似猴子一樣的遛下了樹干。
一大兜子囫圇個(gè)的棠梨照樣也被我享用了。小孩嘴饞又貪心,再加上奶奶老是由著性子的寵著;棠梨吃多了,也就出問題了。晚上肚子里難受,折騰過來(lái)再折騰過去,說(shuō)什么都睡不著;熬到終于睡踏實(shí)了又尿了床。自然少不得母親的一通埋怨和斥責(zé)。可是,孩子的特色就是記吃不記打,第二天照吃不誤,沒辦法,好吃嘛。
奶奶這個(gè)人熱情好客在關(guān)屯是出了名的,每當(dāng)棠梨熟了的時(shí)候,如若山下的鄰里們來(lái)做客,奶奶總會(huì)拿起那根細(xì)長(zhǎng)的木棍子,在梨樹上抽打幾下,一陣?yán)嬗旰螅瑵M盆的棠梨端在鄰人面前;吃完了,還要給人家拿一些回去,說(shuō)是給家里的孩子們吃一吃。奶奶這么做,讓我心生不滿;把棠梨都給了別人,自己就沒得吃了。面對(duì)我的埋怨,奶奶只來(lái)那么一句“好東西不能都自己吃”,就把我打發(fā)了;當(dāng)時(shí)我是無(wú)奈的,但是后來(lái)我逐漸意識(shí)到了奶奶這句話的含義;至少,我們家的棠梨從來(lái)沒被誰(shuí)偷過。
至于那棵杏子樹嘛,就有些其貌不揚(yáng)了,比棠梨樹要矮上差不多一半的樣子,樹身也不直溜,是那種典型的歪脖子。
一般的樹都是朝陽(yáng)的那一面茂盛蔥蘢,而這棵杏樹卻很怪,它歪向西面,樹冠也是向西傾斜,而面西的樹冠依然很茂盛,初夏之后,樹冠上掛滿了金黃的杏子,把枝頭壓得很低很低,奶奶踮起小腳就可以摘到枝頭上的杏子,我搬來(lái)一個(gè)小板凳踩上去也可以摘到。
那杏子個(gè)頭絕對(duì)不亞于杏梅,口感也相當(dāng)好;肉質(zhì)在嘴里,讓你感覺到一種柔軟的親切,尤其那淡淡的酸味兒里夾雜著一絲絲的甜,真是既爽口又爽心。
每到杏子熟了的時(shí)節(jié),兩個(gè)姐姐總是捷足先登,她們的個(gè)頭加上板凳的高度,還有那難看的吃相,惹得我又氣又急——用現(xiàn)在的話來(lái)說(shuō):那可真是羨慕嫉妒恨啊!只不過她們還是忌憚奶奶的招呼:“給大寶分點(diǎn)兒,別光顧著自己吃!”這時(shí)候她們兩個(gè)才會(huì)極不情愿地“施舍”幾個(gè)杏子給我,但免不了還責(zé)備我?guī)拙洌豢吹轿以诮憬忝媲拔臉幼樱棠滩桓吲d了,索性趕走了她們兩個(gè),然后也站在凳子上給我摘下來(lái)一些,看著我吃夠了才算了事兒。
樹上的杏子越來(lái)越少的時(shí)候,奶奶叮囑兩個(gè)姐姐不要再去摘了,剩下留給我吃。我很開心,在奶奶那里我總會(huì)受到優(yōu)待的。她們兩個(gè)這時(shí)候倒是對(duì)我的得意也生出嫉妒來(lái),經(jīng)常在我面前說(shuō)奶奶偏心眼,還說(shuō)要給我“小鞋穿”(就是找我的麻煩)。我不怕,我有奶奶當(dāng)靠山呀,沒辦法啊,奶奶慣著我呢。
每當(dāng)春天泥土完全從酣睡中蘇醒過來(lái)的時(shí)候,奶奶總是顛著那一雙小腳,用廢水桶或者土籃子,從豬圈或者廁所里取出足量的糞水,然后在棠梨樹根部用鐵鍬挖出一圈淺淺的坑來(lái),說(shuō)是給樹“喂食”。哈,聽說(shuō)給小孩子喂飯,還沒聽說(shuō)給樹喂食呢。奶奶見我好奇,就簡(jiǎn)單地說(shuō)小孩兒天天喂飯才能一點(diǎn)點(diǎn)長(zhǎng)大啊,樹要多結(jié)果子,也要給它喂食啊。哦,我似懂非懂地點(diǎn)點(diǎn)頭,也幫著奶奶忙活起來(lái)……
可是總見奶奶給棠梨樹喂食,卻極少看見她給那棵杏樹喂食。問奶奶緣由,奶奶一臉不屑地說(shuō)那棵歪脖子杏樹,就那樣吧,樣子也不好看如何如何。可是,畢竟那棵杏樹也給了我們夏季爽口的美味兒啊,怎么會(huì)有不一樣的待遇呢?就是因?yàn)樗摹伴L(zhǎng)相”難看嗎?在我一再的堅(jiān)持下,奶奶勉強(qiáng)地給杏樹喂了不多的食。我為那棵杏樹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委屈而鳴不平,可是我拗不過奶奶,也只好那樣了。每當(dāng)夏季吃杏子的時(shí)候,我看著杏樹發(fā)呆,再想想奶奶的做法,有一種說(shuō)不出來(lái)的滋味涌上心頭。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過去,兩棵樹就那樣安靜地開著花、結(jié)著果。可是,就在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個(gè)夏天,夜里,好大一陣子的電閃雷鳴后,那棵棠梨樹被霹靂攔腰斬?cái)唷R辉缙饋?lái),我看見了碩大的樹冠躺在地上,還有那些枝頭上青澀的果子也散落一地,心里十分難過,我再也吃不到脆甜的棠梨了,那些脆甜只能屬于這個(gè)夏天之前的甜美記憶了。
那棵杏樹呢,那年夏季里也只掛了稀疏的果子,很快就被我和姐姐們消滅了。在秋天還沒來(lái)的時(shí)候,它的葉子竟然開始打蔫,隨后就干枯了。母親說(shuō)杏樹是遭受了一種專門吸食樹身營(yíng)養(yǎng)的蟲子的襲擊,這種蟲子啃食樹身,在樹身鉆了無(wú)數(shù)個(gè)洞,產(chǎn)卵、生子,榨取樹的營(yíng)養(yǎng)和水分,最后樹就枯萎了。我自然痛恨那些蟲子,卻也無(wú)奈這樣的結(jié)局。
曾經(jīng)帶給我無(wú)限快樂和美味的兩棵樹,竟先后遭此厄運(yùn),可以說(shuō)結(jié)局悲慘,沒能壽終正寢,這也是它們的命運(yùn)吧。至今想來(lái),記憶中的這兩棵樹能留下的也只是美好和哀婉,也許就夠了,還能奢求什么呢?
想起魯迅在小說(shuō)《社戲》里有這樣一句話:從此再也沒有看到過那夜似的好戲,吃到那夜似的好豆……就現(xiàn)在的我而言,再也不會(huì)有那樣脆甜的棠梨和微酸柔軟的杏子打動(dòng)我的味覺,那些脆甜和微酸絲甜的感覺,不會(huì)再來(lái),它只歸屬于童年的美好,只歸屬于心靈美好抑或傷感的沉淀……
老戲臺(tái),消逝和遺留的猜想
老戲臺(tái),在故鄉(xiāng)關(guān)屯大廟山的西山坡上,那是每天都早早地曬在陽(yáng)光里的一個(gè)角落。戲臺(tái)早已不復(fù)存在,小時(shí)候乃至今天能夠看到的,就是掩映在荒草之中的兩座大墳塋。墳塋的上面,有一個(gè)被荒草覆蓋且形狀模糊的平臺(tái),料想這就是當(dāng)年所謂戲臺(tái)的遺跡吧。
其實(shí),關(guān)屯人早已習(xí)慣地把那兩座墳塋稱作老戲臺(tái)。這樣的一個(gè)代名詞,讓我從小時(shí)候就開始猜想,這兩座墳塋與一個(gè)泥土平臺(tái)間到底有什么聯(lián)系。
許是心理作用吧,小時(shí)候,每每見到墳塋,總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疑似有所謂的“鬼”會(huì)從那里爬出來(lái)。一次跟伙伴們鉆林子藏貓貓,藏著藏著,一不小心便誤入了老戲臺(tái),當(dāng)看見那兩座大墳塋時(shí),嚇得我嗷的一嗓子,兔子般地撒腿就跑,伙伴們也跟著四散奔逃。然后我便是大病一場(chǎng),整天昏沉沉的,發(fā)著高燒說(shuō)著胡話。母親跟奶奶急得又是找大夫又是燒什么“聚魂貼”,還在夜深人靜時(shí),用水瓢輕敲水缸,接連不斷地念叨著“成文魂兒快上身啊!”
我也不知道最終是什么療法救了我的命,反正后來(lái)病是好了。奶奶心疼地叮囑我:以后可千萬(wàn)別再去老戲臺(tái)了,讓那兩個(gè)戲子見怪了,可不得了啊。
奶奶的話讓我愈加好奇起來(lái),戲子?什么是戲子啊?奶奶極其認(rèn)真地解釋說(shuō),就是唱戲的。為什么唱戲的叫戲子啊?奶奶有些不耐煩地說(shuō),小孩子問那么多干嘛?!后來(lái)想想,奶奶其實(shí)也不知道戲子稱謂的由來(lái),也就故作不耐煩地那么搪塞我了。
母親見我好奇心很強(qiáng),就把她從太爺那里聽來(lái)的故事講給我聽。
說(shuō)是大廟山建成了龍母廟之后,就在山的西面修建了一個(gè)簡(jiǎn)陋的戲臺(tái),每每遇見重大節(jié)日,南來(lái)北往朝拜的人多的時(shí)候,就請(qǐng)來(lái)了戲班子演戲,為那些朝拜的人們豐富點(diǎn)娛樂生活。據(jù)說(shuō)有一天晚上臺(tái)上的武生戲正演著,不知何故,竟然有兩個(gè)扮相跟臺(tái)上兩個(gè)戲子一模一樣的人混上了戲臺(tái),于是雙方就真的打了起來(lái)……后來(lái)那兩個(gè)演武生的戲子就死在了臺(tái)下;再后來(lái),關(guān)屯人就把那兩個(gè)戲子埋在了戲臺(tái)的下面。于是就有了現(xiàn)在的兩座大墳塋。
也許是忌諱那地方死了人吧,從此戲臺(tái)便不再有戲上演了,它被人們冷落著逐漸淡出視野,然后經(jīng)年風(fēng)剝雨蝕變得越來(lái)越破敗,倒先于大廟山的龍母廟被拆掉了。
我有些惋惜,為什么是兩個(gè)武生戲子死了?他們不會(huì)功夫嗎?興許死的是那兩個(gè)混上戲臺(tái)的壞人呢?我向母親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母親無(wú)奈地回答我說(shuō),你太爺就是這么講的,細(xì)底究竟怎么樣,我上哪兒知道啊。
是啊,太爺早已故去,我再?zèng)]有機(jī)會(huì)去找他問問清楚了。
從那之后,我經(jīng)常一個(gè)人傻兮兮地遠(yuǎn)遠(yuǎn)地望著西山坡上的那兩座墳塋發(fā)呆,始終想知道那兩個(gè)戲子與戲臺(tái)更多的東西。顯然,答案也就僅限于母親告訴我的那些。
我就那么帶著惋惜與遺憾望著,也帶著一顆好奇的心,想象著那兩個(gè)土堆下面深埋的故事。
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初期,當(dāng)電影版的京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在關(guān)屯上演的時(shí)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把童祥苓扮演的楊子榮的形象,與想象中的老戲臺(tái)上那兩個(gè)逝去的戲子進(jìn)行比對(duì)——想象他們的眼睛也是那么亮、動(dòng)作也是那樣地干凈利落,唱腔也是那么的清脆圓潤(rùn)……
看完電影,我竟然又胡思亂想起來(lái),興許童祥苓等京劇演員就是那兩個(gè)戲子的后代或者是他們徒弟的后人。這樣的想法跟母親一說(shuō),母親竟然笑得眼淚兒都流出來(lái)了——兒子啊,你都想到哪兒去了,笑死媽了啊!為什么不會(huì)啊?我一臉認(rèn)真地反問。你都哪來(lái)的那么多為什么啊,我可不知道啊,也不能瞎說(shuō)啊。
我還要問什么,母親剛才的笑臉突然一下子消失了,她板著面孔嚴(yán)肅地告誡我:到外面可不能這么亂問別人,也不能這么胡亂聯(lián)系啊,楊子榮是革命英雄,那兩個(gè)戲子是封建的牛鬼蛇神,是被批判的對(duì)象,這么聯(lián)系就是反動(dòng)派啊,是要被批斗的啊。這……我又糊涂了,但看著母親那張嚴(yán)肅的臉,我剛要出口的話又咽了回去,似懂非懂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后來(lái)看到的一些人和發(fā)生的一些事,證明母親的告誡是正確的。那時(shí)候,是不能亂說(shuō)話的,無(wú)論大人還是小孩兒。
但心里面,老是在犯嘀咕:不都是演戲嗎,怎么還分英雄形象和牛鬼蛇神啊?唉,真的搞不清楚了……
真正搞清楚的時(shí)候,童真已不再,只有故鄉(xiāng)的老戲臺(tái)以及相關(guān)的疑問始終在腦海里徘徊。
現(xiàn)在想想,關(guān)于老戲臺(tái),我認(rèn)為母親當(dāng)年講的不是故事,是傳說(shuō),可信度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有些捕風(fēng)捉影的意味兒。可是,我又不愿意相信那是傳說(shuō),因?yàn)槟莾勺鶋瀴L還在,那個(gè)地方依然被故鄉(xiāng)人稱作老戲臺(tái)。一些陳年的舊事盡管沿革成了傳說(shuō),但畢竟還有些影子在里面摻雜著,不可能是空穴來(lái)風(fēng)吧。
無(wú)論如何,老戲臺(tái)——那兩個(gè)大土堆,豐富了我童年時(shí)代的猜想,也許,我的聯(lián)想和想象能力的培養(yǎng)就是從對(duì)它的猜想開始的吧……如是,除了感謝故鄉(xiāng)的老戲臺(tái),剩下的依然是無(wú)法抹去的猜想。
童年里關(guān)于老戲臺(tái)的那么多的疑問,至今仍是一個(gè)謎。沒有誰(shuí)能幫我揭開,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我只能在心中無(wú)奈地承認(rèn)這是一個(gè)傳說(shuō)的事實(shí)。但,從另個(gè)層面上,我著實(shí)地感覺到,那兩堆厚厚的土層下面,分明深涵著故鄉(xiāng)關(guān)屯的一些歷史和人文的東西;抓一把那里的泥土,會(huì)滲出故鄉(xiāng)古老的文化成份;或者說(shuō),老戲臺(tái)的傳說(shuō),是故鄉(xiāng)人對(duì)關(guān)屯往事的懷戀情結(jié)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