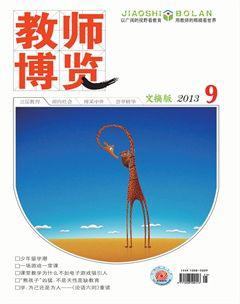學:為己還是為人——《論語六則》重讀
陳國安
“《論語》為中國的社會、政治和倫理的主要思想提供了基礎。它成為后世的圣書,要求學生必須背誦,因此它的許多段落成為格言,甚至沒有文化的農民也會不知不覺地引用。”這是一位美國人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中對《論語》的評述。中國人的《論語》類乎歐洲人的《圣經》,不讀《圣經》無法理解歐洲,同樣,不讀《論語》也無法理解中國。
《論語》中多數話是孔子所說,由他的學生記錄了下來的,因時間久遠,很多話的語境已非常模糊以致無從還原了。即便如此,真正的孔子還是活在《論語》里。《論語》里的孔子一開腔便是“學而時習之”,也許它不是孔子第一次上課說的第一句話,只是后來編《論語》的弟子們認為這是孔子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以此貫首,似有深意在焉。
孔子最凸顯的人格角色是教師,教師跟學生談得最多的應該就是學習。孔子時代學習風氣已經很不好了,“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王夫之《讀通鑒論》)所以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揚,為己者因心以會道。”(范曄《后漢書·桓榮傳論》)可見孔子時代的學者已經不是為了充盈自己而學習,而是希望通過學習獲得名利了。這在孔子看來實在不是件好事,而是世道墮落的標志,于是他大聲疾呼回到“古之學人”的境界中去。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要切當地用于生活,學問是為了解決問題的,學問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的,歸根到底,學問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學而不習,知識便永遠只是知識,而不能成為解決生活問題的力量,知識成為第一生產力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習。“習”繁體作“習”,本義是指雛鳥學飛,是個會意字。雛鳥學飛是為了發揮天賦和解決生存問題,只有這樣的“習”,“學”才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的“學”和“習”才能真正“為己”,只有“為己”的學習才能真正成為內心的愉悅。“求知心”是孔子理想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成分,也是人生的起點。一個人有怎么樣的“求知心”,便會有怎么樣的人生,它在生活中形成張力會給人帶來內心的愉悅——這種愉悅不是喊出來的快感,而是會心的、靜默的“樂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說的是純真的“童心”,這是孔子理想的人格中另一種重要成分,也是人生的過程。“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苦旅”,一個人孤獨地走,固然有種無法言喻的美,但在孔子看來,這不是完美,完美的人生應有人相伴,甚或有人陪著彼此凝望,這需要有一顆純真的童心作為基礎。后世有詩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只要有朋友存問,天涯再遠也近若相鄰,更何況朋友上門來了,從遠方來探望自己了!一個“樂”字,寫盡了孔子那種童真之心:“樂”的繁體“樂”也是個會意字,指一組石鼓掛在鼓架(虡)上被敲響,“呯呯砰砰”,就像孔子聽到老朋友喊門忙不迭跑將出來的腳步聲。這一句話中沒有“而”,節奏簡明,極其歡快!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一句的“而”落在了后面,孔子強調的是“不慍”。不高興的事情常常會發生,但是若是因為別人不知道你就不高興了,不免陷入“別人的泥潭”。你首先是為自己活的,你的學習也是為你自己的,沒有人知道你,沒有人知道因為學習而改變之后的你,甚至作為你的你始終都沒人知道,你也不會不高興,這才是“君子心”,有了“君子心”的人才可能是君子。由此看來,孔子也認為,一般來說,君子是孤獨的。“君子心”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最后一種成分,這指的是人生的終極。一個人撒手人寰時,若別人評價他是個“君子”,一生無怨尤,并由此而喚醒他人走向“君子”之路,君子也許就不再孤獨了——但同時,君子的人生也就此終結。
孔子一開篇說出的三種理想的人生構成,或者說,編《論語》的孔門弟子一開始便將孔子對人生的三重構想赫然宣出,大概覺得只有這三句話才足以鎮得住整本一萬六千字不到的《論語》吧。不過,一如吉川幸次郎所欣賞出的那樣:從“非常穩健”到“節奏一變”,“高興得似乎雀躍歡呼”,最后“韻律繼續延伸”,“實在是非常之美的文章”!孔子在《論語》里閃亮登場的三句話真是精彩紛呈!
從“求知心”啟程,讓純真的“童心”貫穿行程,以“君子心”告別人生的旅程。“求知心”與“童心”都在誘發著人們的好奇心,每一天的人生都是新的,所謂“日日新”,日子如此,知識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里孔子說了一個教師標準:在知識觀上具有“獨立”價值。這是“為己”的教師,是“古之學人”,為愛知識而求知,因愛教育而從教,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 “師”!
教師要承擔著“故知”傳承的職責,同時,也要完成生發“新知”的使命。新知源于故知。故知存在于昨天的生活,在今天的生活中“習”之“溫”之,于一個具體的人來說,這本身便是一種“新”了。但這到底還沒有完全脫離“故知”而成為今天的“新知”,只有在今天的生活中“求知心”又拓開了“新境”,“活潑潑”地改變了今天的日子,“新知”才得以誕生。
無論解釋為“既要故知又要新知”還是解釋為“由故知而成新知”,“溫故而知新”都在告誡太陽底下最光輝的靈魂工程師們:“只有故知而無新知”的老師,是“為人”之師,充其量算是“經師”而已,“知故知新”“由故而新”才稱得上“人師”。為“人師”,必須有“為己”之學,“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陳寅恪)無非說的也是這個道理。為“人師”,才能援引“故知”來作為孩子今天生活的力量,并在今天的生活中“溫”“習”它們而醞釀出“新知”,放入孩子人生前進的行囊。
不只教“知識”,而且教“為人”,唯有“為己”的老師才能承當,因為唯有獨立的人才能教得出獨立的人。獨立的人一定是獨立的學習過程培養出來的。“獨立的學習過程”的標準是:在學習中學會思考,在思考中學會學習,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一邊思考一邊學習。二者缺一不可,偏頗不得。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考與學習一旦分離便會有迷惘和疑惑的樣子,學習者就成了一個“容器”或一匹“野馬”。若將“罔”“殆”視為互文,這樣“學”“思”背離的苦痛就更為酷烈了。無論是迷惘還是疑惑,其實都是非獨立人的樣子。獨立的人也許會犯錯誤,但不會疑惑、迷惘,所以獨立的人犯了錯誤,對其作出修正往往會成就一種人生的美麗,而因為迷惘和疑惑所犯的錯誤,常常會使人生陷入一個接一個“別人的泥潭”。破除這一迷障,還是孔子說的“為己”之學的道理管用:學習若為了自己,便不會不思考;思考若是自己思考,便不會不學習。
學習和思考結合在了一起就足夠了嗎?學與思結合就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習者了嗎?孔子認為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問。學不僅與思結合,還要與問結合。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勤學好問曰文。”(《逸周書·謚法》)“文”人是相對于“野”人而言的,只有自己成“文”人,人身上的知識才會散發出“人性”的熠熠光輝。“好學”,是打心底萌生的“求知欲”,不斷地敏捷地讓自己處于一種“好學”的狀態,這樣的人才可能走得遠。“敏而好學”也許尚存有一些功利目的,若能“不恥下問”,那才是真的以知識為知識,“為人”而學的可能性便少了很多。不以下問為恥,不是沒有“恥感”,而是突破“為人”的“恥感”。“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莊子的“任情”與孔子的“多情”在這里交匯了。
只有把知識當做充盈自己靈魂的“糧食”,那一個“糧食店”(南懷瑾的比喻)的意義才是孔子的,哪怕是一味藥,也是一種糧食了,那一個“藥店”的意義才是莊子的。無論是吃飯還是吃藥,都是為了自己的,那才是自己的人生。所以把“不恥下問”看作“糧食”或是“藥劑”都是 “為己”之成“文”而進行的一種修煉。
孔子是一位“為己”成“文”的人,但不是單純的文人,“為己”成“文”之后便“為己”成“師”,這大概是孔子的人生軌跡最簡單的描述了吧。孔子在這一過程中最為得意的也許是:
“默而知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默識,不滿足地學,不疲倦地以故知新知教誨別人(主要是學生吧),這三點是孔子很自信的可稱之處。有人說這里孔子太謙虛了吧,其實自信的意思用謙虛的語氣說出來時很有話語的魅力!
孔子說的很謙虛的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內心已經把自己定位為“為己”之“人師”的孔子,仍然時時準備當學生,從“善”而改“不善”。孔子這里沒有闡明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或者評判標準一如他在《論語》里所說的那些“善”與“不善”、“賢”與“不賢”,不過無論如何選擇或改正,“我師”這個“我”是關鍵!一切都是從自己出發的,這才是“為己”而從師。
“為人”而“喪己”不是本真的狀態(張世英《“為己”與“為人”》),“為己”而“保真”才是自己的人生。《論語》總是將最深蘊的人生用最簡單的話語表述出來,所以識字的中國人應該每年讀一遍《論語》,常讀常新。
■責編:袁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