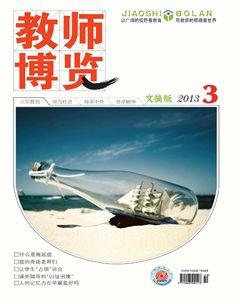歐洲留學:獨特的“小眾口味”
陳舊
18世紀之前的英國人,不在26歲之前到歐洲周游數年,沒去烏菲茲與西斯廷臨摹過文藝復興名作,沒去巴黎或維也納的沙龍里把個貴婦,沒在羅馬或尼斯的勾欄里惹一身梅毒,此生算白過了。
如今,每逢夏季,北至瑞典,南至希臘,西至英國,東至波蘭,依然游蕩著來自美洲、亞洲或非洲的學子們。他們一雙夾腳人字拖,背NorthFace大背囊,拿一張Eurorail火車通票,住火車或YHA通鋪,便能自由穿梭于邊界消失的歐洲。他們在哥本哈根Christania與無政府主義者調情,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里抽兩口大麻,在英國Glastonbury音樂節撒野,在巴黎貝爾拉雪茲Jim Morrison墓前跳舞,在西班牙Ibiza島喝到爛醉,在希臘Mykonos沙灘上裸奔。經歷過這樣放浪而迷醉的青春之后,他們回到各自所在,從Young Person(歐洲慣例,26歲以下為Young Person,出入博物館與乘坐交通工具有折扣)成長為Adult,開始西裝革履,娶妻生子,夾緊尾巴做人。
如今,幾乎歐洲每一所大學,都找得到中國人身影。中國人赴歐留學曾有三段高潮:第一段容閎發起的官派留學生,包括赴歐留學的船政留學生。第二段,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主力為赴歐赴美。第三段,改革開放至今,赴美者最多,赴歐者亦為數不少。
如果說一代、二代留學生還是為求知、為救國,如今留學者多不為學。可以游學、閑學、玩學或休學,但學統統排在第二位。另一種陳詞濫調是為“開闊眼界”,某些人到歐洲小城待久了,沾染了中、歐的雙重土氣,中不中,西不西,洋倒不洋,土倒更土。若真為開闊眼界,你應去中國、印度。
官二代去英國,藝術家去法國,裝逼犯去比利時,吃貨去意大利,精分去德國。小說《圍城》里,方鴻漸出洋留學,四年中換了三所大學,分別在倫敦、巴黎和柏林,最后卻拿回美國“克萊登大學”文憑。如果真有這樣的大學,我倒真想一讀。
有錢人喜歡去英國(代表人物:徐志摩、錢鐘書)
最出名的留英生非徐志摩莫屬,他1921年赴劍橋。他的《再別康橋》讓不少人心醉神迷,也讓更多人大呼上當。不過徐情圣濫情的生活方式與表達方式,都是典型法式的,也是最讓英國人深惡痛絕的。
最得英國人神韻的是錢鐘書。他1935年就讀于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英文系。關于他的機智、刻薄,馮友蘭之女宗璞曾作小說《東藏記》挖苦,其中的主人公尤甲仁、姚秋爾夫婦,家住“刻薄巷1號”,“他們以刻薄人取樂,他們這樣做時,只是覺得自己異常聰明,凌駕于凡人之上,不免飄飄然,而毫不考慮別人受的傷害,若對方沒有得到信息,還要設法傳遞過去。射獵必須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閉門說說會令趣味大減”。后人考證其即指錢鐘書、楊絳夫婦。
徐、錢尚算人中龍鳳,數十年之后,留英生因其門檻低(不用再學第二門語言)、學制短(本科三年、碩士一年)、收費貴(適合炫富)而成為官二代、富二代樂園。
如今,中國大陸學生已逐漸成為英國除歐盟外第二大留學群體。20世紀90年代初,全英的中國大陸學生不過兩三千人。進入新千年以來,中國學生劇增,2003-2004年,在英高校注冊的中國學生已增至4.5萬人。據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教育處估計,若把研究生、本科生、語言生和中學生等都算在內,目前中國留英在校生總數至少應超過9萬人。目前在英國約100所正規大學中,幾乎都可看到中國人身影。據英國文化委員會最新預測,未來十年,中國赴英留學人數將保持年均15%的增長率,將繼續成為英國最大國際學生來源國。
不僅如此,中國學生的專業分布也高度集中:據《華商報》統計資料,就讀管理專業的中國學生達52%,財經類占23%,其他學科(電子工程、材料等)只占25%。
關于留英學生最常見的詬病,是總有些人揮金如土。
藝術家去法國(代表人物:趙無極)
錢鐘書離開英國后曾轉赴法國,但迅速地厭倦了巴黎。在他看來,巴黎保持了一貫的熱熱鬧鬧和亂亂烘烘,也就是那種“美妙的雜亂”(beaudesordre)和“浪漫的混亂”(romantischeverwirrung),人們在抱怨中享受自由。錢鐘書不喜歡法國人的行為方式、說話方式,甚至吃飯時間過長,也讓他心煩意亂。
但藝術家就愛這樣的生活。趙無極1948年留學巴黎,自此定居于法國。他曾說過:“我必須說,隨著我思想的深入,我逐漸重新發現了中國。或許悖謬的是,這種深遠本原的歸復,應該歸功于巴黎。”
從2000年開始,法國這個文化大國逐漸被更多中國留學生所關注,很大原因是法國留學的經濟性。法國國立大學本科每年注冊費和保險約為360歐元(約3200元人民幣),比國內高校都便宜。
據中國駐法大使館教育處信息,大部分中國留法學生是自費,管理和商業等專業依舊熱門,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文學、藝術等文科專業,服裝和設計也吸引了不少中國學生。除了正規學院,不少人到法國修讀短期課程:如花半個月修讀紅酒班,或花一周學做馬卡龍。
但法國文憑最大的問題仍是辨識度不高。最近電視節目《非你莫屬》鬧出的“BAC+5風波”即為一例。
拿德國學位難如登天(代表人物:陳寅恪、季羨林)
國學大師陳寅恪13歲起就負笈西游,到過德國、日本、瑞士、法國及美國,其中留學德國時間最長,先后去了兩次,共計5年。德國學者特有的對精確性的追求與對徹底性的偏愛,深深地影響了陳寅恪。被這種“德國的影響”影響的還有后繼者季羨林。
德國大學的注冊費便宜,只收取100歐元左右(約900元人民幣),廉價的入學費用、先進的科技水平、傳統的歐洲文明和高水平的福利政策,是德國最吸引人的優勢。從2001年起,中國學生開始形成一個留學德國的小高潮,并在2007年形成一個高峰。據統計,目前生活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總人數在30000萬人左右。
但讀過德國大學的人都說,學德語難,拿德國學位更難如登天。
德國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學位體制與歐美其他國家迥然不同,學位無學士碩士之分,學生們需要一次性面臨五六年甚至更長的學習時間,淘汰率非常高;德國大學里更沒有年級和班級概念,只有學期數和專業區分。學校開放所有課程,學生需要自己安排學習進度。只要完成專業內的必修課程和規定數量的選修課程,以及實驗、實習、報告、論文等內容就可畢業。
更令中國學生崩潰的是,德國大學連課本都沒有。教授往往只提供自編講義或提綱,有些課程甚至只有教授板書作為一手資料。習慣了“填鴨式”被動教學的中國學生,其手足無措之窘,可想而知。
難怪有人感嘆,要么神經病才去德國讀書,要么去德國讀成了精神病。
吃貨都去意大利
雖然貝盧斯科尼很不靠譜,意大利政府又瀕臨破產,但意大利政府至今都把教育作為非營利產業,對所有學生實行學費全免,留學意大利的花費僅為去英、美、澳、加等國費用的1/3左右。
意大利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其他學校在歐洲也屬一流水平。2005年7月,意大利與中國教育部簽訂協議互相承認學歷,之后越來越多中國人來到意大利。意大利本科學制3年,碩士2年,博士生為3年或更長。意大利排名較靠前專業包括設計類、建筑類、美學和音樂類專業等。另一個好消息是,去意大利的中國留學生,很少被拒簽。
另一個吸引中國人的好處是意大利無處不在的美食。大自然賜予的物產如此豐富,以至于在意大利你很難吃到一頓差勁的飯菜。多少世紀前,意大利廚師就已懂得不要太“改善”食物。只要給意大利人一些新鮮橄欖油,一只鮮檸檬,一籃子番茄,一點大蒜、胡椒,幾片羅勒,以及一塊巴爾馬干酪,他們就能做出使你久久難忘的可口面點。難怪連法國人都說,食在意大利。
(摘自《新聞選刊》2012年第8期)
責編:熊春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