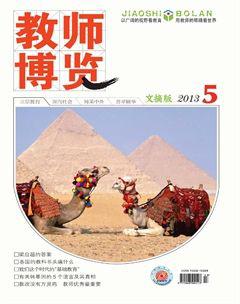我們這個時代的“基礎教育”
孤獨,不是身邊沒有人,而是因為沒有共同語言,再具體一點說,就是沒有了一個可共享、可分享的共同世界。沒有了這樣一個可共享、可分享的共同世界,隨之而來的就是虛無主義的問題,就是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就是功利性、實用性、目的性需求對我們的支配。一個工具化了的世界已然形成,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之中——這大約可以假定為我們的一個基本共識,這也是教育界所面臨的一個共同背景。
現在的問題不是要發展出一套規范性的教育理論、制定完善的幾年計劃,也不是如何編寫教材,如何因人施教。這些東西,早就不是問題了。我們應該意識到教育自身的悖論或困境。一個是馬克思所說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教育者先受的教育來自哪里?一層一層往上推,又涉及到軸心時代所開創出來的某種超驗意識。再一個就是教育永遠是國家的事,如何在此背景下尊重并發展個人的尊嚴與自由?在喬爾·斯普林格(Joel Spring)所著的《腦中之輪:教育哲學導論》中,他告訴我們教育就是給人的大腦裝輪子,離開了被裝進去的輪子,我們幾乎就不會思考,不會說話。這是與馬克思同時代而且同屬“青年黑格爾派”的施蒂納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至少提醒我們:看看我們的孩子,從那么小就說著與大人一樣的話,千人一面,眾口一聲。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我們給他們幼小的心靈中裝進了這樣的輪子。我們自己的輪子又是怎么裝進去的?這是一個需要反省的問題。只有在反省的前提下,一方面,我們知道教育總是免不了要給人的大腦“裝輪子”,另一方面就會想到不妨多裝幾套輪子,讓孩子們有所思考,有所選擇。這也是我們提倡多看書、多聽不同意見的一個根本緣由。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基礎教育。
我們現在有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基礎教育的不同說法。
人文教育涉及人生的意義問題,也就是傳統的文、史、哲。黑格爾的精神哲學中所講的藝術、宗教、哲學,總之,涉及到前面所談到的超驗存在的問題,因為它與我們是否能擁有一個可共享、可分享的公共世界有關;通識教育是讓我們從學科分化、分類的局限中掙脫出來。要跨學科,不但跨文、理之間的學科之分,還要跨越藝術、宗教、哲學的界限。前面說了,現代性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分化”。我們如何才能從不斷“分化”著的專業領域里跳出來,視野開闊一些,說到底,還是一個自由的問題。
自由幾乎是一個不可定義的問題,就如時間、世界、經絡一樣;但只要我們意識到它的不可定義,轉而通過描述、敘事的方式來呈現它,我們就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自由。自由與未來有關,也就是與可能性有關。沒有了未來,沒有了可能性,也就沒有了自由。自由是一種超出我們預料之外的可能性,它與一切可預期、與一切成型或定型了的模式相反,因為正是在這樣那樣的“相反”中,自由才成為了人的本質特征。
當然,這里所說的自由不是任性,不是故意對著干。關于這一點,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導言》中,當他告訴我們“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規定,正如重量是物體的根本規定一樣”時,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人都有意志,但人并不都隨意胡來。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也好,人權也好,都是道德概念。如果沒有自由,也就談不上承擔、責任、義務,談不上對未來的想象,當然也就沒有了精神上的冒險。而這些,正是哲學所要討論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教育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我們通常所犯的一個錯誤(或者不要理解為錯誤,最好理解為偏向)就是把力氣花費在搞清楚正義、人權、責任、義務的概念理解上;而且認為制度或法制的設立才是保證。這是對的,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的教育對象是孩子,我們就應該努力引導著他們離開得失、利益、結果的偏向,而是更多地從過程與責任的角度,從現實生活中的“可行性”,從是否可以立即糾正的一些非常明顯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利于環境衛生”、“不尊重別人”中去培養功德意識。這并不難,只要有很淺顯的道理,事情就能說得清清楚楚。因為它確實涉及到一種生活方式的養成。
所以,我理解的基礎教育,這個基礎,不是相對于學科,相對于以后的學業進步而言的基礎,而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共同的基礎,這就是自由、尊嚴、權利與人格上的被承認。如果作為個人,把這一點肯定下來,那么,當我們談到外在世界,談到人與人的關系,談到一個公共世界的可能性時,我們也就知道了這樣一個世界其實永遠處于我們自由創造的過程之中。它在彼岸,但又與此岸有關,就如它是我的世界,但又永遠離不了他人的存在、他人的參與一樣。這恐怕是所有教育者在心里都應該努力去想透徹的一個問題。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僅供參考而已。
(本文系作者在同濟大學的講演。陳家琪,同濟大學政治哲學與法哲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德國哲學》編委。長期從事政治哲學與法哲學、德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等領域的研究。節選自2013年1月14日《文匯報》)
責編: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