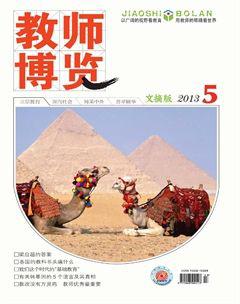小學老師
林白
李洪波老師
認識李洪波老師的時候,我十一歲,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他是我的科任老師,教算術。在小學里,四五年級就是高年級了,教高年級的都是業(yè)務骨干,洪波老師顯然教得很出色,他的教學進度總是比其他各班快。記得有一個學期竟比別班快了許多,他教完本學期那冊教材后又給我們復習了一遍,期考的日子仍遠未到來。我們都有些不耐煩了。學校便允許:他在他的課時里給我們講些關于防止核戰(zhàn)爭的常識,他邊說邊在黑板上畫,搞得全班都很興奮,一時間,人人滿嘴都是“白光”“沖擊波”等新鮮名詞。啊,我們班在全年級真是鶴立雞群呢!
洪波老師又能畫畫,若是圖畫老師生病或請假,便由他替上。他拿了彩色粉筆就到課堂上來了。他剛在門口出現(xiàn),大家就驚呼:“換算術課了?!”李老師微笑著說:“圖畫課。”李老師這一笑一答,使我們感到某種心領神會的親切。大家便都安靜地準備好鉛筆和蠟筆,抬頭看時,黑板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好看的圖畫:房屋、樹木和太陽。李老師刷刷幾下上了顏色,房屋和樹木頓時都有了生氣,亮晶晶地在我們面前晃動。
洪波老師有很好的嗓子,能唱很好聽的歌。記得當時上映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里面有一首歌很好聽,但我們都不會唱。有一天清晨上學,聽見走廊里有人在唱“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我們在春天里加入游擊隊……不管風吹雨打烏云滿天,我們歌唱我們戰(zhàn)斗……”是李老師十分好聽的男聲,渾厚悅耳,我們幾個女生站著聽了好一會。
多才多藝的李洪波老師在我五年級的時候擔任了校文藝宣傳隊的文藝老師。當時我是宣傳隊的隊員,排的節(jié)目除了樣板戲,還有李老師編的小戲。劇本發(fā)下來,第一行總是:地點:桂南某山區(qū)。記憶中李老師還會吹拉彈唱敲木魚,若是樂隊缺了人,他可以臨時補上。
小時候就知道李老師是個無所不能的人,卻偏偏不知道他會寫詩、寫小說。直到八十年代末,當時我在電影制片廠當文學編輯,有一次回家鄉(xiāng)探望母親,縣里正開文代會,便也應邀參加。在會上我十分吃驚地看到自小學畢業(yè)后一直沒有聯(lián)系的李洪波老師,這才知道,洪波老師1 9歲就在很有影響的《羊城晚報》副刊發(fā)表作品了。多年來他一直業(yè)余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大量詩歌、小說和散文,成績斐然。看上去李老師還是那樣年輕,文人氣十足,好像十幾年的光陰一點都沒有流過去。
之后就不斷聽到洪波老師的消息:調(diào)到文聯(lián)了,在《人民文學》上發(fā)表作品了,出版第一本詩集了,等等。后來我到了北京,在一家報紙當副刊編輯,洪波老師給我寄來他的作品,我這才第一次看到他的詩作。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他的詩并不像一個教了二十多年算術的人寫出的,充滿了才氣和靈性,飽含對生活的感情,語言樸素,既有生機,又有一種靜態(tài)的美,雖平白如話,卻絕不寡淡。
不久前我因繼父病危,回鄉(xiāng)探望,看到家鄉(xiāng)經(jīng)商大潮洶涌,鋪天蓋地,省會、地區(qū)、縣等各級舊日文友紛紛經(jīng)商下了海。運氣好的甚至買了私家車。文壇一時有凋零之感。但見洪波老師仍一如往日,依然平靜、從容、孜孜不倦地沉浸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交談起來,也并不眼紅人家發(fā)了財。
覺得頗為不易,尤其是在基層。
洪波老師的第二本詩集《泥捏的戀人》將由國家級的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作為后生晚輩,謹以此文表示祝賀。
龐桂珍老師
我八歲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曾經(jīng)餓倒在課堂上。上課剛剛上到第二節(jié),饑餓的燒灼感就開始隱約出現(xiàn),它們以極快的速度滋生和集結(jié),每一分子,一手舉著長矛,一手舉著火把,在我的身體里步步緊逼,它們一次次把我的唾液趕到我的喉嚨,我一次次地把它們咽下去以平息腹中彌天的燒灼。饑餓的怒火非但沒有緩解,反而變本加厲。在這場力量懸殊的拉鋸戰(zhàn)中我很快敗下陣來。我全身的冷汗奔涌而出,眼睛再也看不見黑板上的字,也聽不見老師的聲音了。我全部的感官只提供同一個感覺:腹部里有一個越來越燙越滾越大的火球,它正在擠壓我全身的水分和力氣,它已經(jīng)燒到了我的心,快要燒到我的臉和我的頭了。這是一個巨大的唯一的感覺,遮天蔽日,如果我不逃脫,我將死于這個火球。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同時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沒有任何能力熄滅這個兇猛的火球,我已經(jīng)精疲力竭了。
我全身發(fā)軟地癱倒在書桌上,我知道我再也不行了。但酷刑還在繼續(xù),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結(jié)束這一切,什么時候才能結(jié)束這一切。后來我絕望地哭了起來。當我回憶這饑餓的哭泣時,我已經(jīng)無法弄清是什么引起了當時正在上課的老師的注意,是哭泣還是暈倒,我想不起來哭泣的聲音,一個饑餓至極的孩子,趴倒在書桌上,她哭泣的聲音像游絲般微弱,有誰會聽到這個聲音呢?
我模糊地感到有人在走近我,溫熱而干燥的 手摸了摸我的額頭,又摸了摸我的手。她說:“你是餓的,快去買一碗米粉吃就好了。”她從口袋里拿出一角錢和二兩糧票放到我手上,說:“你現(xiàn)在就去,不要等下課了。”
我什么都沒說,握著老師給我的一角錢和二兩糧票就往街上跑。當時的一角錢是小鎮(zhèn)許多家庭一天的菜金,兩分錢能買到一斤空心菜,五分錢能買到一斤咸蘿卜,四分錢就能買到一碗素的湯米粉。我握著一角錢,就像握著了神話中的某種寶物,體內(nèi)那只燒灼的火球奇跡般地消失了,我的眼睛和腳重新有了感覺。我一溜煙走出校門口,朝著街上最近的一家米粉店飛奔而去。我交上錢和糧票,坐凳子上,既興奮又新鮮。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吃東西,母親在醫(yī)院工作,她在衛(wèi)生方面要求嚴格,任何時候都不允許在街上亂吃東西。“細菌”這個詞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被猙獰地灌輸進了腦子里。我看見條狀潔白的米粉被放進了一口大鍋,濃白的蒸汽在升騰,時疏時密,婀娜而澎湃。米的香味從這片白色的氣體中散發(fā)出來,猶如太陽的光芒從云層中透出。氣味的光芒越來越燦爛,它們在濃白的水汽中間跳蕩、閃爍,照亮了整個店鋪,每個人的臉上都被這特殊的光亮所照耀,臉上一副滿足的神情。蒸汽風起云涌,氣象萬千,我們的太陽就要出來了!
圍著布圍裙的人將一只光滑的竹笊籬伸進大鍋里,蒸汽的云霧從正中被破開,竹笊籬水光閃閃開始左右晃動,沸騰的湯如大花般怒放。米粉,我們饑餓之軀的太陽,在竹笊籬的托舉下,從云霧的中央,從沸騰的湯中迅速上升,它呼地一下就升起來了,呼地一下倒在了大碗里,然后它飄動著白汽,如同翕動著柔軟的翅膀,明眸皓齒,儀態(tài)萬方地來到我面前。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未見到、也再沒有見過如此美好的食物,它的顏色和香味在時間中聚集、堆積,成為堅硬的晶體,隱藏在我的味蕾和呼吸中。它的光芒永不落。
綴結(jié)著所有這一切的人,是我的老師龐桂珍,這是一個真實的名字,這個名字珍貴而樸素,多年來我把它珍藏在心里,多年來我等待一個認真的場合把它鄭重地說出,猶如等待一個堅硬而平坦的臺地,語言的青草繁茂地生長,芬芳而濕潤,而我默念著我老師的名字,把它鄭重地書寫在這里。這是我多年來的心愿,我愿意所有與我的文字相遇的人,也同樣與她相遇,被她慈愛的眼光所籠罩。
(摘自《美文》2012年第10期)
責編: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