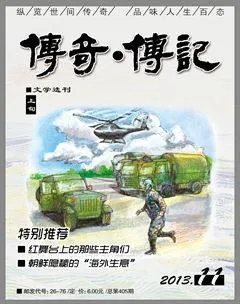飛來的好運
吳淵是一家裝潢公司的老工人,這家公司負責裝修的“燕鮑一品”酒樓下水道出了問題,老板派他和幾個工友過來維修。干完活已經是晚上九點多,吳淵拎著在后廚討的一些剩菜,不想正跟一個醉醺醺的胖子撞到了一起,手里的剩菜撒了一地。胖子一個趔趄,回手一個大耳光重重地扇在吳淵的臉上,他猝不及防摔了一個大跟頭。
胖子暴跳如雷,嚷嚷著要討說法。樓層經理一溜小跑過來連連賠著不是,還呵斥吳淵,讓他趕緊掏錢賠償。這時吳淵的工友聽到吵嚷也趕到了,圍上前跟胖子述說著吳淵家里的窘狀,求他網開一面少要點損失費。
聽到吳淵的名字,胖子愣了一下,再次揪住他的衣領,直勾勾盯著他。
胖子似乎酒醒了,呆呆地說:“你……叫吳淵?78屆三中畢業的?”吳淵一愣,心里升起了一絲希望,趕緊使勁點頭。胖子的手松開了,使勁揉眼睛晃腦袋,口齒也不伶俐起來:“小……小從文?天啊,我……我是李大元啊!是我呀班長!”
吳淵慢慢挺直了腰。“小從文”,幾十年沒聽見有人喊他的綽號了。從眼前這張近在咫尺的肥臉上,他找到了三十年前那張娃娃臉的模子,沒錯,這個盛氣凌人的胖子正是高中同學李大元。三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飽受生活磨難的吳淵看上去已經是個老年人了,難怪李大元一時半會認不出。
忐忑不安的經理和工友意識到危機解除,都長長松了口氣。
要說這酒可真是好東西,恰到好處地蓋住了胖子李大元的臉,他擦著汗非要拉吳淵去包間喝酒。原來巧得很,今天正是他們老三班的同學在聚會。吳淵再不愿見同學,也由不得自己了。
打開房門那一刻,吳淵腦海里浮現出一個人——大觀園里的劉姥姥。那一瞬間他產生了強烈的悔意,如果可以選擇,他寧愿賠那件價值不菲的T恤,也不愿穿著臟兮兮的工作服,紅腫著半邊臉,萬分狼狽地跟老同學們見面。
同學聚會一向是成功者樂此不疲的游戲,主旨無非是男生們夸官斗富,女生們比美比老公,所以這豪華大包房里到場的三班同學,非富即貴。其中以李大元最為顯赫,已經是省里的廳級官員了。
大家對突然闖入的老班長熱情有加,一杯又一杯紅的白的灌下肚,所有人都心潮起伏,回憶起當年集體逃學去偷農戶的黃瓜,半夜翻墻出去看露天電影,李大元考試不及格被班主任蔡老師暴打……提到班主任,有人居然背誦出他寫的詩歌,不過這詩人總是慘遭家暴,動不動包著半邊臉來上課……酒越喝越多,情越嘮越稠,吳淵的臉還在隱隱作疼,心里一陣酸,一陣苦。
眼前一張張承載了過度熱情和酒精的臉恍惚起來,吳淵的腦子開始發暈,嘴也沒了把門的,含含混混嘮叨著:我?我是班上唯一住在大山里的學生……窮啊,打小沒爹,老娘還是一條腿,三十多歲才混上媳婦……媳婦?人是挺好,就是她家族有遺傳病,好好的人到了二十多歲胳膊腿兒就不聽使喚,不到三十就都沒了,要不人家也不能嫁給我……后來,后來她給我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她先發病就死了……孩子們?開始還好,腦子是真聰明,我尋思是老天可憐,孩子們遺傳了我,能躲過去這一劫,就帶他們來縣城租房打工上學,哪想到……現在倆孩子都在床上癱著,吃飯都得我老娘一口口地喂……
多了,真是喝多了,多到舌頭根本不聽大腦的控制。似乎后來他還號啕大哭,哭訴當年的學習一點不比在座各位差,可就是造化弄人高考落了榜,這些年,苦哇……寫稿?對,當年在校文學社,我還是社長,蔡老師一直指點我寫作,夸我是“小沈從文”,可這些年,苦得我啊,詩情畫意風花雪月早拌著黃連和淚吞了……
吳淵醒來時天已經大亮,老娘和兩個身子軟如面條的兒子六只眼睛惶恐地望著他。他慢慢坐起來,只覺得頭疼得要裂開一樣。然后他的眼睛就瞪圓了,嘴巴也大張著合不攏——身邊的炕上,有好多嶄新的百元大鈔!
兒子們含混不清地搶著告訴他,昨晚是一輛小汽車把他送回來的,他已經醉得人事不知。車走以后大家才發現,吳淵的衣袋里,懷里,塞滿了鈔票。
吳淵哆嗦著捧起鈔票,大略清點一下,居然有兩萬多塊!他趕緊給李大元打電話,問起這筆錢的來歷,李大元打著哈哈說是老同學的一點心意,也別細追問了。吳淵不停地用袖子抹著眼淚,這時他才確信,昨晚誤打誤撞闖進這個聚會,也許不是壞事。他很想跟李大元多說幾句感恩的話,可對方的口吻雖然和藹,卻多了種說不出的疏遠隔膜,吳淵也就知趣地結束了通話。
吳淵在家歇了一天,轉過天一大早來到單位上班,平時總拉著長臉像欠了他幾世錢的經理居然笑容可掬地找他了:“吳叔,你是咱這兒的老工人了,公司發展到今天的規模,你老功不可沒!公司管理層經過研究討論,決定提你當帶班班長!薪水漲到四千,全脫產呦!”
面對工友們羨慕得發紅的眼睛,吳淵一頭霧水。就是這個長臉經理,昨天不是還嚷嚷要辭退他嗎?吳淵硬著頭皮撥通李大元的電話,詢問是不是他從中幫了忙。李大元的聲音冷漠而不耐煩,說自己絕對沒安排,馬上要去跟省長匯報工作,不多聊。
聽筒里傳來電話掛斷的聲音,吳淵猶豫了一下果斷地刪除了這個號碼,他知道,自己和李大元之間的鴻溝,遠比當年魯迅和閏土的要深得多。
幾天以后,好幾家省內大報記者涌到吳家采訪。很快,各大報大篇幅發文呼吁有關醫院伸出援手幫幫這可憐的一家人。吳淵帶著兒子們輾轉了幾家醫院,病情卻絲毫不見起色,一家福利機構伸出了援手,愿意免費接納孩子們。
好運接踵飛來。這一天吳淵正在工地忙碌,一個騎著摩托車的郵差高喊他的名字,說有他的匯款單,手里還舉著一本雜志!吳淵連連說他找錯了人,可郵遞員一口咬定是他的沒錯。
吳淵疑惑地打開雜志,見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兩萬多字的報告文學,署名正是吳淵。他立刻跟雜志社聯系,聲明這文章絕不是自己撰寫。可那家大雜志社的編輯斬釘截鐵地說,投稿的就是這個名字通聯,絕不會錯。
吳淵對著飛來的兩千多塊稿費單發了幾天呆,那篇文章當然讀得爛熟。這一天和煦的陽光照射進出租屋的窗子,照射在他花白的頭發上,他心里豁朗一聲仿佛有一扇窗被推開了!他對著那篇報告文學大聲叫著:這東西有什么啊?我也寫得出!
這飛來的好運激活了吳淵沉睡多年的文學細胞,文采如同地下的巖漿,呼嘯著噴涌而出,大半生的苦難也翻轉為巨大的財富,他忘我地投入到文字創作中。每個月都有匯款單從各地雪片一樣飛來,小說、故事、劇本,應有盡有,只不過一年多以后,他收獲的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勞動果實了。“民工寫手”、“農民作家”,一個個頭銜紛至沓來讓他應接不暇。
兩年以后,吳淵原創的一個地方小戲獲了省里的獎,縣文化局戲劇創編室主動向他拋出了橄欖枝——在沒有花費一塊錢好處費的情況下,吳淵被作為特殊人才,由縣長特批,特招進縣文化局任職專業創編員,公務員編制。
帶著老娘搬進單位安排的適用房沒多久,兒子們先后離開了人世。喪事過后,他從悲痛中抬起了頭,撰寫了一篇長長的散文,他要表達的情愫是感恩。工作落實以后,他曾經去省城找過幾次李大元,希望找出托起他的那只幕后巨手,可惜每一次李大元都有事,這個心愿也就始終沒有達成。
恩人無從找起,吳淵準備去拜訪文學之路的啟蒙恩師蔡老師,給自己的散文結一個精彩的尾巴。幾十年過去了,自己終于熬到了可以堂堂正正拜見恩師的一天。
蔡老師跟兒子住在鄰近的城市,聽說身體不太好。吳淵撥通了同學給他的號碼,聽到那個蒼老卻依稀熟悉的聲音,他激動得心跳都加速了,報上名以后迫不及待地提出見面,電話那邊的老人卻似乎被嚇住了,好半天才抖抖索索說了句:“你找錯人了!”電話就掛斷了。
吳淵對著電話發愣,再次撥過去對方已經關機!難道老師得了老年癡呆?他悔恨著聯系得太遲,打算周末過去看望老師。不料他臨行前再次撥打那個電話卻被告知,蔡老師突發腦溢血死了!而且他發病的日子就是自己打電話那一天!
蔡老師的墓址在一灣自然湖泊的附近,是他最有出息的學生李大元親自選的,據說是一處風水佳絕、福佑兒孫的寶地。李大元讀書時沒少挨蔡老師的板子,難得他對老師的回報之心。
那個周末,吳淵在蔡老師的墓前獻了一束花,對著照片上那張老態龍鐘的臉深深鞠了三個躬。
幾個月以后,參加同學聚會的吳淵得知,李大元被雙規。這年頭的官員出事沒什么稀奇,只是他落馬的原因比較特別。李大元為蔡老師挑中的墓地果然好風水,被所有方以高價一墓多賣。李大元仗勢強行下葬,被人實名舉報了,這一查就查出個大貪官!
李大元的落馬讓吳淵著實惴惴了一些日子。他一直懷疑幕后的貴人就是李大元,只怕自己這飯碗要端不住。好在一直風平浪靜,如果這事兒真的跟李大元無關,就是吳淵的成就起了決定性作用。
李大元被法警帶進法庭的時候眼神落在了坐在邊緣的吳淵身上,他一愣,隨即就漠然地轉過了頭。
審判員的第一句話就讓吳淵大吃一驚:被告李大元,曾用名吳淵……怎么李大元還曾用過跟自己相同的名?吳淵盯著李大元那張到老不改的娃娃臉,眼前似乎有一層云翳即將被撥開,他急切地想抓住什么,卻還是看不清楚。
經過了冗長煩悶的庭審程序,審判長宣布,判處李大元有期徒刑20年。
同學們惋惜地看著李大元。當他走到大家面前時,忽然轉過身子,撲通一聲跪在吳淵的面前。
所有人大吃一驚,吳淵趕緊彎腰去扶他,那一剎那腦子里豁然一亮,一件往事跳了出來。那些年曾有同學開玩笑說李大元是蔡老師的私生子,他們的娃娃臉一模一樣,而蔡老師也的確因為各種傳聞導致家庭失和。當然這都是小道消息,蔡老師管教李大元格外嚴厲倒是真的。這個念頭一閃即過,一句足以嚇住吳淵的話脫口而出,聲音大得讓他自己都吃驚:“李大元!當年,你比我學習差得遠!我考上了對不對?是蔡老師跟你合謀,讓你頂替我上了大學?對不對?”
李大元低垂著頭費力地站起身,良久才吐出兩個字:“報應!”
盯著那個夾在法警當中的臃腫背影,吳淵的臉抽搐成了一團,他捂著臉慢慢癱坐在地上:可憐的人,你早該想到的,如果不是這大貪官出于愧疚起了惻隱之心,槍手發文、請記者、特招公務員……命運哪會如此憐憫你?
福佑兒孫的風水寶地成為葬送李大元錦繡前程的墳墓,他已經一敗涂地,要查清當年的事并不難。可當事人已經死的死,倒的倒,查清了又怎么樣呢?吳淵一遍遍回味著這悲慘的大半生,終于發出一聲短促的苦笑,鼠標一點,刪除了那篇只差結尾的散文。
〔本刊責任編輯 吳 俊〕
〔原載《百花·懸念故事》總第3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