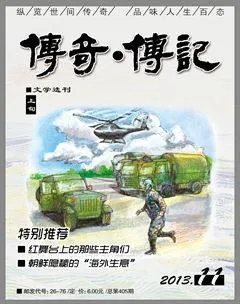中國遠征軍在印度集訓
1942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遠征以兵敗野人山為結局落下了帷幕,日軍席卷了整個東南亞,不但徹底斷絕了中國與外界的陸路交通線,還出兵滇西威脅我國的大后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在美軍的攻擊下節節敗退,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越來越明朗。此時,為履行中緬印戰區的作戰義務,國民政府決定擴充中國駐印軍的編制,而當務之急就是要解決部隊中官兵文化素質較低的現狀,由此,國民政府放開了學生從軍的限制,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動員國內的知識青年加入中國駐印軍,奔赴印度受訓。第二次遠征軍作戰就此拉開了序幕……
鄧某,男,民國15年生(1926),這個山東布匹商人的兒子,自打11歲起就被迫背井離鄉,1938年下半年跟隨家人輾轉來到戰時的陪都重慶,開始了新的生活。隨后,他考取了內遷的南開中學,開始了求學生涯……
1943年,17歲的小鄧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是繼續考大學,還是參軍抗戰?小鄧的兩難,主要是因為和家人出現了分歧。家里人都希望家中的這個獨子能老老實實地完成學業,而小鄧則具有那個時代年輕人普遍的熱血情懷,希望有一天能穿上軍裝,保家衛國……
遠征軍老兵鄧某通過自述,帶我們回顧了那段歲月。
十萬青年十萬軍
家里人自然是希望我考大學的,但我并不情愿,一是家里的經濟環境不太好,從山東老家搬家到重慶后,雖然父親一直還在維持著自己的小生意,但戰爭年代的蕭條以及人離鄉賤的事實都讓家里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供我讀完中學都非常勉強。更何況當時的校園也正經讀不了什么書,常常上課鈴剛一響,鬼子的飛機就準點來了,亂哄哄地疏散躲避,等空襲結束回到學校,大半天就過去了,還常常有老師因為迫不得已要安置家人,尋找跑散的同學,搞得連剩下半天的課都上不好,那個時候的學校都是如此。對于繼續上學我還是希望的,但要想安安靜靜地求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徹底打敗日本人!
當時在學校里,被人談論得最多的就是何時反攻的話題。自從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直接參戰后,那個時候的陪都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反攻在即。但時間一天天過去,政府始終沒有提到反攻的事情,反而前線不斷有不好的消息傳回來。
1943年下半年的時候,我的一個好友李壯丁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政府有意放開學生參軍的口子,鼓勵學生參軍。
李壯丁帶來的消息讓我們很是吃驚,學生從軍不是沒有先例,但情況比較特殊,參軍的大多是學校沒有隨同南遷的零散學生或者類似于東三省流亡學生。而且政府一向都不提倡學生參軍,即便是鄂西會戰的時候。眼看著日本鬼子就要殺進四川的危急情況下,政府也同樣沒有放開這個口子。我們知道李壯丁家里有個不得了的親戚,但對他的這個消息還是半信半疑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消息越來越多,李壯丁的消息看樣子是真的了。
1943年年底,學生從軍已經成了重慶各大學校的一股暗流,很多原來對我們橫眉冷對的街頭征兵官開始對大膽報名參軍的學生和顏悅色起來。
1944年年初,有確切的消息傳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定開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廣泛動員在校學生參軍。帶回來這個消息的國文老師馬上就被興奮的同學包圍了。很快,學校就統一開辟了學生參軍的報名點。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之所以從拒絕學生到現在鼓勵學生參軍,主要是因為美國人的因素。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和美國成為戰略同盟,為保衛滇緬交通大動脈,成立了中緬印戰區,由蔣介石擔任司令官,美國將軍史迪威擔任參謀長,以中央軍精銳為基礎,組織了第一次遠征軍。但10萬大軍因為戰略決策上的失誤,兵敗野人山,精銳之師或葬身異域,或被迫撤退到印度,僅有少部分回到國內。中緬交通也隨之中斷,中國已被日本形成了半包圍的戰略態勢。但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略態勢的好轉,美國迫不及待地開始武裝中國駐印軍,但讓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壯丁兵學英文,了解活塞發動機的工作原理,這顯然是強人所難,所以美國人一再要求蔣介石輸送知識青年到印度參加遠征軍。
政府放開了學生參軍的口子,我第一時間就報了名,但也是偷偷摸摸的,我知道家里一定不會同意。李壯丁也和我一起報了名,同樣也是瞞著家里人。我們報了名后就回家偷偷簡單收拾了一下,并且預先寫好了書信。到了集合的那一天,離家的時候才感到有點不舍,但還是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我們先是在學校集合,點了名后,大部分報了名的同學都來了,還有一些家里死活不同意的沒有到場,之后我們就上了卡車,被運到了郊外的兵營中,拿到了沒有軍銜的軍服和一些生活物資。穿上軍服,雖然沒有軍銜,但依然覺得自己容光煥發。隨后我們進行了一個月的新兵訓練。當時還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由于很多同學都和我一樣是瞞著家里來參軍的,到家里發現人失蹤以后紛紛發動人手來找,有的學生家長能量比較大,找到了這個兵營。但守營的士兵不管是誰都不讓進,所以營門口每天都有很多喚兒喚女的家長徘徊著。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來了沒有,我不忍心去想,更不忍心去看……
新兵整訓結束后,我們放了幾天的假,被允許回家看看,但嚴格規定了歸隊時間,而且得同學們相互作保,若有人不按時歸隊,作保的人就得受到牽連。我沒忍住思念,還是回到了家里。父母見木已成舟,只有默認了這一事實,只是帶著眼淚不斷地叮囑我注意身體和安全。假期快結束時,我才在父母和鄰居們依依不舍的送別下回到軍營。因為我們被告知,過幾天將通過空運的方式前往印度遠征軍營地。
坐飛機對于我們這些學生兵來說還真是新鮮事,日本鬼子的轟炸機倒是經常見,但坐飛機,而且是飛到國門之外,這種新鮮感是無與倫比的,當時幾乎所有的戰友都在討論坐飛機的事情。但后來殘酷的事實擊碎了我們之前所有的幻想,那幾小時的旅程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時刻。
到印度去
在剛上飛機的時候,飛機遠沒有我想象中那么神秘,不算大的機艙并不舒服。在上飛機之前我們還要經過體檢,全部脫得光溜溜的,只剩下一條內褲,由美軍的軍醫挨個替我們檢查,檢查了很多項目,檢查完畢的,由每個醫生在每個人手臂上用章蓋個戳,當時的感覺就像當年準備被賣到美國的“豬仔”一樣,渾身不自在。本來以為檢查完就可以穿上衣服,但上面傳下來了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所有人都不允許穿上衣服,部隊配發的槍支彈藥、背包水壺等東西也一律不準帶,大家都得光著身子上飛機。
當時是初春時節,但四川盆地一向氣溫不算低,再加上都是些年輕的棒小伙子,所以即便是光著身子上的飛機也不覺得有什么,而且大家都光著,也就沒有了怨言。不知道發愁的同學們還在比誰的肌肉多,甚至還取笑某位胖同學身上的肥肉。
但飛機起飛以后,我們就再也笑不出來了。飛機里人很多,大家幾乎都貼在了一起,沒有多少活動的空間,起飛的時候顛簸得很厲害,飛了一陣才平穩,然后一群本來都很緊張的半大孩子又開始了嬉笑打鬧。但沒過多久,大家就發現了異樣:隨著飛機越飛越高,氣溫也越來越低,有眼尖的發現機艙的窗戶上已經結了霜。當時大家就開始打哆嗦了,后來實在冷得受不了就相互抱在一起取暖。在最冷的時候,機艙的喇叭傳來通知,是美國飛行員用英語發出的通知,大意是說飛機準備飛越喜馬拉雅山,空氣中有強氣流,請所有成員注意做好準備。
沒過多久,飛機就開始顛簸起來,而且更糟糕的是氣溫更低了,很多人就抱在一起在那亂罵,有的人甚至哭了起來,要求停機返航。但駕駛艙的飛行員根本聽不見,機艙里的人都被凍壞了,有的人甚至開始出現幻覺,在喊著熱,當時我也幾乎失去了知覺。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飛機降落了,等飛機停穩以后,機艙門被打開,除了大鼻子的飛行員之外,還有很多美國的軍醫和教官。艙門一被打開,我分明聽見了一聲驚呼“Oh My God”,然后就失去了知覺。當我再度醒來的時候,是躺在一片陌生的草地上,周圍到處都是同機的伙伴,依舊沒有衣服,但蓋著一床薄毯子,印度的太陽暖洋洋的,曬得人很舒服。之后,很多在飛機上被凍昏過去的同伴都紛紛醒了過來。這時候才有一個美國教官過來整理隊伍,全部的人都經過了醫生的體檢,然后每人先發了一身軍服穿上,美式新軍裝,但遺憾的是依然沒有軍銜。
那個美國教官很好奇,就問我們為什么是光著身子從飛機上下來的,難道我們之前被強盜洗劫了嗎?有同學回答說是長官的命令。那個美國教官皺了皺眉,聳了聳肩膀,說道:“真是奇怪的命令。”
后來我們才知道為什么我們會受這一路的罪了,原因在于當時需要轉運的學生兵太多,而飛機有限,所以官僚們拍了拍腦袋就想出了這么個餿主意,讓所有人把衣服脫光,這樣每架飛機能多塞幾個人上去,而且留下來的衣服還可以給后來的士兵穿。這個辦法簡直是一舉兩得,惠而不費,反正我們這些人到了印度以后美國人也要負擔我們所有的裝備補給。但他們卻沒有想到在零下幾十度的氣溫下,光著身子是一種什么感覺,或者說這些官僚大老爺根本不在乎。因為出現了凍死凍傷的情況,美國方面拍電報向重慶提出了抗議,從那以后,這一現象沒再出現。
到達印度后,因為在飛機上被凍狠了,我們休息了好幾天才緩過神來,然后就到了選擇兵種的時候。出乎意料的是,不是讓我們來選部隊,而是部隊來選我們。當時的專業科目很多,最受人矚目的自然是坦克兵,最倒霉的自然是工兵,比較無所謂的則是汽車兵或者通信兵了,而偏偏汽車兵和工兵的需求量最大。我那個時候雖然年紀不大,但個頭不小,坦克兵訓練營的教官經過我面前,我連忙抬頭挺胸作威武狀,結果那個美軍少尉看了我兩眼以后就搖搖頭走開了,反而是站我前面的李壯丁被選上了。李壯丁雖然比我年齡大很多,卻是非常典型的四川人的身材,比我矮一個頭,又瘦又小,他居然被最被人看好的坦克兵營選走了,幾乎讓所有人跌破了眼鏡。后來我才明白,越是像坦克或者戰斗機的駕駛員就越需要身材瘦小而靈活的人,因為坦克里活動空間有限,要是弄幾個大胖子進去,大家在里面都不能動了。
在一眾同伴或羨慕或嫉妒的眼光中,李壯丁歡天喜地地被領走了。接下來,又有多個兵科的教官來選人,到工兵營的教官來的時候,我趕緊佝僂著身子,生怕被選中,但世界上偏偏怕什么來什么,這個教官是一個中國教官,走到我面前時,我幾乎把頭都縮進脖子里了,結果他喝了一聲“立正”,我在前面軍訓的時候養成了下意識的反應,立即站直了。這個教官捶了捶我的胸口,稱贊我長得結實。其實我當時很想告訴他我身體很差,但終究沒有說出口,我不幸中標,在同伴們幸災樂禍的眼神下進了工兵營報到。
美國式集訓,操練新來的學生娃
1944年,隨著國內知識青年的踴躍從軍,蘭姆伽這個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的一座偏僻小鎮突然間熱鬧了起來。最初到達蘭姆伽的是在遠征軍第一次作戰失敗的新三十八師及后來敗退至此的第五軍殘部約一萬人,隨著空運的開展,到后期平均每天有四百多名學生兵從國內空運至此。在這里,學生兵們按照美軍的訓練方式訓練,并全部配備了最新的美式裝備,為反攻緬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工兵營應該說是科目最多的特種營了,雖然我主要的學習方向是舟橋專業,但是例如爆破、排雷、排爆、測繪、工事建筑、偽裝等科目也需要學習,經常聽課都要聽一天。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美國教官,因為我英語聽和說的能力較強,相比營里其他從戰斗部隊轉過來的老兵來說,學習起來進展很快。那些老兵當初都是戰斗部隊的士兵,有的還負過傷得過軍功章,說到打仗他們是一套一套的,但說到聽用英語講授的工兵課他們就傻眼了,很多人斗大的中國字不識一個,就更別說英文了。偏偏工兵又是各部隊需求量最大的兵種,所以人員缺口極大,不得不從戰斗部隊里選拔合適的人。但這里的合適也只是個相對的概念,當時國民黨軍隊伍里的文化水平低,能把自己的名字完整寫下來的都是了不得的文化人了,讓他們聽英語工兵課程明顯是強人所難,所以當時駐印軍才迫切需要知識青年從軍。
由于我們是最早一批來到印度的學生兵,所以在工兵營里就我們三個學生兵勉強能跟上進度,我們的王教官見老兵們在美國教官的課程上如聽天書,覺得不是個辦法,就請求我幫他們補習,一開始我是在課堂上進行同步翻譯,后來我就逐漸培養他們聽說英語的能力。其實能被部隊保送來工兵營的大多數人比較聰明,只是少年時期少了受教育的機會,而我也因此成了工兵營里的新兵班長。后來在評定軍銜的時候,我因此直接成了中士,而其他人除了一個老兵在部隊上就是中士軍銜外,其他都評為下士。
在駐印軍序列中,士官的待遇相當優厚,因為采用的是美國的軍銜與相應的補給制度,士官比普通士兵多了很多福利。其實福利什么的我倒不在乎,我是覺得有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兵能恭恭敬敬地叫我一聲班長,那得意勁確實不擺了(四川方言,就是不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意思)。
我們在駐印軍的訓練中,除了要學習相關的特種兵(這里的特種兵是指汽車兵、通信兵、工兵等輔助兵種)知識外,還得進行相應的軍事訓練,畢竟我們以后也要被分配到作戰部隊中去。因此,老兵們總是喜歡在這個時候收拾我們,許多學生兵因為一來就成了班長,很多老兵就不服氣,所以在訓練場上就使壞要整我們。但這種整也不是說刻意的害人,而是采取一種高標準、嚴要求的訓練標準,拼刺動作不達標,跑操場20圈;站軍姿不達標,跑操場20圈。好在我身體還好,還經得起這樣的磨煉。
在印度的時候還有個很不好的現象,就是士兵們拉幫結伙的現象比較嚴重。有一次,在食堂打飯的時候,負責放飯的班長是東北人,每個東北籍的新兵每人多打一勺菜,第二天,輪到四川班長執勤,就給每個四川籍的新兵多打一勺菜。結果那個東北的班長不愿意了,那個四川班長就反唇相譏:“你打得,老子就打不得嘍?”然后兩個老兵班長就扭打起來,東北籍和四川籍的新兵們也去助拳。周圍其他省籍的新兵就在邊上起哄,一時間包子與饅頭齊飛,湯鍋與碗筷共舞,打成了一鍋粥,一些開始還在邊上看笑話的人屢屢被誤傷,也擼起袖子加入戰團。結果當天在那個食堂吃飯的,統統被關禁閉一天。
在印度的生活其實現在回想起來有笑有淚,但總體來說還是開心的時候比較多。到1944年年底的時候,隨著到印度受訓的學生兵越來越多,我們第一批受訓的學生兵大多已經畢業,接下來就準備開赴緬甸前線對日作戰了。
〔本刊責任編輯 柳婷婷〕
〔原載《中外書摘》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