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電影的一世情緣
夏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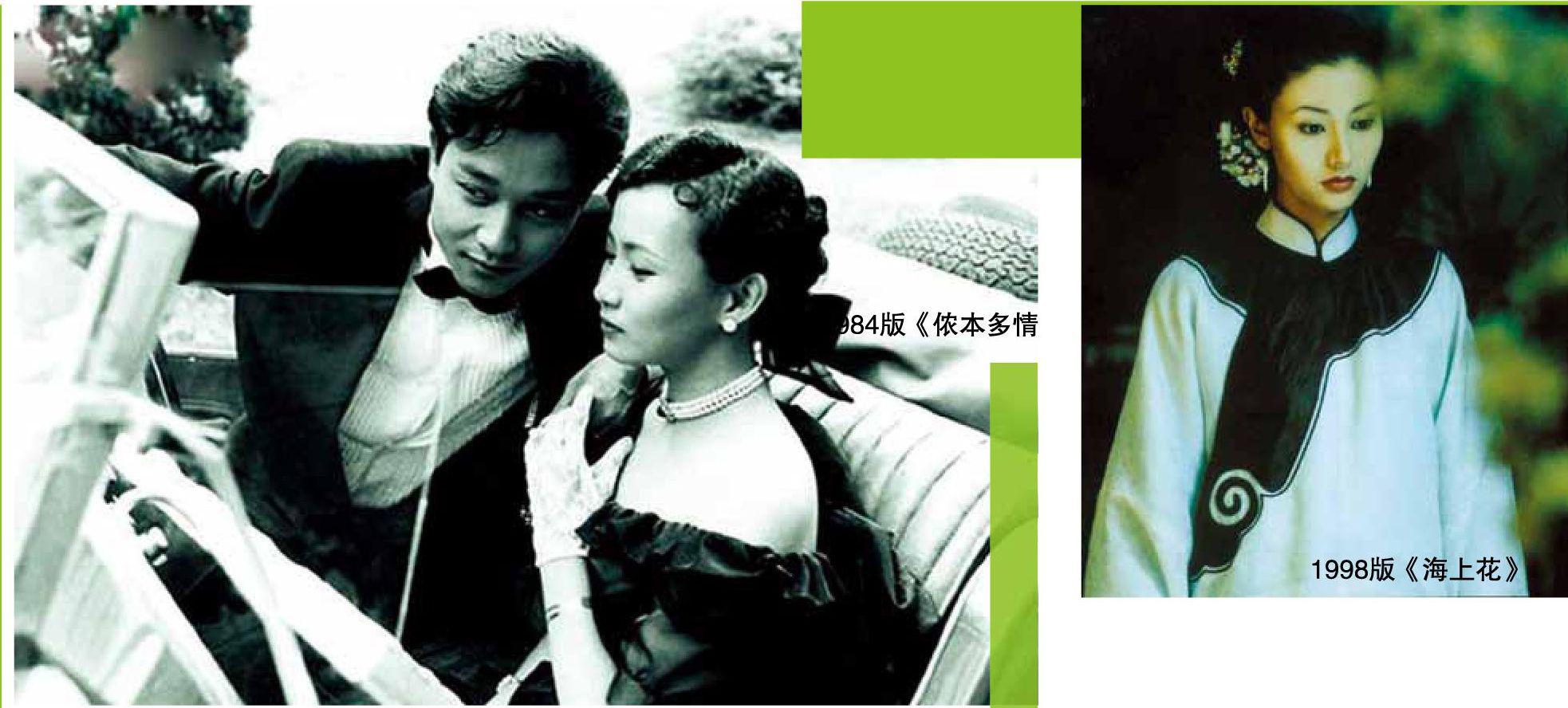
從看電影到評電影:最看重的不是名氣而是技藝
著名現代女作家張愛玲是1920年9月生于上海的,她的青少年時代也主要是在上海度過的。在這座現代中國電影事業最為興盛發達的城市里,她從小就得以廣泛地接觸中外電影文化,深受電影藝術的熏陶,進而與電影結下了終生的不解之緣。
張愛玲很小就獨自一人去電影院看電影,雖然來回都需家里傭人接送,有時遇到傭人迎接不及時,看完電影后,還要在電影院門口等上好一會兒,但她從不厭煩,樂此不疲。她平時從學校放假回家,或去舅舅家與表姐們玩,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也是看電影。有一次她和弟弟張子靜從上海去杭州親戚家玩,剛到的第二天,看到報紙上廣告說她所喜愛的一位女影星主演的電影正在上海某家電影院上映,便立刻說要趕回上海去看。親戚們怎么攔也攔不住。張子靜只好陪她乘火車返回上海。她一到上海,就帶著張子靜直奔那家電影院,一連看了兩場。看完電影,張子靜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幸虧今天趕回來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難過呢!”
張子靜曾回憶說,張愛玲學生時代“訂閱的一些雜志,也以電影雜志居多”。“在她的床頭,與小說并列的就是美國的電影雜志,如《Movie star》、《Sereenplay》等等。三四十年代美國著名演員主演的片子,她都愛看。如葛麗泰·嘉寶、蓓蒂·戴維斯、瓊·克勞馥、加利·古柏、克拉克·蓋博、秀蘭·鄧波兒、費雯麗等明星的片子,幾乎每部必看。”張愛玲自己在《談跳舞》、《談看書》等文章里,也提到過一些她青年時期觀看的外國影片,如日本電影《貍宮歌聲》和《舞城秘史》,法國電影《冬之獅》,美國電影《叛艦喋血記》和動畫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記》等等。其中像《叛艦喋血記》兩次攝制的不同影片版本,她都看過。
張愛玲也很喜歡看國產影片。特別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影壇嶄露頭角的阮玲玉、談瑛、陳燕燕、顧蘭君、上官云珠、蔣天流、石揮、藍馬、趙丹等人主演的影片,她都是要看的。前面提及的她由杭州趕回上海要看的電影,就是30年代才華出眾的女影星談瑛參與主演的《風》(1933年聯華影業公司出品,吳村編導)。1934年6月,蔡楚生編導的《漁光曲》在上海連映84天,盛況空前。萬千觀眾之中自然少不了張愛玲,而且她連影片中的主題曲《漁光曲》也極為喜愛。她不僅在學練鋼琴時自彈自唱《漁光曲》,還興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個叫小胖的小傭人學唱這首歌。盡管不識字的小胖學唱很吃力,僅《漁光曲》的開頭兩句“云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學了差不多一個上午,還是不太會唱,但張愛玲仍然其樂融融地教了她一遍又一遍。
張愛玲性格較內向,不善于交際應酬,一向話不多。即使和家人親友在一起,若是談到不感興趣的話題,她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的,但是一談起她喜愛的小說、電影、劇本等等文學藝術的話題,她就逸興飛揚,侃侃而談。她在學生時代與唯一的弟弟張子靜見面時,總是談小說和電影,很少談家人親友和日常生活,至于她的私事更是絕口不提。在上海解放前后的一段時期內,張愛玲同已經獨立生活和工作的張子靜聚談時,興趣盎然的話題仍然是文學和電影,而對當時世人關注的政治時局少有涉及。她雖然不太適應解放初期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但對解放區作家趙樹理的成名作《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和新中國初期電影的代表作《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很是欣賞,除了自己閱讀、觀看外,還熱情地向張子靜推薦介紹。可是,當張子靜關切地問起她對未來有什么打算時,她卻默然良久,不作回答。后來她離開上海去香港,事先也沒有告知張子靜。
也許是由于青少年時代親情關系不甚和睦的影響,曾自稱“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的張愛玲,內心世界較為封閉,難于合群,交友很少。不過,與她有深交的親知友好,大多也是與電影有交情的。如張愛玲的終生至交炎櫻,原是她就讀香港大學時的同學,也是時常在一起看電影的同好。張愛玲曾在散文《燼余錄》里熱情夸贊她,原因之一就是1941年底日軍攻打香港時,“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另一個出名的女作家蘇青,是張愛玲當時可以與之互換衣服穿的密友,也是一位對電影興趣盎然的同道,還曾一度進入電影公司就任編劇。她平時孝敬侍奉母親的“常規”之一,就是陪母親去看中國電影。而她自己去影院看電影時,寧可冷淡遇見的女友,不與她們應酬交談,也要“全神貫注到銀幕上的動作和表情”。而寫過《夜店》、《海誓》等十幾個電影劇本的著名作家柯靈,從張愛玲試筆文壇一開始就給予了大力扶助,曾在其主編的40年代有名的雜志《萬象》上,登出了她早期撰寫的小說《心經》、《琉璃瓦》和《連環套》,以后又熱心地引導她進入了戲劇和電影創作的領域。50年代初期,張愛玲去香港后的莫逆之交宋淇(林以亮),時任香港電影懋業公司制片部經理,也為張愛玲在五六十年代與“電懋”攜手制作電影盡過很多的心力。
張愛玲不僅喜歡看電影談電影,也很樂意評電影。1937年,她在上海圣瑪利亞女校高中三年級學習時,就在學校年刊《風藻》上,發表了一篇評析當時動畫影片創作傾向和發展趨勢的文章《論卡通畫之前途》。以后,她的職業作家生涯實際上也是從寫影評開始的。1942年11月,張愛玲從香港返回上海,插入圣約翰大學文科四年級就讀不久,便因經濟窘困等緣故輟學而專事寫作。最初,她給英文《泰晤士報》撰寫了一些影評和劇評。接著,她又為英文月刊《二十世紀》一連寫了1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也是影評。如她在該刊1943年5月號上登出的《Wife.vamp.child》(《妻子·蕩婦·孩童》),就是關于當時上映的家庭生活倫理片《梅娘曲》和《桃李爭春》的評論文章。在6月到11月的各期《二十世紀》上,她也都寫有影評文章,分別評論了當時公映的《萬世流芳》、《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兩代女性》、《母親》、《萬紫千紅》、《回春曲》、《新生》、《漁家女》等影片。此后,她因發表《沉香屑》、《傾城之戀》、《金鎖記》等小說而贏得盛名,稿約紛至,應接不暇,就不再為《泰晤士報》和《二十世紀》撰文寫稿了。但她似乎很珍惜自己出道之初在這些英文報刊上用英文撰寫的影評。如《Wife.Vamp.Child》和另一篇《MotheranaDaughters一in一law》(《婆婆和媳婦》),就被她用中文改寫后,更名為《借銀燈》和《銀宮就學記》,收入1944年12月初版的散文集《流言》中。1995年,張愛玲謝世以后,臺灣《聯合文學》第3卷第5期還翻譯發表了她這些英文影評中的5篇,以表紀念。
張愛玲是個“隨便什么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一點”的人,對電影的欣賞也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獨到之處。例如,對于電影演員,她所看重的主要是演技,而不是一般人通常關注的名氣或外貌。她觀看抗戰勝利后昆侖影業公司的力作《萬家燈火》時,就與眾不同地認為其中最好的演員并不是擔任主演的藍馬、上官云珠等大牌明星,而是一位在銀幕上一閃而過的女配角。這位在影片中飾演主人公家中女傭的演員,盡管沒有一句臺詞而且只有兩個鏡頭,但其自然貼切的出色表演讓張愛玲為之心折,過目不忘。而她評論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桃李爭春》時,也著眼于演員的表演,直言不諱綽號為“南國美人”的影星陳云棠在影片中“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氣了些”,并且十分不滿另一女演員白光“單靠一雙美麗的眼睛”來彌補其“吃力”表演的缺憾。在上海淪陷時期,發表過張愛玲許多作品的《雜志》社曾搞過一次活動,“邀請東亞明星李香蘭女士和中國女作家張愛玲舉行座談”。當時張愛玲關于李香蘭說的最多還是她演藝的戲路子,并且毫不客氣地當面直言她的表演像仙女,像小鳥,但不像一個普通的女人。張愛玲喜歡看美國女影星葛麗泰·嘉寶演的電影,也是因為欣賞她的精湛演技。她看世界名片《亂世佳人》,所推崇的僅僅是表演超群的費雯麗和蓋博,對其他的演員都退而視之。有一次,她談到美國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時,也還是說其中的演員詹姆斯·史都華演技很好。
寫電影:始于“不了情”,終于“離恨天”
1946年7月,參與籌辦文華影業公司的著名編導桑弧,經柯靈的介紹,約請張愛玲編寫電影劇本。在此之前,張愛玲從未寫過電影劇本。但她早有“觸電”之心,中學時代就曾有一個時期“想學畫卡通影片”。以后在小說創作中,她也常常借用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法。如在其代表作《金鎖記》中,有關主人公曹七巧守寡前后10年間變化的一段描寫,就采取了曾被“迅雨”(即翻譯家傅雷)大為贊賞的電影中“巧妙的轉調技術”。因此,當張愛玲答應與桑弧合作以后,便憑著蓄積已久的電影藝術素養和創作準備,很快寫出了電影劇本《不了情》。這是一個“美麗蒼涼”的哀情故事:貧寒的家庭女教師廖家茵與婚姻不幸福的主人夏宗豫相互由憐而愛,但又難以擺脫夏宗豫已有的無愛婚姻和廖父厚顏無恥的胡攪蠻纏,最后廖家茵毅然自斷情愛,向夏宗豫謊稱要回家鄉和表哥結婚,而只身到千里之外的廈門去教書。
桑弧拿到這個劇本后,十分欣喜而又極為重視,立即將其作為“文華”創業的開山之作投入拍攝。他根據《不了情》的劇作特點,選擇了當時最紅的男影星劉瓊和退隱多年的女演員陳燕燕出演男女主角。其中陳燕燕是張愛玲以往最喜歡的女影星之一,已演出過30多部影片,被譽為“最有前途的悲旦”。雖然她在抗戰勝利前后曾一度息影,但此次東山再起,參與《不了情》的演出,“面貌依舊美麗年輕,加上她特有的一種甜味”,還是很受觀眾的歡迎。此外,在影片中扮演廖父和夏家女傭姚媽等重要角色的演員也都很稱職。因此,《不了情》于1947年初上映之后,一炮打響,賣座極佳,產生了很大的轟動效應。張愛玲也乘勢把《不了情》的電影劇本改寫為中篇小說《多少恨》,于1947年夏登載在桑弧為實際主編的《大家》月刊上,36年后又收入了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電影劇本集《惘然記》。
桑弧獲得了與張愛玲聯手創作電影《不了情》的碩果以后,并不滿足。他隨即又敦請張愛玲繼續合作,再寫一個電影劇本,并提出了創新的構想。張愛玲嘗到《不了情》轟動的甜頭,對桑弧的建議欣然應允。桑弧把電影構想告訴張愛玲后,她即一氣呵成,完成了劇本。這個劇本就是隨后被桑弧搬上銀幕的《太太萬歲》。
與《不了情》的悲情格調相反,《太太萬歲》是一出世俗氣息較濃的輕喜劇。其主角陳思珍是一個精明能干、八面玲瓏的家庭主婦。她想方設法使吝嗇勢利的父親出錢資助丈夫唐志遠辦起了公司。可是唐志遠發財以后,卻移情別戀于一個交際花,唐母也開始對她多方責難。但她在忍氣吞聲的生活中,仍然幫助面臨公司破產的唐志遠渡過了難關,同時巧妙地制服了交際花的敲詐,并促成了其弟與小姑的婚姻,最后終于贏得了丈夫的回心轉意,兩人重歸于好。為了吸引觀眾,張愛玲把這一出家庭生活喜劇寫得流暢風趣,編入了一連串的誤會、巧合和逗笑的噱頭。而桑弧精巧細致的導演和蔣天流、張伐、石揮、上官云珠、韓非等人生動靈活的表演,則把張愛玲創造的這些紙上的“熱鬧”,妥帖地轉化為銀幕上觀眾喜聞樂見的畫面。據說《太太萬歲》上映的時候,觀眾的笑聲不斷。一度與張愛玲結為夫妻的胡蘭成,也曾提到過他當年在溫州看此片時,電影院里觀眾的情緒相當活躍。
《太太萬歲》是文華影業公司成立后制作的第二部影片。桑弧與張愛玲兩度成功合作所創造的“開門紅”,令“文華”的大老板心花怒放。他為此特邀桑弧、張愛玲等“有功之臣”去無錫游太湖,吃“船菜”。張愛玲平時很少參加這類應酬,但這一次卻欣然而至,和大家一起聊天吃菜,興致勃勃。后來她提起這次游太湖,還直說“印象深刻,別致得很”。
然而,當時張愛玲因與桑弧通力合作而被人硬扯出的情緣糾葛,卻給她帶來了不少煩惱。其時,張愛玲27歲,已和另結新歡的胡蘭成決絕分手,而桑弧30剛出頭,單身未婚。兩人相得益彰的合作和日漸親密的交往,引動了他們的一些朋友想“成人之美”的好心。如與張愛玲和桑弧都很熟悉的龔之方,有一次去看張愛玲,就把朋友之間認為他們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對佳偶之類的想法,向她婉轉地提出。可是張愛玲卻讓他碰了個硬釘子。據龔之方回憶說,當時“她的回答不是語言,只是對我搖頭、再搖頭和三搖頭,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說下去了”。盡管如此,這些朋友要為張愛玲和桑弧撮合婚事的好意已被一些小報獲悉,并被渲染為張、桑已有男女之情一類的艷事逸聞。這自然讓當時尚未擺脫離異痛苦的張愛玲心中不快了。但她與桑弧的友誼和交往并沒有因此而中斷。不久,當桑弧獨自編、導言情片《哀樂中年》時,她還熱心地提出了一些參考意見,以至后來有不少人誤以為此片是她編寫的。
張愛玲寫完《太太萬歲》以后,又把曾被“迅雨”譽為“最完滿之作”的《金鎖記》改編為電影劇本。據說仍由“文華”出品,桑弧導演,并內定張瑞芳為主演,但始終未能開拍。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藝的夏衍極為看重張愛玲的才華,很想安排她去自己兼任所長的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擔任編劇。可是,有些人因為張愛玲在上海淪陷期間涉嫌“文化漢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態度。夏衍一時未能如愿。而張愛玲當時雖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并在龔之方奉夏衍之命所辦的《亦報》上發表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中篇小說《小艾》,但她還是深感不合時宜,很快去了香港,當然也就不能在新中國電影界展露其才了。夏衍聽到這個消息后,直嘆可惜。
張愛玲在香港呆了三年多,又于1955年11月乘船赴美,到了紐約。第二年2月,她獲得了美國愛德華·麥克道威爾寫作基金會為期兩年的寫作獎金,于是搬到這個基金會所管轄的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僻靜莊園專事寫作。在這里,她結識了曾為好萊塢編寫過12年電影劇本的德裔作家賴雅,并很快于8月與之成婚。當時張愛玲36歲,賴雅已經65歲,兩人以前均有過一次離婚的經歷。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他們就由相識而結婚了,婚后生活也很美滿。
張愛玲和賴雅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多年,直到1967年賴雅病逝。在此期間,張愛玲與香港電影懋業公司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電影創作合作關系。“電懋”是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界最有實力的電影公司之一。張愛玲經摯友宋淇的鼎力相助,與“電懋”合作了近10年之久,而且一直比較順利。她最初為“電懋”所寫的電影劇本《情場如戰場》,是根據美國麥克斯·舒爾曼創作的舞臺劇《溫柔的陷阱》改編的。其主要劇情是圍繞著幾位都市未婚男女之間陰錯陽差、好事多磨的戀愛糾葛展開的。同《太太萬歲》一樣,《情場如戰場》也有著顯明的世俗喜劇色彩,只是比前者多了一些都市白領階層談情說愛的浪漫情調。這個劇本于1957年拍成電影,據說上映后打破了當時香港國語片的賣座記錄。
以后,張愛玲又接連為“電懋”編寫了《人財兩得》(1957年,岳楓導演,陳厚、李泥主演)、《桃花運》(1958年,岳楓導演,陳厚、葉楓主演)、《南北和》(1961年,王天林導演)、《南北一家親》(1962年,王天林導演,雷震、白露明主演)、《小兒女》(1963年,王天林導演,雷震、尤敏主演,獲當年臺灣金馬獎優等劇情片獎)、《一曲難忘》(1964年,鐘敬(啟)文導演,張揚、葉楓主演)、《南北喜相逢》(1964年,王天林導演,雷震、白露明主演)、《魂歸離恨天》(1965年)等劇本。這些作品大多沿襲了張愛玲以往電影劇本創作的套路,以婚姻戀愛為經,世態人情作緯,演示出一個個世俗男女悲歡離合的言情故事。由于張愛玲對所寫的人物及其生活十分熟悉,又掌握了豐富的編劇經驗和技巧,所以她所寫的這些劇本,凡是攝制完成上映的,都很叫座。其中如《南北喜相逢》等,還由宋淇執筆改為粵語版本,吸引了許多說粵語的觀眾,更加擴大了影片的影響。張愛玲因此而成了當時海外華語電影界大受歡迎的名編劇。
張愛玲樂意為“電懋”編劇本,“電懋”也很善待她。她為“電懋”所寫的劇本,差不多都拍成了電影。絕無僅有的例外是1965年張愛玲編寫的劇本《魂歸離恨天》,它還沒有來得及交到導演手上,“電懋”就因董事長兼總經理陸運濤遭遇空難,而于同年9月改組為國泰機構(香港)有限公司。從此,張愛玲便脫離了與“電懋”的合作關系,也永遠離開了電影創作領域。她此后直到1995年9月去世,再也沒有寫過電影劇本。《魂歸離恨天》成了她為“電懋”編寫的最后一個電影劇本,也成了她整個寫作生涯中涉筆電影創作的最后成果。 【責編/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