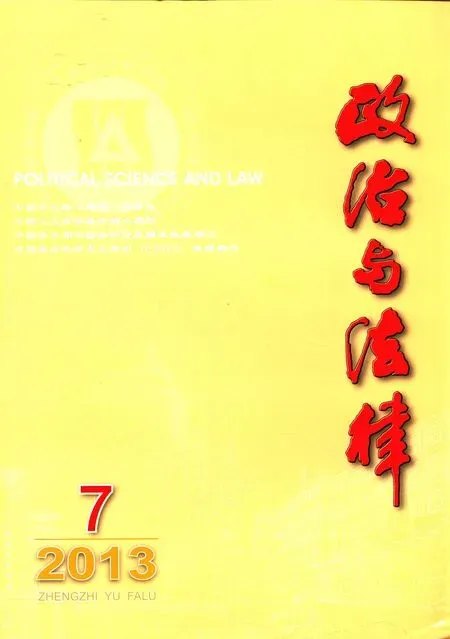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偏向考證*——兼及刑事政策導向與法規范性之協調
孫萬懷 李高寧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42)
一、問題的提出——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打擊態勢與打擊特征
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對涉及食品安全類的犯罪進行了全面的修改,1這也體現了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類犯罪所持的積極規制的態度。不僅于此,在現實司法過程中也體現了這樣的態度。“2008年,全國法院共審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件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84件,生效判決人數101人;2009年共審結此類案件148件,生效判決人數208人;2010年共審結此類案件119件,生效判決人數162人;2011年1月至10月已審結此類案件173件,生效判決人數255人。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依照法律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等罪名追究了刑事責任。”2“2012年1月至6月,全國法院共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330件,審結276件,生效判決人數425人。”32011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該通知指出,食品安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國計民生、社會穩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中央高度重視食品安全,要求對違法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嚴重擾亂市場,危及人民群眾利益甚至生命的犯罪行為,務必依法嚴懲,公開審判,營造堅決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的社會氛圍。42011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4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5提供了具體的裁判樣本。在當前食品安全堪憂的時候,運用刑法,重視對食品安全犯罪進行打擊十分必要,也與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宗旨吻合,但是在貫徹刑事政策的過程中,合法性的要求也不應被忽視。筆者選取食品犯罪中最為嚴重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具體司法判例的研究發現,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有毒有害食品類犯罪行為在定罪和量刑中存在不足。
筆者從北大法意上共收集了40余起相關司法判例進行分析,其中判處10年以上以至無期徒刑、死刑的有9例,約占總數的20%,這9例中有8例為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具體參見表1)。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的共有34例,約占總數的78%,其中有16例判處了緩刑(參見表2、表3);而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僅有1例,占總數的2%。6上述統計結果顯示在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中存在兩個極端,對基本犯罪判處的刑罰較輕,大量適用緩刑;對加重結果情節判處刑罰較重,頻繁適用死刑,體現了輕輕重重的政策傾向。

表1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的案例

表2 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適用緩刑)的案例

案名images/BZ_149_493_306_510_340.png 裁判機關images/BZ_149_835_306_852_340.png 案號images/BZ_149_1238_306_1255_340.png 刑期images/BZ_149_1731_306_1748_340.png任衛東案 河南省夏邑縣人民法院 (2011)夏刑初字第172 號 判處有期徒刑6 個月,緩刑1 年 黃宗斌案 福建省古田縣人民法院 (2011)古刑初字第68 號 判處有期徒刑1 年6 個月,緩刑2 年 趙廣明案 河南省內黃縣人民法院 (2010)內刑初字第348 號 判處有期徒刑3 年,緩刑3 年 余祖強、 余珍鳳案 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 (2002)豐刑初字第22 號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 年,緩刑2 年 陳國祥案 河南省沁陽市人民法院 (2011)沁刑初字第307 號 判處拘役6 個月,緩刑1 年 孫占其案 河南省沁陽市人民法院 (2011)沁刑初字第297 號 判處拘役3 個月,緩刑6 個月

表3 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不適用緩刑)的案例
需要說明的是,在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包括為嚴懲犯罪分子而判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案件和201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四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之一的“瘦肉精”案件,本文一并統計。
二、有毒有害食品犯罪量刑中的輕輕重重傾向之質疑
(一)治理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體現了輕輕重重的量刑思路
通過對以上有毒有害食品犯罪40余起判例的研究分析可以發現,一方面,在當前的打擊態勢下,對于社會影響比較大、危害后果比較嚴重的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司法實踐中具有明顯的重者更重的傾向。具體而言,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的6個判例中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有5例,比例高達80%以上。此外,我國的相關刑事政策也充分體現了對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懲罰之高壓態度,如2011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罪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另一方面,對于危害較小的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體現了輕者更輕的傾向。具體而言,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的34個判例中有16例適用了緩刑,比例高達47%。其中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一般僅僅實施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為,尚未造成危害后果;同時個別犯罪分子又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成立自首;且認罪態度好,確有悔罪表現,具備了依法可從輕處罰或酌情從輕處罰的情節,故針對這些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適用了緩刑。可見,我國治理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體現了輕輕重重的量刑思路。
在理論上,我國也有學者大力推崇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甚至認為我國現行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就是輕輕重重的具體體現。如有學者指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國際范圍內“重重輕輕”兩極化刑事政策的中國化。7有學者認為,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在我國稱為“寬嚴相濟”。8筆者認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與輕輕重重的兩極化刑事政策存在很大差異,不能將二者等同視之,而且我國目前的社會現實和法治環境也不同于美國當年提出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社會背景,因此不能簡單移植和適用。
首先,輕輕重重刑事政策有其產生的獨特背景。輕輕重重是西方國家秉承的一種刑事政策,又稱為兩極化的刑事政策。正如有學者指出:“對于重大犯罪及危險犯罪,采取嚴格對策之嚴格刑事政策;對于輕微犯罪及某種程度有改善可能性的,采取寬松對策之寬松刑事政策。如此之政策,亦稱刑事政策之兩極化。”9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其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對矯正刑現狀的不滿。兩極化的刑事政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此前美國奉行的是矯正刑。但是矯正刑導致刑罰懲罰的異化,矯正刑打著預防犯罪的旗號完全拋棄了報應刑的觀念,最終沒有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而且導致放縱犯罪的結果。矯正刑的現狀使得民眾對其大為不滿,在這種背景下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登上了舞臺。有學者指出:“矯正刑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踐中的濫用,最終導致美國的刑事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生了轉向,催生了美國的兩極化刑事政策的誕生”。10其產生的原因之二是刑法資源不足。矯正刑要求刑罰執行的過程中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的犯罪人對癥下藥,通過個別矯正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美國有學者提出為了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應當將監獄改造成醫院。11但這必然會加大資源的投入,一般民眾對加大資源的投入用于犯罪分子改造存在不滿。刑罰報應正義的缺失必然導致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顛覆,納稅人不愿意在犯罪人的改造中再投入更多的資源,而有限的資源又不足以實現矯正犯罪的效果,這種惡性循環導致社會上嚴懲罪犯的呼聲日高。正如有學者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缺乏安全感的美國公眾要求嚴懲嚴重犯罪的呼聲日趨強烈,迫使這些國家通過加重刑罰來作出反應。強調懲罰要與犯罪的嚴重性相適應。”12其產生的原因之三是犯罪數量猛增。20世紀70年代,美國犯罪率上升導致其刑事政策上的轉變。13特別是在“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的理念產生了劇變。其在刑事政策上表現為被視為美國精神象征的個人自由理念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動搖,或者說美國政府和民眾要在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價值之間重新尋求一種平衡。14
這些獨特的背景目前在我國是不存在的,具體而言,“2008年,全國法院共審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件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84件,生效判決人數101人;2009年共審結此類案件148件,生效判決人數208人;2010年共審結此類案件119件,生效判決人數162人;2011年1月至10月已審結此類案件173件,生效判決人數255人。”15由以上數據可看出,我國的食品安全案的數量和受刑罰處罰的人數雖然是遞增的,但并沒有爆炸式的增長。關于矯正刑的弊端在我國也并不存在,因為我國目前的矯正刑正處在初創階段,《刑法修正案八》剛剛確立對緩刑和判處管制的人適用社區矯正。綜上,目前我國的現狀與美國當時產生兩極化刑事政策的社會背景存在極大的不同。
其次,我國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等同于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其獨特的產生背景和涵義,因此不能以二者相同來論證輕輕重重傾向的合理性。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著力整治突出治安問題和治安混亂地區,掃除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堅決遏制刑事犯罪高發勢頭。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積極推行社區矯正。”這一綱領性文件確立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建立在以下基準之上的:其一,對于嚴重刑事犯罪的打擊并沒有被包含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范圍之中。其二,對于非嚴重刑事犯罪才存在一個寬嚴相濟的問題,該決定將寬嚴相濟政策與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與“積極推行社區矯正”放在同一語序中,說明寬嚴相濟政策的核心在于“以寬濟嚴”,也就是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對以前“嚴打”政策的一種糾正。其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一個“司法”政策,這是該決定所明示的,是不能隨意擴張的。其四,對嚴重刑事犯罪的打擊必須“依法”而行,不能超越法律;而寬嚴相濟的政策又是一個“司法”政策。顯然,該決定只是針對特定領域而形成的一種刑事政策,而且也不能夠理解為一種重重輕輕的政策。尤其是針對一種犯罪采取不同的政策顯然也不是政策的應有內涵。對任何犯罪的打擊都應當嚴格依照法律進行。對于嚴重的犯罪適用嚴厲的刑罰本就是刑法應有之義。
既然黨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從寬和嚴的視角來解讀寬嚴相濟政策的,所以寬嚴相濟政策與重重輕輕不是一回事。即使從基本語義上來說,對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也應當是:“嚴,就是要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暴力性犯罪以及嚴重影響人們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必須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寬,就是要堅持區別對待,該寬則寬,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寬大處理。”16陳興良教授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出了更為精辟的解釋。他認為,要想理解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必須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三個關鍵字即“寬”、“嚴”、“濟”加以科學界定。所謂寬指的是刑罰的寬緩,可以分為該輕而輕和該重而輕;所謂嚴是指嚴格或者嚴厲。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在“濟”,這里的濟是指寬與嚴之間的救濟、協調和結合之意。17上述分析可知,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存在極大的差異,兩極化刑事政策要求對重罪和輕罪分別采用更加嚴厲和更加寬緩的政策,輕輕重重是相互分立的兩極。而寬嚴相濟并非是寬與嚴之間的兩極分化,而是要求兩者有機的結合,嚴厲與寬緩互濟、互補。
綜上,我國的社會現實決定了盲目移植輕輕重重刑事政策很可能帶來水土不服,也很可能在不能很有效地解決目前高發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礎上產生其他問題。如上所述,在同一罪名中針對不同情節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目的性,因此對于這種因社會管理失范所引起的高發犯罪,在嚴厲打擊的過程中仍應以最基本的罪刑均衡原則為最高準則,如此方能做到不枉不縱。
(二)有毒有害食品犯罪量刑中必須堅持罪刑均衡原則
1.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基本情節適用輕刑時應防止過輕
在筆者收集的40余起案例中,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的共有34例,占總數的78%;同時在這34個案例中有16例適用了緩刑,比例高達47%。可見,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基本情節普遍的適用了輕刑,其中適用緩刑的比例過大,體現了“輕者更輕”的傾向。筆者認為,對基本情節適用輕刑雖然是合理的,但是應防止過輕。第一,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緩刑的適用有濫用的傾向。緩刑是我國刑法確立的重要刑罰制度之一,是懲罰與寬大相結合的基本形勢政策在刑法運用中的具體化。18在我國適用緩刑必須要求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較輕,并有悔罪表現,且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19通過對上述16例適用緩刑的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僅有10例具備自首情節且認罪態度良好,確有悔罪表現,依法可適用緩刑;但是另外6例中除了具備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基本情節之外,犯罪分子完全不具備悔罪表現,不符合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對其適用緩刑是不恰當的。比如福建省泉州市余祖強、于珍鳳案20,兩被告人對檢方的指控作了無罪辯護,且在開庭后對案件事實有翻供現象,可見被告人完全沒有悔罪表現,更沒有從輕處罰情節,但是法院最終以被告人于珍鳳以書面形式較為深刻表達了其悔意為由對其適用緩刑,這是不妥當的。第二,對基本情節的刑罰適用時應以罪刑均衡原則為依據。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刑罰是對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罪刑均衡原則是確定刑罰程度的基本原則,是人們樸素的報應正義理念的具體體現。罪刑均衡原則的標準在于刑罰應當與犯罪性質相一致,刑罰應當與犯罪情節相一致,刑罰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在罪刑均衡原則下應當防止極端輕刑主義傾向。刑法對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基本情節規定了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相對于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等一些商品類犯罪的基本犯罪情節最高3年有期徒刑的規定來說,該罪基本情節的最高法定刑明顯要偏重些。同時,《刑法修正案八》也取消了原來有毒有害食品罪基本情節中的拘役刑。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為行為犯,其社會危害性比較大,我國刑法對其基本情節也設立了較重的刑罰。故在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基本情節的刑罰適用上應堅持罪刑均衡原則,根據犯罪人的不同犯罪情節,充分考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防止刑罰過輕。
2.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加重情節追求重者更重的時候應當慎重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的9個判例中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有8例,比例高達89%以上,體現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具有明顯的重者更重的傾向。此外,2011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罪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嚴懲“地溝油”犯罪活動的通知》要求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食品安全領域的適用,其明確指出:“在定罪量刑時,要充分考慮犯罪數額、犯罪分子主觀惡性及其犯罪手段、犯罪行為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危害、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程度、惡劣影響等。對于具有累犯、前科、共同犯罪的主犯、集團犯罪的首要犯罪分子等情節,以及犯罪數額巨大、情節惡劣、危害嚴重,群眾反映強烈,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依法嚴懲,罪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可見,我國目前對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實際上是要求罰當其罪,罪刑均衡。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才適用死刑,這符合立法的基本要求。但是,對于哪些情節可以視為“罪行極其嚴重”,一定要審慎對待,把握嚴格的法律標準,不能因為“群眾反映強烈”就強調重者更重,不惜動用重刑乃至死刑。因此,針對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加重情節量刑時追求重者更重應當慎重。第一,罪刑均衡原則是量刑的基本原則,量刑過程中應當注重罪與刑的均衡,質言之,量刑的基礎是罪名的社會危害性。對一個罪的社會危害性的評價應當是全面的,社會危害性主要包括客觀危害和主觀惡性,其中客觀危害主要是行為對社會秩序的危害程度。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屬于經濟類犯罪,作為行政犯的經濟類犯罪是禁止惡,與作為自體惡的自然犯相比社會危害性要小。從主觀惡性而言,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行為人主觀上主要是以牟利為目的,之所以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質是因為這種犯罪行為能夠為其帶來商業利益。其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放任的、否定的態度,故從罪過形式上,犯罪人對消費者的死亡只能是間接故意,相對于直接故意其主觀惡性要小很多。且在間接故意的案件中,犯罪人間接故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即對危害結果發生的放任程度有高有低。如“三鹿奶粉”案件中,三鹿集團的負責人發現“問題奶粉”后,緊急召開會議并決定“調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產品換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產品,并逐步將含三聚氰胺的產品通過調換撤出市場”,21可見犯罪人主觀上對可能發生的危害后果的放任程度與不采取任何補救措施的完全放任存在著惡性上的差異,顯然其主觀態度的惡性并非罪大惡極。第二,前述兩個通知中將“群眾反映強烈”作為加重量刑的標準并不妥當。罪刑均衡原則要求影響量刑輕重的要素只能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以及實施的犯罪所體現的社會危害性,而“群眾反映強烈”作為民意的體現不應該作為量刑的依據。刑事司法的不可妥協性決定了民意在其中沒有作用的空間,并且刑事案件的專業化特征也決定了民意的不宜擅入,在刑罰權不能讓渡給被害人的情況下,讓渡給民意是無法想象的。如果向民意妥協,雖然看起來暫時的維護了社會穩定,但實際上卻是犧牲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最終也就犧牲了法律的正義。另外,在現代社會網絡發達的情況下,何為真正的民意很難辨別。目前網絡輿論已成為民意最重要的表現方式,但網絡輿論所傳播的事實往往是松散的,甚至沒有經過質疑或論證,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又帶上了傳播者的個人價值觀和傾向性,客觀性大打折扣,極可能誤導民意。第三,前述兩個通知中將累犯、前科、共同犯罪的主犯、集團犯罪的首要分子作為嚴懲的依據并不妥當。累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但是不能基于累犯而提高對犯罪懲罰的法定刑檔次。前科并不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而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集團犯罪中的首要犯罪分子在1997年《刑法》中已經不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了。在罪刑均衡原則要求下應明確量刑的具體標準,不應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之外的因素考慮到量刑中。
三、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定罪中“量刑反制”的偏好及其否定
(一)有毒有有害食品犯罪中呈現出明顯的“量刑反制”傾向
在三鹿奶粉案件中生產“奶蛋白”22的張玉軍、張彥章等和河南“瘦肉精”案件中劉襄等被判處的罪名均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沒有認定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物質罪的原因在于行為人實施的是生產“奶蛋白”和“瘦肉精”這種添加物的行為,對象上不符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是考慮到行為人明知其生產的“奶蛋白”和“瘦肉精”一經使用會危害到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權,仍然生產、銷售,最終導致重大的危害后果,應當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兩個案件中值得思考的是,假如行為人生產的是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出售給食品生產商進行添加,是否仍應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筆者認為,對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的行為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錯誤的。第一,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性相當的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23在性質上,此罪是放火、決水、爆炸等罪的兜底性罪名;在犯罪構成上,此罪具有開放的構成要件。在認定該罪名時不僅要看結果上是否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等造成損害,還要看行為上是否達到與上述危險方法危險性相當的程度。關于危險方法,有學者指出,危險方法同時涉及行為的自身屬性與危害程度兩個方層面。在性質上,“其他危險方法”必須等同于放火、決水、爆炸和投放危險物質,即行為本身一經實施就具備了難以預料、難以控制的高度危險性;在程度上,“其他危險方法”又必須達到放火、決水、爆炸和投放危險物質所能產生的同等危險狀態,即足以威脅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財產安全。24換言之,危險方法并不是泛指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只有那些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的方法才是危險方法。25所謂“相當”僅指行為性質而不包括行為后果,因為能夠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非常的,如果以后果相當來評價危險方法,則就此失去了此罪作為刑法規范的確定性機能。26因此,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為雖然出現了危害大多數人生命健康的后果,但從行為性質上,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為不能等同于放火、決水、爆炸和投放危險物質等方法,即行為本身并不具有難以預料、難以控制的高度危險性。第二,這里需要澄清的邏輯認識誤區是以結果來推定行為的危害性,進而影響定罪。這種邏輯推理是本末倒置的錯誤思維形式,而生產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為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時法院采納的理由往往都犯了這類錯誤。正如在三鹿奶粉案件中,27法院認為張玉軍等人將“蛋白粉”銷售給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奶制品生產企業,對廣大消費者特別是嬰幼兒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國家投入巨額資金用于患病嬰幼兒的檢查和醫療救治,眾多奶制品企業和奶農的正常生產、經營受到重大影響,經濟損失巨大。法院認定張玉軍等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是張玉軍的行為對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的結果,而忽略了對行為本身性質及危害性的分析,是以結果影響定罪的體現。
筆者認為,對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的行為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典型的“量刑反制”現象。從犯罪流程上看,行為人基于主觀惡性支配行為,因行為而產生危害結果,所以行為是結果發生的原因,結果不可能決定行為本身的危害性程度。針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為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走入了以結果來推定行為的危害性的誤區,將以推定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作為量刑的標準,然后通過裁量之刑來制約罪名的認定,這嚴重違背了刑法的基本原理。
(二)“量刑反制”削弱了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定罪的確定性和規范性的標準
梁根林教授較早使用“量刑反制”的稱謂。在討論許霆案件中,他提出:“刑從(已然的)罪生、刑須制(未然的)罪的罪刑正向制約關系是否就是罪刑關系的全部與排他的內涵,抑或在這種罪刑正向制約關系的基本內涵之外,于某些疑難案件中亦存在著逆向地立足于量刑的妥當性考慮而在教義學允許的多種可能選擇間選擇一個對應的妥當的法條與構成要件予以解釋與適用,從而形成量刑反制定罪的逆向路徑?”28關于量刑反制定罪,學界存在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肯定說的主要觀點是:第一,通過認定刑事責任的有無和高低來認識行為的實質,這是刑法的基本邏輯;第二,先定罪后定量的順序推導不出正確定性是刑法的實質;第三,正確認定罪名,判斷具體犯罪構成的形式差異性只有手段性意義,最終目的是以恰當的方式和形式評價犯罪的危害性、服務于刑事責任的量定。29否定說的主要觀點是:第一,倘若先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再確定罪名,要么使法定的構成要件喪失定型性,要么對案件作出不符合事實的認定;第二,弱化罪名的重要性,即在某個案件事實符合法定刑較重的犯罪構成時,為了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就認定法定刑較輕的犯罪,這容易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第三,在更多的情形下,弱化罪名的重要性的做法,不利于量刑的公正。絕大多數犯罪的法定刑都是適當的,因而在絕大多數案件中,都不可以弱化罪名的重要性,否則反而導致量刑的不公正;第四,除了畸重畸輕的情形外,對犯罪人判處幾年徒刑合適,是不能憑對案件最基本情況的了解得出結論的。30
筆者認為,量刑反制的現象在現實司法中已經不局限在疑難案件中的“逆襲”,而是有泛化的傾向,這導致定罪與量刑關系的畸形異化,將定罪和量刑的因果關系反轉,違背刑事法治理念。
首先,量刑反制違背了罪刑關系。刑法主要解決兩大問題,即定罪問題與量刑問題。定罪與量刑是緊密相連先后有序的兩個問題,定罪后才能量刑,司法實踐正確的處理方式是根據刑法的規定先認定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構成何種犯罪,確定罪名以后再根據刑法規定的該罪的法定刑認定行為人的宣告刑。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定罪為量刑提供相應的法定刑是量刑得以存在的先決條件,也是防止重罪輕罰和輕罪重罰的基本保障。”32而主張量刑反制的學者指出:“判斷罪名的目的,是以恰當的方式和形式評價犯罪的危害性、服務于量刑。刑法解決的是行為人刑事責任有無和大小的法律,其他所有中間過程,都服務于這一終極目的。”32筆者認為,上述學者的對“定罪與量刑之間是手段與目的關系”的理解,完全沒有領會定罪與量刑這一關系的靈魂,因為它并沒有吸收刑事法治的合理內核。量刑反制為了追求所謂的“個案正義”,也不能違背基本的罪刑關系、脫離案件的具體事實而根據應判處的刑罰來選擇罪名,因為“不同的罪名對應的是不同的犯罪構成,而不同的犯罪構成來源于對截然不同犯罪事實的法律概括和提煉,出于量刑的目的更換罪名,否定了整個案件的事實,使定罪與量刑的邏輯關系產生根本性的錯位”。33并且,定罪與量刑的合理配置歸根結底是人類實踐經驗的產物,罪刑關系不合乎比例的情況雖然在所難免,但是應該通過刑法立法的完善和刑法解釋來解決,而非擅自改變定罪與量刑之間的關系定位。若強行如此,必然把司法置于風險境地。量刑反制現象不僅顛倒了定罪在前量刑在后的順序,而且量刑還影響到了定罪,違背了罪刑關系,應當予以擯棄。
其次,量刑反制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易造成刑事司法混亂。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應當承擔何種刑罰懲罰,都應當由刑法明文規定。量刑反制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在量刑反制中定罪并不是刑法的明文規定而是行為應當承擔何種處罰。質言之,行為人應當承擔多重的處罰成為定罪的依據,或者應當判處多重的刑罰影響到了罪名的認定。同時,量刑反制定罪論主張“量刑為目的,定罪為手段”,認為量刑才是最終目的,為了量刑的公正可以在諸多手段中選擇最優,其中包括了改變罪名,使同樣事實和情節的行為所定罪名不一,量刑有異。這明顯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因為刑法條文已經確定,即應成為法官進行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在沒有法律依據和罪名爭議的情況下變更罪名,明顯違反了“罪刑法定”的題中之義。此外,架空罪刑法定原則的量刑反制定罪易造成刑事司法的混亂。量刑反制定罪將會增加法律判決的恣意性,并使法律規范的預見性喪失。34
最后,量刑反制是重刑主義思想的殘余。量刑反制體現了重刑主義傾向,因為在量刑反制中一般都是根據刑法規定應當判處的刑罰不能滿足公眾報應的需求,需要尋找一個更重的罪名進行處罰。如上述三鹿奶粉案件中,公眾認為張玉軍的行為導致嬰兒死亡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對其進行嚴懲,所以法院適用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再比如,酒駕未入罪之前很多人就主張對于醉駕駕駛導致數人死亡的案件應當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這種重刑主義思想是過度報應思想的具體體現。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應當對過度報復思想、重刑主義思想予以摒棄。而量刑反制反映出來的重刑主義思想殘余同樣應受到清算。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在量刑反制案件中一般都是加重犯罪人的刑罰處罰,但是有時量刑反制也可能成為犯罪人逃脫法律制裁的工具,如上述案件中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最終因為量刑反制而被判處了輕罪罪名。
四、結 語
目前,各地司法實踐部門針對食品類犯罪都做出了相關的規定,而這些規定體現了重刑主義和量刑反制傾向,而重刑主義和量刑反制的本質是刑法工具主義。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關于辦理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2012年9月28日公布)為例,其第2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國家行業主管機關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質,或者銷售明知摻有國家行業主管機關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質的食品的,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國家行業主管部門命令禁止使用的非食品物質與有毒有害物質不是同等概念。該紀要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為了便于刑事偵查,從快打擊犯罪。該紀要第2條第2款規定:“對于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行為人在食品中摻入國家行業主管機關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質的,對涉案食品不需由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這同樣是出于從快打擊犯罪的需要。這種刑法工具主義傾向與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上述從快打擊食品犯罪的目的可能會導致對行為定性的錯誤,比如國家明令禁止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如果經過鑒定不是有毒有害物質,那么行為可能會被定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或者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該紀要第9條規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為《刑法》第144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生產、銷售假藥、有毒、有害食品或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也屬于其他嚴重情節。”可見,該紀要將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作為量刑的標準,而且是作為重刑標準,這與法律的宗旨存在著一定的偏差。
筆者認為,在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不能秉承重刑主義,而且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也應當摒棄重刑主義思想,不論從報應刑的角度還是預防刑的角度都應對重刑主義進行批判。有學者指出:“高度的封建專制統治,形成了以國家為主,以刑法工具論為基礎,以重刑主義為主體的刑法思想。重刑主義就象一個無法擺脫的幽靈,一直在國人的心中游蕩。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與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必須認真反思并徹底地根除重刑主義這一幽靈。”35從我國目前的食品安全問題看,刑事立法基本上符合社會現狀,通過重罰來預防食品領域犯罪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目前大量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與有關行政監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以及社會管理失范有密切聯系。刑法上的越位既會導致行政不作為的蔓延,也會導致社會管控手段的嚴苛,不利于法治社會的建設。
注:
1將原《刑法》第143條規定的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的罪名修改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為了打擊食品領域的瀆職類犯罪,加強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新增了食品監管瀆職罪。
2、15袁定波:《今年1至10月審結危害食品安全案173件》,ht tp://www.chinadai ly.com.cn/micro-read ing/dzh/2011-11-24/content_4473388.html,2012年11月20日訪問。
3張先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保持高壓態勢,依法嚴懲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http://www.tjacour t.gov.cn/popbase.asp?ArticleID=1639,2012年11月20日訪問。
4《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發出通知要求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http://www.cour t.gov.cn/xwzx/fyxw/zgrmfyxw/201105/t20110528_103702.htm,2012年11月20日訪問。
5 4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分別是:劉襄、奚中杰、肖兵、陳玉偉、劉鴻林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孫學豐、代文明銷售偽劣產品案,葉維祿、徐劍明、謝維銑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王二團、楊哲、王利明玩忽職守案等。
6參見“劉襄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ht tp://rmfyb.chinacour t.org/paper/html/2011-11/25/content_36557.htm,2012年11月20日訪問。
7參見王安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之我見》,《法學雜志》2007年第1期。
8參見梁根林:《歐美“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新走向》,載趙秉志主編:《和諧社會的刑事法治(上卷:刑事政策與刑罰改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頁。
9許福生:《刑事政策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頁。
10、12、16黃華生:《“寬嚴相濟”與“兩極化”之辨析》,《法學家》2008年第6期。
11 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1 Publishers,1975,pp1122)1231.
13 JackM cDev iu etc:Im prov ing theQual ity and Accuracy o f B ias Cr im e Statistics Nationa l ly(Fina lPro ject Repo r t),The Cen terfor C rim inal Justice Po licy Research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Februa ry 28,2005.
14參見李曉明:《歐美“輕輕重重”刑事政策及其借鑒》,《法學評論》2009年第5期。
17參見陳興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法學雜志》2006年第2期。
18參見劉憲權主編:《刑法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頁。
19參見陳興良主編:《刑法總論精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915頁。
20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余祖強、余珍鳳案”,(2002)豐刑初字第22號判決書。
21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石檢公刑訴[2008]271號。
22以三聚氰胺為主要原料生產的旨在虛假提高牛奶蛋白質含量的一種物質,俗稱“奶蛋白”。
23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頁。
24參見孫萬懷:《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為口袋罪》,《現代法學》2010年第5期。
25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21頁。
26、34參見于志剛、李懷勝:《提供有毒有害產品原料案件的定性思路》,《法學》2012年第2期。
27“張玉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2008)石刑初字第353號判決書。
28梁根林:《許霆案的規范與法理分析》,《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
29參見高艷東:《量刑與定罪互動論:為了量刑公正可變換罪名》,《中外法學》2008年第3期。
30參見張明楷:《許霆的刑法學分析》,《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
31趙廷光:《論定罪、法定刑與量刑》,《法學評論》1995年第1期。
32高艷東:《量刑與定罪互動論:為了量刑公正可變換罪名》,《現代法學》2009年第5期。
33曹堅:《“以量刑調節定罪”現象當杜絕》,《檢察日報》2009年12月21日。
35胡學相、周婷婷:《對我國重刑主義思想的反思》,《法律適用》2005年第8期。